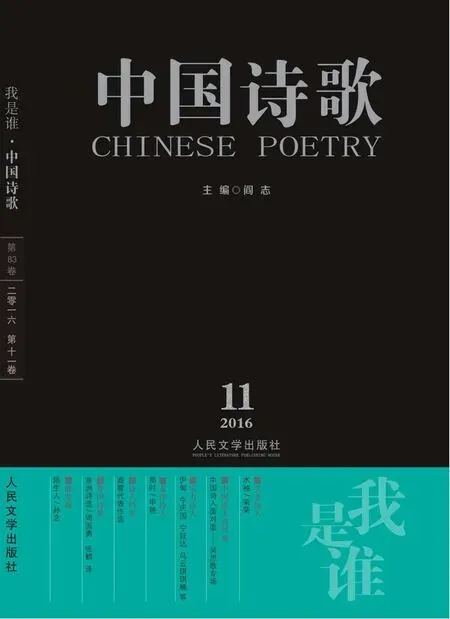泄露天機的人
□何 弘
泄露天機的人
□何 弘
和馬新朝共事多年,又是老鄉。1953年農歷十月二十四,他出生于唐河縣馬營村。村子就在澗河邊上,過了河便是我的家鄉新野。村里人趕集逛街、看病購物基本都是到新野這邊,而且,新朝的夫人也是新野人,因此,我和新朝就更多了層關系。但是,這么多年來,我卻從未專門給他寫過一篇文章。多年前新朝曾讓我給他寫篇評論,我滿口答應了,但因時時在應付催命般的文債,而新朝又不會多做催討,文章就這么擱置下來,直到現在。沒想到還這文債卻是在新朝遠行之后,想來就讓人感慨唏噓,隱隱心痛。
今年6月初的一天,我上班快到單位時,接到了新朝打來的電話。電話一通,就聽新朝說:“何弘,出大事了!”我心想當年新朝自己開車在高速上把車撞得幾乎報廢,也沒說什么,他退休后除參加各種詩歌活動外就是熱衷于書法,會有什么大事呢?新朝說自己得了胰腺癌。我懷疑,他說基本確診。然后他又說辦公室已經騰好,里面的一些舊書隨便處理了就是,辦公室就算正式交回了。我趕忙問了醫院、病房號,到單位簡單安排了工作,立即趕往醫院。
在醫院,新朝說,剛確診時,心里接受不了,過了一天就想通了。新朝平時不吸煙不喝酒,沒有不良嗜好,他說得這個病可能和家族遺傳有關,這就是命。他說他是農村出來的孩子,該經歷的經歷了,該做的做了,該得到的得到了,多活十年少活十年,并沒有太大的區別,所以他決定不做過多治療,對癥處理,減少痛苦就行。我和他說了原定的出集子的事,希望他身體條件允許時整理一下,然后我安排人來做。新朝當即同意了。但從醫院出來時,新朝夫人說,他的病已經沒法手術,肝和淋巴都有轉移,只能對癥做些處理,不讓他太痛苦。后來,新朝在做了膽管支架介入手術后,還是簡單進行了化療。我后來去看他時,他說大夫說適度的化療還是得做,腫瘤就像螃蟹一樣,張牙舞爪,得用藥控制一下。說這話的時候,新朝的旁邊放著一本杜甫詩集,顯然還在時時翻閱,這讓我再次感受到了新朝面對生死的曠達。但病情的發展還是出乎意料地快。8月21號我和馮杰一起去看他,又一次做完膽管擴張手術后,新朝的情況并未有明顯改善,黃疸嚴重,身體驚人地消瘦,醫生已下了病危通知。我們進去時,正好趕上新朝清醒過來,他輕輕擺手讓他妻子出去,拉住我的手只說了一句話:“我很痛苦。”我無言以對,面對新朝的痛苦,我無力為他減輕哪怕一點點,有一種沉重的無力感。后來,在病房門口,新朝夫人對我說,新朝快不行了,他多次和她說起,何弘是個厚道人,想為他做些事,但出集子、開研討會,都沒什么意義了,就不做了。我聽后心里感到深深的不安,有很多事,我們完全可以更早地做完、做好,卻偏偏要等到時間無可挽回地失去,徒留下遺憾。第二天中午,我正在單位吃午飯,接到新朝夫人的電話,說新朝情況很危險。我聽了趕緊和馮杰、萍子趕往醫院。到了醫院,新朝的呼吸已很困難。在新朝短暫清醒的時間里,和他做眼神的交流,感受著他承受的巨大痛苦卻無能為力。后來,情況出人意料地穩定下來。9月3日黃昏時分,我還在文學院時,新朝夫人打來電話,說新朝走了,16點50分。
我立即打車趕過去,路上通過微信發布了消息,通知了文學院和他詩歌界的幾位同事、朋友。在新朝家,我和新朝的親屬商量了他后事的安排,詩歌界的朋友也紛紛趕來幫忙操辦。第二天,自發趕來吊唁和幫忙的詩友站滿了院子,外地多位著名詩人也先后趕來,充分顯示了新朝在詩歌界的影響力。
新朝有一位叫馬體俊的遠房大哥,是個老地主,曾做過民國政府武漢市的教育長,很有學問。新朝少年時,常去聽他講古文詩詞,背了不少舊體詩詞,這是他日后創作的啟蒙。1970年11月新朝參軍入伍,到一軍二師服役,先是在開封,后來換防到浙江,期間開始創作,并提了干,做了宣傳股長。1985年初,他退役到共青團河南省委《時代青年》雜志社工作,繼續他的詩歌創作,也寫寫報告文學等。這期間,他隨隊采訪了黃河漂流,從黃河源頭一直走到入海口。這段經歷對他影響巨大,讓他寫出了榮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的《幻河》,并成為其創作的重要轉折點。2005年5月,他調到河南省文學院工作,先是做專業作家,后來又做副院長,成為我的搭檔。
新朝原本就愛好書法,在接近退休時更是差不多到了癡迷的程度。原本文學院成立有河南省作家書畫院,但多年來基本沒什么活動,新朝興致起來拉著馮杰要大干一番,并且給我安了個名譽院長的虛銜。這段時間的新朝,臨池不斷,從隸書、漢簡一直寫到甲骨,字很有些特點和氣象,于是就和詩歌界的子川、張洪波共享了“南川北馬關東張”的稱號。
新朝從事詩歌創作多年,在全國大刊上基本都發表過作品。他后來也寫一些應景的作品,但他多次和我談到自己對詩歌的理解與堅守,明白應景之作不過出于權宜,他說他決不把這些作品收入集子。新朝出版的詩集有《幻河》、《愛河》、《青春印象》、《黃河抒情詩》、《鄉村的一些形式》、《低處的光》、《花紅觸地》、《響器》等,還出版有報告文學集《人口黑市》、《閃亮的刀尖》、《河魂》,散文集《大地無語》等。《幻河》是讓他獲得巨大聲譽的作品,它讓流淌于大地上的母親河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之河,既寫實又精神高蹈,是對民族精神、氣質、魂魄的詩性表達。他到文學院之后,創作了很多短詩,并結集為《花紅觸地》、《低處的光》等。這些詩作是新朝詩歌創作的新突破,他以更低的姿態,在具體的生活事件上,在細微的事物中,感悟生命與存在,讓人對生命的真相有更深刻的把握。這些詩作體現了新朝對詩的根本理解:“詩歌是我生命的燈盞,我一邊用它照看自己,照看這個蒼茫的人世,一邊用手罩著,以免被四周刮來的風吹滅。我相信詞語后面所隱藏著的神秘的真相以及真理的美和拯救的力量。”新朝去世前幾天,他的最后一本詩集《響器》出版。“死者只與響器說話”,這是新朝《響器》中的詩句,似乎是讖語。在新朝的靈堂前,我坐在他平時常坐的沙發上,讀他的詩集《響器》,讀得毛骨悚然。他說他的詩是寫給“你們這些活著的人”的,“我這沒有燈火的殘軀/將引領你們回家”。他寫道:“我知道你們的前世和今生/你們所走過的腳印,都留在我的詩篇中/就是此刻,我突然升高,高出遍地燈火/高出你們生命中全部上升的血色素/我的形體里閃爍著人性之光。”新朝在這些詩篇中,通過常見的事物,寫出了他對生命最深的理解。把詩寫到這個份兒上,差不多是把生命最深的秘密揭穿了,也算是泄露了天機。古人常說:“天機不可泄露。”也許新朝是用詩的方式泄露了天機,上天惟恐他講出更多的秘密,決定把他招到天上吧。
新朝說:“詩是帶有體溫的文字,1000年后它還有體溫。”如今,新朝的身體已然成灰,沒了溫度。但他的體溫留在他的詩里,多少年后讀者仍然能從中感受到他的體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