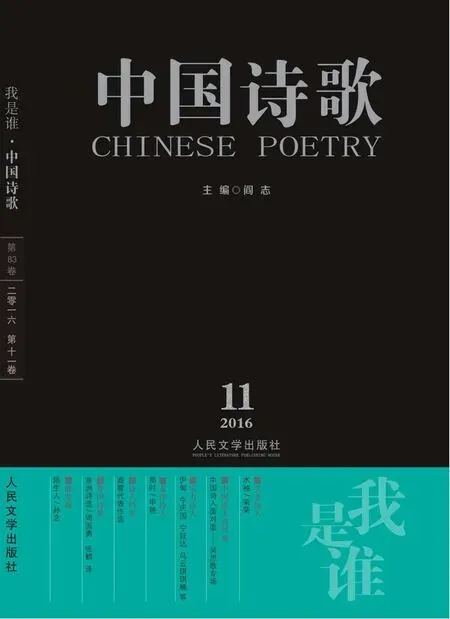水袖(組詩)
□榮 榮
水袖(組詩)
□榮 榮
代擬詩信
阿某:沒有你的日子時光常常斷流
我一次次起身 看到夜晚這只太老的貓
蹲在濃黑里 我害怕與它對峙
如同你那年的逃離
有些事我不想繼續了 它們不再是必須的
比如維持好名聲或好身體
它們曾是攀附你的閃電 而愛情雷聲在外
比如與你重逢 幕布再次掀開
看芥蒂和傷害的暗器又一次摸向胸口
阿某:其實托人寫信是多余的
你疏離已久 地址不詳
像好消息走失于人群
我費勁地描畫你幾近消蝕的臉龐
半夜醒來 疑惑是停不下的鐘擺
這世間是否真有過一個你?
但你決絕的話語炸裂每一處靜謐
最后那次相見也歷歷在目
一個章回小說里的情節:
一個不正經的帝王與失寵的侍女
你過大的雄心 我過度的卑微
時間的劍刃帶著尖銳的呼嘯
阿某:我知道我早被徹底丟棄
我知道我也該丟棄你
所有有關你的回憶全是致幻物
你給過的爛漫和明亮也只是
向命運高利借貸的油彩 由我獨自償還
一塊板結的泥土起身行走
是為了趕一場透雨
而我仍停留在你預設的路線上
眼下的你 多么適合抱怨
但你生來并非為我
你深入我的身體里 也只是一把意外的刀子
現在 我瘋狂地安靜著 仿佛垂死之物
仿佛命運眼皮底下 一件被退回的廉價贈品
站在一片沃土上想起的幾組詞
豐美和柔軟是一組詞
這是它愜意生活的感性部分
寬闊和強大是一組詞
這是它內在的意志被隆重說出
科技與藝術是一組詞
這是陽光和雨露 它的名詞和動詞
雄心勃勃 血氣方剛也是一組詞
直接接駁風生水起 日新月異這一組
還有潮流與激情 智慧和創新
它們都帶著鮮活的讓這片沃土沸騰的巨能
而心靈與家園是一組更深邃的詞
它們是這片沃土的底蘊 溫暖和芬芳
是這片沃土最尋常的愛的表情
幸運
閑下來突然惦記你。
真是幸運啊,你說你活著。
這是你慣常的語氣:
“真是幸運啊!
名利是夜街上追逐的貓狗。
我有真正的健康,童心和安寧。”
我想象你穿著闊大的衣服,
在菜場里恣意晃蕩,也學你造句:
真是幸運啊,生活可以如此寬松。
比起更艱難的旅人,我可以停頓。
比起更黑暗的行走,我可以等候。
真是幸運啊,這些年鎖孔沒有銹蝕,
門前地氈下總能摸到家的鑰匙。
真是幸運啊,我還能去看你。
聽細小的火花在我倆掌間畢畢剝剝跳動。
陳腐的愛情故事
他們只是牽掛著 越說越近
某一天才發覺已難分彼此
像兩只小心接近水源的羚羊
猜度和想象幾次將饑渴之心逼到絕境
也只相信眼淚渲染的愛情
眾里尋她千百度 她的悲傷閃閃發亮
也只是天各一方的輾轉反側
他短缺的夢里 盡顯她的星月亂象
時光窩在眉眼里
近些再挨近些 留一張剪不開的合影
相見已恨須發白
他眼觀鐮刀鐵錘 她身懷六甲刀劍
但一次次分手 她十步一回頭
他在那里 仍在那里 還在那里
和一個懶人隔空對火
僅僅出于想象 相隔一千公里
他摸出煙 她舉起火機
夜晚同樣空曠 她這邊海風正疾
像是沒能憋住 一朵火躥出來
一朵一心想要獻身的火
那支煙要內斂些
并不急于將煙霧與灰燼分開
那支煙耐心地與懶人同持一個仰姿
看上去是一朵火在找一縷煙
看上去是一朵火在冒險夜奔
它就要掙脫一雙手的遮擋
海風正疾 一朵孤單的火危在旦夕
小心!她趕緊斂神屏息
一朵火重回火機 他也消遁無形
我喜歡看你入睡
我喜歡看你入睡 看你一點一點遠離
你的柔情在嗓子里卡著蜜意又有什么關系
你進入的時空不再有我又有什么關系
像一艘船淺淺地靠往親愛的水邊
我是沉浸的月色 我是凌晨一點
我就在你身邊 這真的很美
你不再關心我的存在又有什么關系
那一會兒 你需要入睡你不需要我
又有什么關系
缺少睡眠的孩子 找到久違的家
我愿意看著你 躲開忽遠忽近的嘈雜
穿過睡眠的門廊 客廳 進入臥房
我愿意你安靜下來
那一會兒我是多余的又有什么關系
又有什么關系 等你醒來
等你一點一點回轉 我們又重逢了
瞧 良辰與美景就在一步開外
走心走肺的情意會多么坦蕩
醉的時候他們才是相愛的
醉的時候他們才是相愛的
酒到七分 他牽著她手當眾盟誓
酒到八分 他跳上臺為她且歌且舞
“酒真是好東西。”朋友們起哄:
“親一個。親一個。”
第二天他不再記得 也沒人提起
也只有在酒醉時 他心里的老虎才放歸山林
單獨遇見 他卻總是垂頭擦汗眼睛轉向別處
他幾次提起初見場景 她不記得
卻不忘第一次同醉 那時她正遭逢擊打
心有萬古愁 求一時忘卻
服務生一次次送酒送到手軟
紅的白的啤的堆高曖昧的酒沫
一幫人瘋鬧到非男非女屋頂微掀天色漸明
這個不自信的女子真的感動
她說 酒醉時分與她夫妻相稱的男子
相見時總給她一份敬重
送行時又搶先提上她的行李走在眾人前頭
他自然流露的好 那么天經地義
擁別時 她的身子想柔軟些卻總顯僵硬
她說 那時候她只想流淚:
“真好啊。想起他我就是快樂的。”
他的情誼是她罕有的珍寶
這不是愛 但比愛或被愛更好
水袖
那年小紅越過矮墻
她的水袖掛破在刺槐樹下
那年梅娘嚼著檳榔 她的水袖
被扯得山高水長 然后斷了
現在是她們 集體亮出的水袖
仿佛要先她們一步找到極樂之地
我如此清白又坎坷的情路啊
至今我的水袖仍深藏在肌膚里
仍沒撞到那一片
容我試探深淺的月光
背離
1
她的鎖心里沒有真愛的牙齒
但她仍是美妙的
他說:我只想做點我喜歡的
比如老年的迷醉和沉淪
春天繼續豐饒 懷想之痛也在
他的一意孤行 磨損多少耐心
“你開心就好!”空城里危機四伏
你反復出走 他永不歸來
2
還是說背離 作為情感的判斷詞
似乎它才是可信任的
就像真實的苦難讓幸福虛弱
就像相愛一再流于形式
當眾多的美只是附庸了春天
繁花落盡露出背離的骨頭
當肉體的親近也變得盲目
“也許。一切很快。”她說:
“我不阻止旁人,但可以叫停自己。”
突然被一句詩噎著了
那個年輕人將一句話藏在一首詩里
為了不被識破 他開始東拐西繞
東風破了西風續上
長城一角掛著曉風殘月
來些物理結構化學組合
再加一兩個虛擬的天體
一首多少有些被輕視的詩
眼下 誰相信還有不朽的篇章?
像習慣于門前小徑的漫步
你仍在閱讀 卻內心無聊眼神散亂
零星的花朵 略過不提
如同許多人 你早已丟下揪心的事物
也失落了較真的耐心
縱使滿腹錦繡終究歸于草莽
但那句話就藏在一首詩里
你突然被它噎著了
風里一縷細致的花香
又驚跳起來 像躲避踩著一朵鮮花
并且聽到細碎的骨骼碎裂聲
你停下來 茫然四顧
晚涼的風在草叢中的形狀
莫名
原諒我的遲鈍吧 我要慢慢確定一個事實
我肯定看到了一把刀 或者是劍
還有寒光 像晨曦劃開夢的口子
然后是血 但疼在哪里
原諒我的遲鈍吧 待我慢慢尋找疼的位置
它在心的正中 偏左或偏右
抑或在稍遠的地方
抑或只是新鮮的血在疼
我退在角落里 從頭搜尋這個事端
原諒我的遲鈍吧 沒有制造事端的人
沒有刀劍 也沒有真實的傷口
我的體內卻站著一個滿臉委屈的人
他的竭力否認 是否也是一種澄清
杜麗娘
她退回到那個夢里 抱住一對翅膀里的兩份輕盈
她退回到死亡里 等待一個人
在鏡月里捧起碎了一地的影子
僅僅相隔了四百年 前朝的生死已難以辨認
只有她 仍被分散在一出出戲里
昆腔綿柔而真愛鏗鏘
她婉轉的袍袖里空余多少顧盼
“不到園里,怎知春色如許。”
這個善情者 一味恣意著
人生很長 她只要一個春夢
死又何懼 她還能為一個人復生
當更多的后來者止于回避 不信任甚至厭倦
這個善情者 仍一次次出場并再三告白
她并非死于情滅 只是死于渴望
靈魂之愛永生于等待之中
文字的杯盤狼藉
她暮年的文字里有妒婦 怨女及抗暴者
也有復仇狂 焦躁病人和通靈者
這些寄生體
它們的活力來源于她內心的
累贅 毒瘤 濃烈的陰影
為什么不再有早先的潔凈和小腰
為什么不是和風細雨
掌燈夜讀 向舊事物里尋寬宥之心
為什么慢慢地跑偏了
慢慢地跟著她的人生走上歧路
眼下 她嗚咽的文字滿目蒼涼
雙刃
促膝不談心 只談眼前的風景
風景是新的 他的眼神也新
新單詞的新 新事物的新
只是他一起身
身邊的風景也舊下來了
是寒意叢生的舊 是薄薄的刀片
插入半明半昧寒意里的舊
而他近處的坦蕩和朝氣
與她遠離他的落寞
是它的雙刃
九回腸
這是否是不被原諒的?
當他用手攬住她 她更往他的身上靠了靠
是否同樣不被原諒:她竟喜歡他微微的碰觸
有一會兒 還以為她暗自發熱的左腿
能與他瘦長的右腿有一段親愛之旅
車窗外 山楂樹果仍是青的
滿山的綠藏起了滿坡的石頭
被一杯酒打開的身體
被一杯酒打開的身體
里面有一只空置的酒杯
你看見的是一個新鮮撕裂的傷口
你看見的是一只蜷縮之鳥的戰栗
被一杯酒打開的身體
也許會毀于再一次的打開
現在 她露出空置的酒杯
里面有她自釀的酒水殘留
像被狂風猛然撬開的窗戶
太長的時間里她有太多必須消化的風雨
四眼井
四十歲前純潔身體 五十歲后純潔靈魂
但隨意的清洗仍是冒險的
清澈甘美的泉水更適合懺悔
瞧 這個負罪之人在自怨自艾
她在四眼井里看到四種過錯四樣輕蔑
還有四個反純潔之詞
她也無法從懷里掏出月亮星星
車船兼程 什么時候它們不再如影隨形?
她只是路過 又一次路過
此刻 她的愧疚之影不被寬恕
未清除的戾氣 激怒了水中雄獅
此刻 她像一杯薄情之酒停于寬闊之源
找不到一種可以傾倒的理由
抱怨之詩
一個女人毫無預兆的憤怒嘴臉
轉向你 她言語里的電閃雷鳴夾雜著
風雨的腿腳 那個男人也是
很快 他們結成一個陣營
很快 身體里的一隊人馬也呼嘯而去
那張臉一改往日的柔情蜜意
多少年了 你總是側身行走
繞過是非小徑 仇恨大道
良善之人 還是步入了嚴酷時辰
像是釀壞的又一壇米酒
像安靜的傷口剝落了膏藥
像塵土四起 狼煙滾滾
你無法抹平內心的皺褶
縱千般委屈能與萬人說也一說就錯
只寫下幾句抱怨之詩看著天黑
昨夜突然失火的教堂
一座教堂的失火是上帝允諾的
或許是它尖頂的指向需要重新調校
這座失火的教堂他倆曾一同眺望
它一直突懸在一個街區的灰暗之上
景觀燈下教堂之美和尖頂之上的那片虛空
恍如天外之物 恍如不被信任的明天
他指尖的火焰來自他們失火的靈魂
他的指點里有一彎虛幻的月亮
而這之前她與他共有一個心臟
總以為一分開誰就會死
那天是哪天?現在是這場火與那場火
燃燒之物 都那么壯懷激烈
至今他倆仍失陷于空茫之境
內心的荒草掩埋了早年并不真切的臉
我是誰
我贊美過你的羽毛 服飾 聲音
有時候我忽視你過于渾圓或瘦削的身子
只贊美你笨拙的手指
它在指點:“茫然是一種更終極的前程。”
我也曾匍匐于地 為了不安的現實里
讓你多一塊立命之所
但我始終知道你是什么——
多么令人恐慌
當我走近 我以為你會認出我
像你的小短腿認出我的步子
你的小顏面認出我的淚水
好大風
好大風 它咆哮著
發動起億萬匹馬力的推土機
大地似乎也在為它挪移
好大風 它揭起了那么多瘡疤
讓黏在地面的厭棄物
有了逃跑的腿腳
好大風 它挨個兒敲打著窗戶
它要去熄滅
躲閃的眼睛里那些黯淡的火
甚至敲落了那顆來不及藏匿的星星
將許多落單的人
吹成憤世嫉俗者
但不用慌亂 正是大風時節
燈影亂舞 我一個人的想
像一張薄紙掙扎在半空
朵上茶吧
一提年代久遠 她就暗自摸一摸身體里
藏掖已久的這個詞
一提年代久遠 楓楊樹懸鈴木不動聲色
巷子的濃蔭卻晃了一晃
跟著晃蕩的還有朵上茶吧里暗藏的
一些身影 那么的仿佛曾經依稀
那么的惺惺相惜 情愫低回
親愛的地方親愛的幽暗氣息
親愛的年代久遠的記憶
但為何她還在悵然四顧
還假裝成千瘡百孔的失怙之人
外露的憂傷涂一層合法的迷彩
像是
像是有個男人正在來路上
她的輕舉妄動需一捺再捺
他只想與她談談禁忌
或單純日常里的種種調劑?
還是為了這場擦肩戲里的
兩顆真實之淚?
從大老遠跑來 他就要到了
像是鄰桌上那道跑味的葷菜
北方白樺林上的蒼茫
北方平原上大片的白樺林
在道路的兩邊盡情鋪排開去
遮天蔽日的蒼茫
也從這些闊大的林中升起
我喜歡這樣的蒼茫
它們一定安撫了我的內心悲愴
我也喜歡看那些長尾鵲
在這樣的蒼茫里悠然地來回
將窩筑在或高或低的枝杈上
仿佛白樺林給了它們更開闊的選擇
它們可以是蒼茫的主人
也可以是蒼茫的仲裁者或代言人
在沂蒙 一位水瓶座的女子只有淚水
一位水瓶座的女子動輒流淚
歡喜流淚 落寞流淚
她多么任性 遠山遠水想個人
見或不見 直淚一道橫淚一道
半夜夢回淚兩行
高興一行 失意一行
在沂蒙 這位水瓶座女子也只有淚水
是感動之淚 感激之淚
多暢快的熱淚啊 只是她不再掩飾
只想讓淚水奔騰著 跟著英雄的熱血
在這片土地上恣意地流淌一遍
在沂蒙 這位水瓶座女子
頭一回覺得自己的淚水是真實的
與這里的山川河流同質
頭一回覺得淚水可以那么滾燙
那是貼著英雄的熱血而流
在沂蒙 她流著淚走過一個個山頭
忍不住將親愛的祖國又狠狠地愛了一層樓
忍不住將眼下的日子又狠狠地愛了一層樓
忍不住將深愛的人兒又狠狠地愛了一層樓
沂蒙紅嫂
如果可以 我也要進入這個群體
用初識的自由 民主 富饒這幾個字眼
憧憬共和國的藍天
我也會像她們一樣 春種秋收 紡紗織布
最后一口糧食 留給戰士
最后一絲布 納成軍鞋
最后一個孩子 送上戰場
最后一滴乳汁 喂養革命
我也要成為這方土地灑不盡熱血的一個源頭
樸素的情感 從心底里搬出來
便是人性浩大的盛宴
虛化
那么多人!每一個都閃著
自以為耀眼的光芒
每一個都有許多方向
每一個身后都跟著許多條大道
還有更多的爭吵和結論
聲音像是潭底一次次攪起的泥沙
他們更詫異于我這卑微之人的孑然獨行
帶著如此微弱的聲音和光亮
詫異于淚水鋪就的小路
竟是我從心所欲的那一條
潘天壽
我的敘述 始于名叫冠莊的村莊
它有質樸的心 淳厚的肺 堅硬的骨骼
它有繞樹三匝的剛山柔水
一個慷慨的長者 從它的肺腑里掏出全部顏色
鋪就他血液和肌肉里原始的底色
我的敘述 始于那座雷婆頭峰
始于它的突兀嶙峋 聰穎靈秀
始于它的疏枝密影 碧波千仞
在那里 他第一次望見了未來之路
從此高山流水 家鄉千里
我的敘述 始于一個漸行漸遠的身影
這個終生的跋涉者
背囊里裝著山水絕句 性情文章
一雙腳用來丈量群峰
走得如此之快
像要趕著節氣開滿樹的花結滿樹的果
將俗世遠遠甩在后面
走著走著路就深了天就寬了
走著走著他就走到了云端
塵埃向下落定 眾人仰頭看他
看他張揚狂放中的清麗 率真
看得十分骨氣十分才學
看一幅天地立軸 鬼斧神工
然后 我要提到那些石頭
看得見的堅硬 看不見的陡峭
一塊 又一塊
他幾乎掏出了偉岸肉身里的全部鈣質
霜花一兩朵 寒鳥三四只
瘦詩七八行 說著深淺
說著天地間的孤懸或隱喻
這些石頭橫空出世 讓酣暢之美無處逃逸
這些石頭擱在心里 他便有了扛鼎之力
便一味霸悍 勇于不敢之敢
這是藝術的骨頭 美的脊梁
他喜歡與石頭說話 這一說就是一生
他說了很多 有些我們聽懂了
那些方的更方的 銳利的更銳利的
一個惜言如金的人 在石頭上露出他的陽剛
他喜歡與石頭說話 這一說就說出了不朽
他說了很多 有些我們一時聽不懂
聽不懂還是想聽 趴在石頭上聽
隆隆聲由遠及近 天上人間聽得分外肅穆
然后 我要說到一只靈鷲
雄踞于方巖之上
或踱步 左一爪孤傲右一爪孤傲
天空藏不住無邊的蔚藍和遼闊
一飛沖天的翅膀藏不住渴望
一只靈鷲 就要抓起一塊生根的磐石
直上云霄 眼下它仍在等待
仍在蓄積更大的力量
那一刻 群山寂默
他讓一只巨鳥的筋骨在渴望中疼痛
這只靈鷲 同樣也說出了他內心的敬畏
內斂的豪情和凌云壯志
也許 我還要從一朵花說到另一朵花
從山花爛漫 清荷新放 菊氣熏風
說到一枝寂寞的勁梅 獨傲霜雪
這些高潔的花朵說出他的高潔
這些干凈的花朵 疏影浮動
將污泥和濁水逼開三丈
一只鳥在盤旋雀躍 許多只鳥在盤旋雀躍
濺起驚訝的春光 一片兩片
這也是他的心花 他捧出來
細致地移栽在紙墨上
為我們說出隔世的孤獨和芬芳
現在 我要說到他的手指了
不指點江山 江山千里萬里的錦繡
他用指力搬來一角
只一角 就氣象萬千
都說他的手指比別人靈巧
這說法總顯輕淺 抹煞了多少
長夜苦熬 百錘千煉
都說指墨畫大師 緣于他小時候
被收繳了畫筆 美景空對
畫事總被誤為“君子不齒之事”
他滿腹荊棘 但不辯白
深入骨髓的 是熱愛至死的疾病
我更愿相信 他以指代筆
只因筆之柔軟無法繃直他的靈魂
磨禿了千支萬支
最終 他拿自己的骨頭作筆
現在 我的敘述里還要提到一場戰爭
一面破碎的鏡子 照著走散的笑臉
同胞在水深火熱 藝術在流離失所
多少新愁與舊傷 握不住一支離亂之筆
沒有所謂的后方
他如何扶正歪斜的畫案
如何畫出愿望里的晴空和藍天
整整八年 悲憤是一塊卡住喉嚨的堅冰
遷徙途中 學生在課堂上圍著要他畫山水
他舉起筆 嘆口氣又放下了
“半壁江山都淪陷了,等抗戰勝利了再畫吧。”
一滴滾燙的淚來自心底的烏云
一滴淚的熱度來自于信念
——腥風血雨總會過去
祖國一定會重開藝術的笑靨
現在 我的敘述里還要提到他命里的三個女人
自由地愛 自由地結合和分離
是長在他生命之樹上的三顆果子
是他一生的甜 一生的不安和愧疚
三條河流 流出他生命里的華章
三場戲 多少悲情多少精彩
他用一生的真誠出場
她們用全部的生命演繹
一個在家鄉望斷秋水
一個為愛終身凄苦
一個是幾十年同甘共苦的患難妻子
時間翻過去流水的冊頁
翻過他的青蔥 他的老年
翻過高大的身軀為柔弱的肩膀擋風遮雨的他
翻過他一世的堅守 暗中的無奈和唏噓
就像他較真了一輩子的國畫藝術
他天分獨厚 英年得志
“行不由徑!” 多少類似的詰問
不改他執著于藝術之真 執著于永恒之道
——“天驚地怪見落筆”
他大筆淋漓 別開生面
“畫當出己意” 他謹記著
又不斷地為自己設置雷霆
一個自我博弈之人 在渴求完勝
畫不驚人死不休 每一張都必須是精品
便畫了撕撕了畫
有時撕得多了撕得重了
落在紙上的花鳥蟲草
隱隱傳出肝臟和骨架細細的碎裂聲
心血紅黃黑白地洇濕了指尖
他每天都要畫完一刀紙
這些紙 只用來承載和渲染他的不羈
——“師其意不師其跡”
傳統和外來文化
像兩只慧眼左右盯視他
他獨立其中 為自己辟開一條大師之路
多少聲譽 也視作身前身后土
多少年的踐行踐言
他著書立說 桃李天下
卻始終放低自己 只愿是一個平凡的畫者
——“做人要如履薄冰。”
一個敦厚的師長
一個樸實訥言的人
眾人眼里一座巍峨的高峰
卻常三思己過 心懷愧意:
“對國家、父母、兄弟是嫌不夠所想,
于心殊感不安。”
他甚至認為自己:
“因為歡喜弄弄國畫,
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表不知其里。”
木秀于林 風必摧之
不愿變通的鐵 寧折不彎的鋼
如何能躲在畫里 撐住清白的顏色
人情世故的薄冰 他可以從容勘破
顛倒的天地 莫須有的罪名
卻讓坦蕩之心找不到躲藏的縫隙
“莫嫌籠縶淺,心如天地寬。
是非在羅織,自古有沉冤。”
雷婆頭峰從不彎腰
倔強的石頭不說軟話
我依稀看到 故鄉的清晨里
一個羸弱的老人跪在風雪之中
天空低垂 仿佛在安撫一對折傷的翅膀
我依稀看到 斯文掃地的日子
他用倔強 和被摧殘的身心
畫著世間最寒冷的一幅圖畫
那些日子沒有太陽
他就是太陽 被無知和野蠻之箭射落
那個夜晚沒有月亮
他就是月亮 他落形的身體
再也扛不住內心的光輝 他在隕落
巨大的隕落聲 很少有人聽見
一個世界在裝聾作啞
一塊大色掉了 天光陡暗
苦難在輾轉反側 傷痛在輾轉反側
他只想靜下來
靜 或者長久地睡去
他抱怨一時還靜不下來的身體
他的雙腳不停地抽搐著
它們走得夠遠的了
它們是否還想走得更遠
它們已不聽使喚了
這心外之體啊——
“我想叫它不要動,不成功……”
“我想叫它不要抖,不成功……”
沒有醫生的看護 或許他真的不需要了
沒有更多的人來送別
只有親人 放不開他的手
這與一個世界的寒冷相連的手啊
只有拳拳老友毫無顧忌的悲傷
一雙顫抖的手摸遍他的全身
一雙顫抖的手摸著他一生的痛
想摸平它們 好讓他不再痛
病房里真安靜 像自制硯臺里
他親手研磨的新墨 傾入時間之水
漾開去 漾開去 漾開去
直到今天 我似乎還能聽到
刺穿心肺的鋼針的落地之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