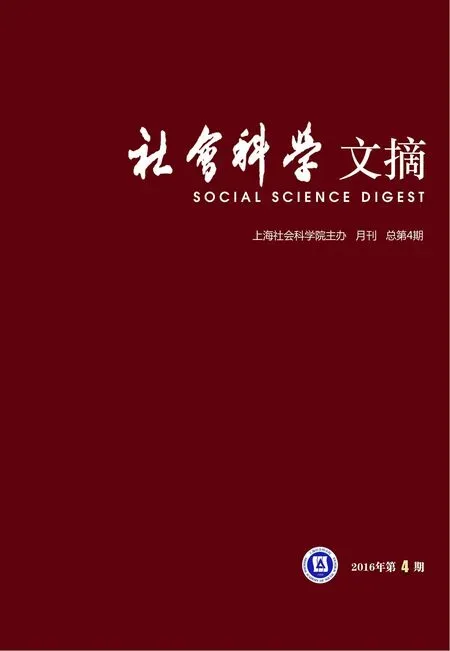政治實踐中的“中華民族”觀念
——從立憲到革命中國的三種自治
文/殷之光
政治實踐中的“中華民族”觀念
——從立憲到革命中國的三種自治
文/殷之光
今天關于“民族自治”問題的討論,大多數從理論上并未真正超出19世紀以來在歐洲形成的當代西方民族主義框架。這種建立在歐洲歷史經驗基礎上的“民族國家”觀念,其基礎是在威斯特法利亞合約中確立的,在基督教國家之間互相認可的國家主權,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新教相對天主教在歐洲內部國家間的平等權利。這種主權觀念,本質上是一種土地產權私有化觀念的延伸。王權與教權之間沖突的一個重要問題,便是對于土地所有權的界定。強調同種同源的“原住民”對一塊土地的專屬權利,是這種現代歐洲民族國家主權觀念的基礎。國家主權的建立意味著與普遍教權的分離。在今天民族主義的敘述框架內,這種法律意義上的排他性主權,被作為“民族國家”重要屬性,并進而將世界打碎,成為了“天然的碎片化空間”的集合。這種碎片化的政治現場無法為平等的大同理想提供思想與實踐資源。
在中國19世紀的革命與近代化歷史語境下形成的“民族自決”與“民族區域自治”,其“民族”觀念,相比這種以血緣為基礎的族裔民族主義認同要復雜得多。這里的“民族”與社會解放政治理想相結合,更涵蓋了對生產關系及世界體系發展的歷史判斷。對于經由革命建國的新中國來說,其“中華民族”觀念的構成,不但與其“反帝反封建”的對抗性革命任務相關,也與其建設性的國際主義普遍關懷密切相連。而只有在20世紀中國與世界不斷變化著的政治現場中,我們才能真正認識到“民族區域自治”政策作為一個產生于中國革命這一特殊歷史進程中的事件,其背后所蘊含的普遍性價值。
在現有對民族及其自治問題的討論中,“民族”被處理為一個知識而非政治范疇。絕大多數敘述,或試圖尋找“民族”概念在辛亥前后作為一個外來觀念,在中國的發生與發展;或希望找到傳統中國天下體系中的“夷夏之辨”與近代(西方)“民族”觀念之間的對應關系。近些年頗為興盛的美國“新清史”學派學者,更跳過“民族”概念本身作為一個晚近創造物的特性,設定了一個中國歷史觀中的“中原中心主義”,并將作為地理概念的“中原”等同于作為近代種族觀念的“漢族”,構建起了一整套“漢族政權”與“非漢族(滿族)政權”,“漢文化”與“非漢族(滿族)文化”之間勾連互動的“多元性”帝國歷史與中國“殖民史”。在這一邏輯下,新清史學者出現了西方中心且非歷史的錯誤,按照今天西方學術話語中的“常識”,預設了“文化”“民族”以及“國家”這些核心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并用此來重新理解一個實際上從法理上與歐洲/美國截然不同的中華帝國。實際上,雖然隨著帝制的衰亡,共和政體隨革命而興起,中國作為一種具有普世關懷的知識體系仍舊在不斷延續。
晚清時期的立憲自治與實踐
我們應當將“民族”觀念的構成放在一個對世界認識的變化過程中。19世紀中后期,隨著殖民主義帝國擴張及貿易權爭奪而日益加劇的清朝陸上邊疆危機,連同清朝海疆及腹地受到的壓力,構成了一種極為復雜的對清朝治理模式——特別是中央與地方關系——的結構性挑戰。越來越多的清朝知識分子以及有處理“夷務”經驗的官僚開始認識到,描述世界的普遍性話語實際上具有多樣性。清朝后期左宗棠、王文韶、李鴻章、文祥等大臣對于“海防”與“塞防”的戰略討論中,清朝開始從政治上意識到邊疆領土與腹地之間的互聯互通關系,并按照近代民族國家領土觀念重新制定對沿海及內陸邊疆地區的管理方式。隨著1884年新疆建省,1885年臺灣建省,清朝在這種逐漸形成的、以民族國家主權為基礎的新國際法世界秩序下,為后來的共和政體,進一步確立了一個包含22省的疆域。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對于“自治”問題的討論,實際上強調的是一種代議制憲政體系下的新型國-民關系,以及對“民”的政治覺悟的要求。
對于梁啟超來說,這種落在個體上的“自治”,其根本目的是為了培養“民權”意識,在新的世界秩序環境下,創造一種政治自覺的“愛國”國民,并進而構成一個具有現代政治意義的“國”。自治還被當作培養民眾政治意識與參政意識的途徑。在諸如兩江總督端方和江蘇巡撫陳啟泰這類立憲派官員看來,立憲改革是世界大勢所趨,而其基礎則是地方自治。他們認為,通過地方自治,改變傳統中國中央集權式的“官治”,在地方設立資政院等代議制機構,自上而下地培養地方政治人才,以期為中央政府設立議院做準備,實現歐美國家式的“自治”。在這個敘述中的“自治”可以對應英語中的“local governance”,或者更為確切地是行政意義上的“Borough”(有議員推選權的最小行政區)概念。這種“自治”實際上是試圖在原有的中央與地方各級行政單位之間的上下級管轄關系中,加入一定的代議制機制。
然而,從效果上,“地方自治”并未真正達到梁啟超等改良派知識分子所設想的培養“國民”意識的政治作用。這種自上而下的改良主張,遠未提供任何有效的手段,將占中國人口比重最大的農村與城市勞動人口組織起來,并培養這部分人群的政治參與意識。實際上,隨著“自治”運動和維新改革而迅速膨脹的地方紳權,不遺余力地以請愿、抗議等方式同中央政府爭權。此外,地方官紳勾結,在地方自治經費自籌的名義下,大肆增加地方捐稅,建設地方武裝,甚至還有干預刑訟。在地方自治名義下,形成了士紳階層壟斷地方教育、實業、財政、司法、警務、公共設施建設等社會關鍵部門的局面。
在清末這種地方自治實踐中,主要支持立憲的省份或是在洋務運動官僚支持下工商業發展較快的沿海省份,或是在路礦企業較多的中南部漢人聚居省份。而在少數民族的邊疆地區,如新疆、東北等地,清政府建省的目的則主要為移民屯墾,發展塞防。
民國政府的自治理念與實踐
清帝遜位之后,一個原本的“天下”帝國在法律意義上突變成為一個“國家大家庭”中的共和國。雖然這一時刻從孫中山等革命者的表述上被看作是一個美國式的“建國”運動,但無論是從《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與晚清立憲之間千絲萬縷的關系出發,還是從反清革命的政治實踐來看,都遠比美國建國時刻的那種割裂式革命要復雜得多。在反清運動時期,革命黨提倡一種“聯省自治”的概念。與立憲派的“自治”不同,革命黨人的“自治”觀念開始具有“autonomy”的內涵,并一定程度上承認了地方的分離權(right to secession)。當然,我們也會發現,這種意義上的自治在辛亥革命時期,被用作對抗清政府治權的武器。其政治底線仍舊是分離后的舊有領土以聯邦制形式重新組織為一個共同體。這一點,無論是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還是孫中山的《臨時大總統宣言書》與《建國方略》中都有明確體現。
從治理邏輯上,民國政府一定程度上仍舊延續了清朝羈縻政策中明確的上層路線。即試圖以行政命令的模式,自上而下地確立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職權關系,且行政手段也明確以處理與地方/民族集團上層人物關系為核心。從選舉制度上,國民政府采用區域代表,而不以民族為單位。目的在于實踐孫中山辛亥后開始提倡的融合五族為一大中華民族的建國思想。1931年頒布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中提出,“中華民國國民無男女、種族、宗教、階級之區別,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這種民族融合觀念下的法律平等地位在1936年5月5日,南京政府公布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中更進一步得到強調,草案提出“中華民國各民族均為中華國族之構成分子,一律平等”。這種對“民族”和“國族”的法律性區分,建立在孫中山《三民主義》中,建立在世界地緣局勢與政治歷史的角度上,與發揚個人民權、聯合宗族、建設一個大的“國族”觀念一致,也與梁啟超在闡述伯倫知理國家學說基礎上提出的“大民族”和“小民族”的概念類似。
但是,以自治為手段,精英為主體的民國平等政治,其結果不盡人意。盡管在孫中山的革命隊伍里有諸如白崇禧、馬步芳、馬國榮、吳鶴齡、劉家駒等這樣的非“漢族”精英。但是,作為群體的“少數民族”仍無法真正作為“國民”,參與到民國政治活動中。民國時期這種延續了清朝立憲運動中自上而下“自治”理念的政治方式,在毛澤東看來是“官辦自治”,本質上是“虛偽的”,而且“不能長久”。在他看來,政治不能是一個“特殊階級的事”,“以后的政治法律”應當“裝在工人們農人們的腦子里”。在他看來,“‘法律學’是從‘法律’推究出來的,‘法律’又是從‘事實’發生的”。
中共視野下的自治理念與實踐
作為一個整體的少數民族及其人民,其政治意義則是隨著中國革命局面變化,特別是1927年國共分裂之后,才逐漸出現在革命建國的實踐視野中。而隨著1927年共產黨實際活動重心從沿海城市向內地農村轉移,以及邊區蘇維埃政權的先后建立,邊疆(以及鄉村)也從原先那種需要被治理與教化的落后地帶,變成了一個構建共和國政治平等實踐的有機參與者,甚至是革命活動的中心地帶。對于邊疆以及通常與之相聯系的“少數民族”的發現,伴隨著中國革命對農民階級的發現。隨著長征,共產黨作為一個有機整體,真正走到了少數民族聚居的邊緣地區,并切實將抽象的革命建國理想具象為被壓迫人民翻身解放的平等運動。在精英政治外部的邊疆/少數民族,也正是通過這一條實在的“長征路”,同作為地理概念的腹地,以及作為政治理想的中國連接起來,并與其他“被壓迫”的“人民”一起,逐漸共享起一個共同的翻身平等的理想。這種被長征路連接起來的平等理想,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而擴展到對整個世界被壓迫民族獲得平等的信念之中,成為新中國得以進行抗美援朝,得以支持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人民基礎。
從《共產黨宣言》德文文本中,我們看到一種更為復雜的“民族”觀念。與單純代表政治性的“民”(Volk,英譯為people)概念,以及代表天然物質屬性的“土(或邦)”(Land,英譯為country)概念不同,“族”在馬克思的敘述中融合了生產方式、階級政治關系以及歷史沿革等多方面的復雜內涵。他描述的這種由于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迅速發展而形成的統一狀態(eine Nation)是一種世界體系,這與之后列寧所描述的“帝國主義”在脈絡上是前后相連的。 “Nation”作為一種生產方式關系的產物反映了一個固定地理區域內部的秩序,它可以由單一的種族構成,也可以是多個種族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政治聯合體。與德語中代表了政府治理權威的“staat”(國家)不同,“Nation”更具政治活力與歷史感。它是一個隨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變化而變化的產物。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理解“Nation”為什么可以進一步擴大為一個跨區域的“Internationale”秩序關系,以及這種秩序關系所代表的平等意義。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已經明確,要將對“民族問題”的理解放在一個國際秩序大框架下。早期共產黨對“民族自決”的理解建立在一種對蘇聯世界革命的理想主義信仰之上。由活躍在東部城市中的漢族知識分子組成的早期共產黨將“中國”視為一個整體受到“世界資產階級”劫掠的市場。而“中國本部”與“疆部”由于“經濟情況”的差異無法統一,因此,需要在“中國本部(包括東三省)”、“蒙古、西藏、回疆”四者之間通過分別自治的方式,形成一個“中華聯邦共和國”。當然,由于各地區面臨的國際壓力不同,因此“自決”的實行方式和時間也各不相同。早期的中共對“現代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原始的民族排外”做出了區分。在對醒獅派國家主義思潮那種“自求解放”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進行的批判中,中共通過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針對民族革命運動的決議案提出,中國“同化蒙藏”的“大中華民族”和土耳其的“大土耳其主義”(即泛突厥主義)均是具有霸權的政治,以“民族光榮的名義壓迫較弱小的民族”。而“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強調民族的自決權,是“平等的民族主義”。在針對蒙古自決問題上與國家主義派的爭論中,共產黨知識分子采用了一種較為模糊的立場,提出雖然“不鼓動”蒙古人自決,但卻也反對“一班人”否定民族自決權的態度。
1927年之后成立的“紅色割據政權”認為,其基本責任是將中國革命的任務從資產階級的“新軍閥”手中延續下去,并最終解放“中國整個的民族”。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隨著革命從城市轉移到鄉村,原有的“國-民關系”被從一個抽象的認同以及民主治理方式,具體化為一個農民和土地之間的關系。開始進行根據地斗爭的共產黨認為,在中國具體的環境下,對于占據人口最大多數的農民來說,其自由權利的伸張是要將其從一個舊的剝削的土地關系中解放出來。這種解放必須承認各地方經濟發展階段的內在差異性,而不能簡單通過一種自上而下地命令方式而達成。在這個意義上,對“滿、蒙、回、藏、苗、瑤各民族的自決權”的承認,是從政治上對這類地區與廣大漢族地區差異性的認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農村革命根據地在少數民族地區的變型。這種自決權已經不再是20年代早期在共產國際指導下那種強調分離權的自治運動,而變成了對各民族、地區人民發揮政治主體性,在對自身社會經濟發展條件、政治環境分析之后,采取不同方式進行土地革命權利的認同。通過這種認可自然差異性的政治方法,新民主主義革命希望達到一個具有普遍性的政治目標——“統一全國”。
在1940年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將中國20世紀革命總結為一個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性發展。以1927年為界,舊民主主義革命形成于半封建與半殖民地的條件下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民族獨立運動;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體則為逐漸具有政治覺悟的人民,同時,人民又在這一革命過程中逐漸獲得政治自覺。這種從舊到新的民主主義革命轉化,在毛澤東看來,與前文所敘述的馬克思對作為世界體系的“民族”關系變遷有著密切聯系。只有將中國革命放在世界革命的整體秩序關系中,才能真正理解革命本身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進步價值,也更能超越簡單的威斯特法利亞體系所規定的那種狹隘的、排外的、以私有土地為基礎的“民族主義”。而革命者們那種“好為人師”的態度以及在這種態度基礎上形成的那種自上而下式的對民族“治理”與民族關系的理解,也在長征這一實踐過程中,真正轉化為一種“實事求是”的政治方法與理論態度。馬克思所描述的那種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普遍聯系,以及在這一聯系過程中形成的民族間作為“公共財產”的文化,也在長征這一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踐過程中,以平等貿易為載體,構成了毛澤東所描述的“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種超越了簡單的“民族國家”范疇的民族與國家主權觀念,在解放戰爭結束之后,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進一步拓展到對整個第三世界民族獨立運動的認識中。
作者單位:(英國艾克賽特大學人文學院;摘自《開放時代》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