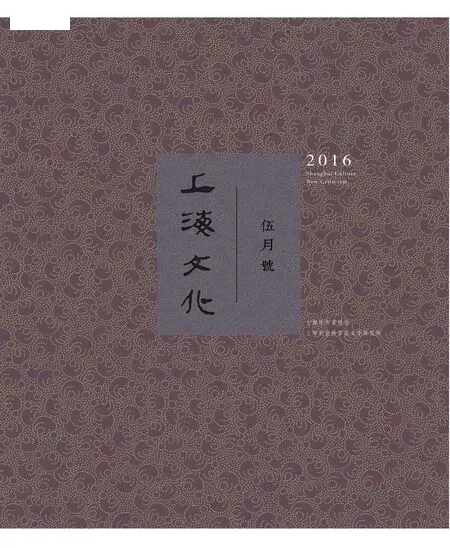我只是大時代中的小書生
趙園項靜
?
我只是大時代中的小書生
趙園項靜
項靜:您這一代學人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是比較特殊的:“文革”后進入高校或科研機構,擁有較為豐富的社會生活經驗,親歷了一些重要的歷史關頭。您能簡略談談自己如何走上學術研究之路的嗎?
趙園:我從事學術工作,完全賴有機遇,沒有任何預先的規劃。當時我在鄭州的一所中學教書,只是姑且一試。考不取,無非繼續教中學,沒有什么可以失去的。至于倘若考取會怎么樣,無從設想。因為我對“中國現代文學”是什么模樣,幾乎沒有概念。應試之前,除了魯迅,沒有讀過其他中國現代作家的作品,包括《子夜》、《駱駝祥子》。從小學到中學,直至“文革”,讀的是外國文學。高中又迷上了中國古代散文。即使1964年進入北大后,因為只有不到兩年的學習時間,對中國古代文學,至多算個愛好者,談不上“專業基礎”。1978年的研究生招考,不過給了我一個改變處境的機會罷了。“走上學術研究之路”,是讀研之后的事。與我的大學同學不同的,或許只是我敢于冒險一試,而有些人不敢,錯失了機會。
幸運的還有,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以至1980年代,是鼓勵學術寫作的時代。出版界以發現與扶持“新人”為己任,你不難“脫穎而出”。并非你真的有怎樣的實力,而是你有可能在生荒地上耕作——中國現代文學這個學科,原有的積累不夠深厚——只要播種,總會有點收獲,壓力較后來的年輕學人小多了。
項靜:“文革”期間京滬等地曾經有地下讀書活動,您的閱讀和這些活動有沒有交集?
趙園:較少有交集。由我讀到的材料看,那個部分知識青年——還應當說,只是極少部分的知識青年——的讀書活動,主要在進入1970年代之后,而我1970年代初就到了河南農村,之后又在鄭州教中學,沒有機會躋身那些“沙龍”、“村落”、讀書會。信息時代之前,京滬這樣的城市,與“外省”氛圍的不同,已經不是時下的年輕人所能想象。我在遠離北京的地方,漫無目的地讀書。除了“文革”初期的讀魯迅,當時的閱讀與之后的專業研究幾乎沒有關系。但那種普通讀者無功利目的的閱讀,是一種美好的經驗。進入了專業,也就漸漸失去,即使告別了學術工作,也未必能找回閱讀的單純性,回到那種狀態。如果說學術工作有什么代價,這就是一種。
項靜:縱觀您的文學研究和散文寫作,知識分子始終是一個不變的中心和線索,始終伴隨著您的生命體驗。您對于自己這一代知識分子與您所論及的知識分子肯定經常有縱向的對比,您能簡略地說一下嗎?自明清以來,這個群體的組成,價值追求和自我界定,肯定有變遷;“知識分子”成為一個延續的話題,其間的關聯是什么?是不是主要和您的寫作氣象緊密聯系在一起,比如您說過的追求大人格、大氣象?
趙園:古代直至近代的知識人,有自身的傳統,有知識群體的自律,有對行為規范的要求。即如清議、鄉評,再如明清士人的“省過”活動。知識群體內部嚴別君子/小人,講求“流品”,區分清/濁(如有所謂的“清流”)。在我看來,這種傳統有中斷的可能。應當說明,近代這一重要環節,我不曾涉及,因此難說“連續”。這個環節太重要了,不能省略。此外我還要說,我并不始終專注于知識分子,還涉及了北京的胡同(《北京:城與人》),“農民文化”(《地之子》)。《論小說十家》考察的主要是小說藝術,而非知識分子。給別人“一貫”的印象,主要應當因為后來的“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似乎與我的第一本學術作品《艱難的選擇》“遙相呼應”。
以知識人作為論題,當然與我的個人取向有關。追求大人格、大氣象,不是預設的目標,更像是考察活動的結果:我與一些我心儀的人物遭遇,他們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吸引了我,或許也影響了我對于學術研究的“氣象”、“境界”的追求。我的確愛用這種說法,“氣象”,“境界”。這也屬于我評估學術的重要尺度,無論對于自己還是對于他人。
項靜:社會對知識分子都有一個模糊大概的認識。薩義德的定義是,現代知識分子既不是調節者,也不是建立共識者,而是這樣一個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評意識,不愿接受簡單的處方、現成的陳腔濫調,或迎合討好、與人方便地肯定權勢者或傳統者的說法或做法。您論述中的士人還不具有這種現代意識,他們是不合時宜者,是在天崩地坼王綱解紐中形成了一種精神烏托邦而自我放逐的一群人。他們的存在形諸敘述,就有一種審美的傾向。您對他們是如何選擇的,誰可以進入考察的視野嗎?有遺民文化,就有這種文化的反面,比如“貳臣”,可能是遺民最主要的客體和精神“敵人”。“江左三大家”,您的論述中也多次引用他們的文字,再比如現代知識分子中的周作人、胡蘭成等,這種知識分子可能有另外的世界。如果研究他們的心態,也可能是更艱難的選擇,會不會有比“光明俊偉”更豐富的內容?趙園:我不熟悉薩義德的定義,較熟悉的是“社會良心”、“社會批評”之類。近代以來知識分子職業化、專業化,專業知識分子也是知識分子。
“光明俊偉”是我的向慕,對研究對象的選擇是另一回事。復雜,可以作為選擇的理由。貳臣的問題,在答《上海書評》劉明揚問中已經談到。我說自己之所以不對貳臣作專項研究,是估量了自己的能力,自知力有未逮。研究錢謙益、吳梅村、龔鼎孳,更要求古代文學的修養,而我在學養方面有明顯的缺陷。也因此對于貳臣,更多地在綜論中處理,不是有意地避難就易。在對議題的選擇上,我首先要考慮自己的能力,而非興趣。不選擇魯迅,就是如此,盡管他對我影響極大。
項靜:在選定了一個群體以后,逐漸延伸出話題,比如戾氣、士風、談兵、家人父子的生活世界等等,一個特定的群體是相對容易把握的,條分縷析,而且還會在聚焦之下產生新的話題。但是作為一個士人階層,除卻有名有姓的知識分子,還有一個龐大的下層。如何在這種以案例、個案為主的論述中,不遺漏,至少不忽視可能更接地氣的普通士人,可信地轉化為對一個群體和階層的描述?
趙園:無名無姓的知識人若沒有文本傳世,該如何研究?當然,或許可以利用另外的材料,比如明清兩代(據說主要是清代)數量龐大的家集,家譜,族譜等等。此外還有方志一類地方性文獻。但由文集入手,是我的方式。做現代文學就已經如此,由此也形成了路徑依賴。我并不勢利,僅以知名度為考量;涉及的有不少非知名之士,至少非一流人物。我們只能經由文本進入“歷史”。“普通士人”如沒有相關的文獻材料,就難以成為考察的對象。希望年輕學人在材料方面更有拓展。陳寅恪說“新問題”、“新材料”,是不刊之論。新材料固然賴有新問題的燭照,也會助成新的問題意識。
項靜:歷史研究首先必須言之有據,但您如何看待歷史寫作中的想象力?
趙園:歷史寫作的確需要想象力。但是文學性的寫作與學術寫作的不同,仍然在于是否有文獻的支持。我不能欣賞學術寫作中的信意發揮。我更愿意承接古代中國那種“傳信”、“多聞闕疑”的傳統。你如果不愿受這樣的束縛,那就去寫歷史小說。當然可以有猜測。但猜測就是猜測,不要將猜測作為“事實”敘述。盡管史料并不就可靠。或許我們永遠不能確認有些“事實”。即使如此,言之有據仍然比憑空臆造更符合學術工作的規范要求。
項靜:您可能對整體性、概括性這種詞匯比較抗拒,但分類或者概括是進入一段歷史必須的。中國地域寬廣,地域、鄉邦是非常重要的塑造人格的要素,比如鄉土知識分子,薄海型知識分子(東南沿海、吳中士人)的區分。傅山跟江南的知識分子就是不同的類型。當然,在易代之際,共同的情感結構可能同大于異。您能談談明清之際地域對于士人選擇的影響嗎?我有一個印象,南方文人可能更容易走向反抗,不知是不是如此。趙園:我其實已經作了這種比較。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我較早寫的《明清之際士人的南北論》就發表于貴刊。王夫之有地域偏見,強調北部中國的“夷化”。但北方民族的進入由北而南,南方士人更有抵抗的準備,是一個事實。
也有其他造成你那種印象的因素。比如士文化的發達程度,士人能量的聚集。這些我也都涉及了。明清易代間士大夫的選擇,除了與品質有關,也有認識上的差異。有些士大夫的降順(順即李自成的“大順”)反清,無非將前者視同照例的改朝換代,自居為“從龍”之士,開國之臣;后者則涉及夷夏之辯、春秋大義,并不就等量齊觀。當然,作為個案,只能逐一考察,不便作一概之論。
我并不抗拒“整體性”、“概括性”。學術工作分析與綜合并重,不可能排斥“整體性”的描述與概括。我“抗拒”的毋寧說是王夫之一再批評的抹煞差異的“一概之論”。作一概之論較之呈現差異更容易。當然我的個人取向也造成片段、零碎,難以摶合。得也由此,失也由此。
項靜:我想談談女性視角的問題,《易堂尋蹤》中已經有女性視角。在敘述易堂諸子的生活世界的時候,很難避開女性,尤其是他們避居山林之后。魏叔子的朋友批評他對妻子的過愛,“率以其服內太篤,待之太過,白璧微瑕,乃在于是。”妻子的地位、作用,是士大夫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我閱讀《家人父子》的時候,很自然地想到女性視角。我發現您在說明傳統社會的生活實踐與倫理原則的錯位,尤其是亂世中倫理實踐中的彈性、縫隙的時候,有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及其后對傳統社會的論述的對話關系。您似乎沒有強調陳子龍、柳如是、錢謙益的故事中陳、錢兩位夫人的視角,未將兩人作為關注對象。冒襄夫人蘇氏,是否有未被講述也不欲講述的故事?那個時代也有另類的女性故事,比如朱彝尊記述的女性獨身的故事,因為家貧五嫁的故事等等。您覺得性別視角在面對一個大部分是男性的群體時會自覺凸顯嗎,還是有意不去強化這個方面?
趙園:《家人父子》這本小書直接或潛在的對話方,女性論述外,還有婚姻史、宗族史等等,但都不深入,未能充分展開。我應當說,我本來做的就是“士大夫研究”,而不是“明清之際面面觀”。
至于“未被講述也不欲講述的故事”,只能猜測。你不能僅據猜測立論。關于陳子龍、錢謙益的夫人也是這樣。其實你想到這個問題,已經有可能接受了我的敘述中包含的提示。當然,野史、筆記中或許有我沒有經眼或不采用的說法。我的論旨畢竟在彼而不在此。古代中國女性留下的文字太少。留下的,大多被反復研究過了。在這一點上,學術對女性還算得上公平。
明清易代間的女性,是另一個題目,可以發展出另一個“明清之際”,但我不是適宜的作者。在“士大夫研究”這一框架下,無從“強化這個方面”。海外學人在這方面已經有大量的學術成果。尤其女性學者。何不去讀她們的書?
項靜:您這一代女性學者趕上了中國女性主義思潮興起的歷史過程。這個思潮對您有沒有影響?
趙園:應當承認,女性主義思潮對我影響不大。這或許與我們的早年經歷有關。我們是在一個不強調性別意識的年代里成長起來的。那個時候耳熟能詳的,是“男女都一樣”。應當說,1980年代涌入的各種“主義”,直接間接、或深或淺都對我發生過影響。我喜歡用的說法是“暗中”。暗中發生的影響也是影響。但我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意愿成為“××主義者”。
項靜:我感覺到您在材料選擇的問題上有一個矛盾和緊張,一方面是明清之際的研究基本上倚賴敘述,主要材料都是靠士大夫的個人言論,文集,書信,后人記述等等,《家人父子》也這樣。而士大夫則因所受教育,最有可能遵禮守法;同時也因所受教育,較有個性的自覺,有不受制于流俗、自主選擇的可能。關于普遍的生存狀態,常態與非常態,不能確證的部分,怎么進行考察?寫作中往往最讓人興奮的是這種矛盾之處,但是閱讀中又有不滿足的時候,就是在論述中到處是這種矛盾、不確定,讀起來會不爽快。因為許多論述都是在申明了豐富性、復雜性之后,往往就止住了,再往后是什么?
趙園:不能確證就不確證,留出余地。有幾分材料說幾分話。再往后,或許可以由別人接著說。有人批評《想象與敘述》缺乏對于明清之際歷史的“深入、可靠的整體認識”。其實《家人父子》也一樣。提供“深入、可靠的整體認識”,不是我向自己提出的任務。我不向自己提超出能力限度的任務。呈現復雜、豐富、相互矛盾的面相,揭開遮蔽,豐富對歷史的認知與想象;“再往后”,有人可能在這一基礎上向前推進,達到更高層次的認識。我所有做過的題目,都可以重做。空間很廣闊,年輕學人對此應當感到高興。
項靜:明清之際的部分士人面對時代交替,不肯認同新朝。有人強調精神生活,也有人由此親近了世俗事務,日用倫常,言論著述有了較多涉及日常倫理的部分。這也可能是知識分子接近常態的時段。您的《家人父子》對明清之際這個時段的考察涉及了許多文化命題。對這一段歷史,會不會有不斷變化的感覺和感情?
趙園:常態與非常態是相對的。明清易代前與易代中,“生活都在繼續”。我已經談到了這一點。即如祁彪佳在清軍即將打到家門的時候,仍然在經營他的寓園。不必對“板蕩”想象過度。
對于明清之際這一特定時段,我的興趣的確會隨著論題而轉移。至于感情,似乎沒有太大的變化。我在學術工作中不過多地投入感情——這或許與別人的想象不同。當然,個別題目除外。如分析“戾氣”,很難不動心。但我一向避免影射比附,也避免濫情,絕不在對象世界中扮演一個角色。我認為這不符合從事學術考察的工作倫理。
由1990年代初至今,我作為學術考察對象的這個時段,已經成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這也是從事學術工作的一份收獲,對象對于我的饋贈。這是浮光掠影地讀過一點不可能體驗到的。你的精神生活也因此而豐富。在我看來,這是件美好的事。
項靜:您在明清之際的人倫關系的重新敘述中,除了還原出彼時彼地的情景,還著力描述了士人關于人倫的理想:嚴于等差倫序卻又不無變通。這種追求,是倫理的又是審美的。父子兄弟雍雍穆穆,夫婦琴瑟和鳴,母子泄泄融融。在天崩地坼的歷史瞬間,未失粘合性的,仍然更是家庭及相關倫理。那些相延已久的經驗與世故依舊發揮著緩解壓力、維系人與人的關系的作用。我在閱讀《家人父子》的時候,時時回到當代的中國人倫日常。我發現由于對道德化的反感,似乎在私人記述中已經少有類似的表述方式。家庭是社會最基礎的單位,也是一個社會良好運轉的基礎。您在《家人父子》余論之二里,也談到了家庭對于中國社會的重要作用,以及在近現代歷史沿革之中走過的破壞之路和家庭在傳統社會內部自我瓦解的歷程。家庭倫理的重要性在今天依然是不待言說的。今天的社會有人稱之為一個無宗信(宗教信仰)的社會,個人很容易在這種空間中無所依傍走向虛無。2014年出過一本翻譯自日本的書《無緣社會》,書中說現在的日本社會是血緣、職場緣、地緣關系淡薄的社會。其實中國也在這條路上。向傳統尋求修復倫理的資源,是不是我們當前一個選項?
趙園:我在那本小書里的確寫到了某些詩意的方面,但卻無意于將傳統社會詩意化。你會注意到,我也寫到了嚴酷,像冒襄的夫人所遭遇的,像葉紹袁的妻子所遭遇的。我理解五四青年對于來自家族、宗族的壓迫的反抗。我所設目標,是補充、豐富我們關于“傳統社會”的認知,而非以此否定五四新文化運動。
在其他場合我更愿意強調的,是對“傳統”的“去蕪存菁”,尤其不以為然于提倡“孝道”,認為修復破壞了的倫理,資源應當更豐富。我們所能做的,就包括了對發生在近代以來的倫理破壞深入反思。整頓吏治,也是修復倫理的必要手段。沒有這種強有力的動作,“社會風氣”是不可能改善的。
項靜:在閱讀您的著作的過程中,下意識地會有一種簡單的比附,諷喻的想象。您對明清之際的研究背后一直有一個可以偶爾回溯的“五四”背景,20世紀五六十年代政治運動,“文革”。這些歷史似乎是一種潛在的背景。比如關于流人的論述與20世紀的政治流放,與“文革”中以“戰略疏散”為名義的大規模流動。這些歷史背景與您的論述是怎樣的關系?
趙園:只能說是背景,而且有時未必清楚地意識到。我所避免的,正有你所說的“簡單的比附”。考察歷史,我努力的,是進入,無論能做到何種程度。但你的經歷不可避免地影響你的選題,你的論述的態度等等。我的經驗是,如果你的分析足夠深入,別人自然會從中讀出更多的東西,不必刻意提示、誘導,尤其不宜煽情。
項靜:您說自己參與構造了筆下的明清之際,也就是說您所作的畢竟是一種敘述,敘述就是把事情清理出前因后果的時間線;而且您說自己的閱讀方式,興趣范圍和期待,早在新文學研究中就已經形成了。這是對于自己研究限制的一種警惕。您是1945年生人,與明清之際的士人相同的是,您也處在許多重大變革的現場,比如現代中國到當代中國的轉換。您經歷了“文革”、插隊。當代中國一些重大的變化,對學人的影響都是深刻的。您在散文中追述過您的家族的命運(《鄉土》)。作為親歷者,您敘述的歷史和作為明清之際士人言論和著述的歷史,肯定是兩種質地。您對自己親歷的歷史,準備如何敘述?尤其是在已經有了大量同代人、親歷者敘述的情況下,您如果重新敘述這段歷史,會繼續選擇知識分子作為切口嗎?主要依據什么進行敘述和需要警惕的是什么?
趙園:如果以當代史為考察對象,我關心的會是問題與現象,不限于知識分子,也不以知識分子為切入點,但仍然會大量利用知識分子的文字。與明清之際的情況類似,至今在講述當代史的,主要是知識分子。讓底層民眾開口發聲,需要條件,即如大規模的社會調研、訪談,但這可能嗎?我知道有人在努力推動這類工作,希望他們的工作不受到壓制,也希望更多年輕的知識人從事社會調查,讓盡可能多的沉默的人們開口說話。網絡空間已提供了便利,這一點并不難做到。
如果以當代史為考察對象,我只能希望在既有的基礎上向前推進:提供我自己的視角,發掘我發現的材料,提出我關心的問題,對一些現象做出我的分析與解釋。我會繼續嚴守學術考察的工作倫理,即使所寫的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學術作品。我會充分利用別人的研究成果,努力與既有的考察建立對話關系。我不會為了取悅誰而過甚其辭,也不會刻意回避或掩蓋。
項靜:您也談到自己的家族記憶,其實我本來以為您會寫一本回憶錄。學術研究畢竟要由他人的著述入手,隔著文字資料,而自己的生活對于敘述者來說可能更直接。您有沒有這樣想過?
趙園:沒有。我沒有寫回憶錄(包括精神自傳)的計劃。我以為有更值得做的事。關于家族和我個人,我已經在多篇散文中寫到了,還會在其他場合繼續寫,但不是自傳或回憶錄。尤其在日益臨近生理極限的時候,我要考量什么是更有必要做的。當然也因為我不以為自己有特別的經歷需要述說。借用別人的書名,我只是大時代中的小書生。當然小書生的命運也可能有大意義,只是我缺乏強烈的敘述的愿望罷了。
項靜:問一個關于文體的問題,這可能是您所不在意的。您說過“文體、感覺這類被別人所褒獎的東西,并非我自己所珍視的,我渴望的,是洞悉世界與體驗生命的深,我渴望體驗與傳達的深度和力度”;“在我,最猛烈的渴望,是認識這個世界,同時在對象世界中體驗自我的生命”。但我特別看重文體意識。文學評論、歷史研究的寫作,當然是由寫作者的旨趣、修養、性情決定的,但跟寫作對象的貼近,會有一個移情的過程,文體風格會不自覺地被沾染,往往要選擇一種與寫作對象相匹配的敘述語調。您理想中的研究文體是什么樣子的?或者您喜歡什么樣的寫作風格?
趙園:其實我還說了另一面,即文體的重要性(見《想象與敘述》附錄二“思想·材料·文體”)。事實上我在文體方面很挑剔,對人對己都苛刻。但也并不偏狹。比如對文學,就既喜愛魯迅,又喜愛郁達夫,也欣賞張愛玲的才情。對學術文體,我希望有內在的力度,能節制,有分寸感,不輕下斷語。或許因為做“明清之際”,會更能接受陳寅恪、陳垣、孟森那種寫作方式,不喜歡渲染,尤其不能忍受“繪聲繪色”。那更像演義。當然中西有不同的學術傳統,有不同的歷史敘述方式。這只是我的個人偏好。
對象也會“暗中”影響我的文字表述——不是有意模仿。比如寫《北京:城與人》,再如寫張愛玲。當然影響更大的,還是明清之際士人的文集。二十多年浸淫其間,不受影響是不可能的。這也屬于對象對于我的賜予。我也仍然愛讀當代文學評論。貴刊就是我愛讀的一種。比如張定浩、黃德海的文字,再如王家新論詩的文字。洪子誠先生的詩論是我必讀的。他的敏銳細膩在時間中毫無磨損,真的令人驚嘆。你問到我喜愛的文體,洪先生的文體,就是我喜愛的一種。深度之外,那是一種令人有信任感的文字。修辭立誠。現在已少有人知道“誠”為何物了。
項靜:關于寫作,您說需要不可重復的對象,同時在對象中寫入不可重復的自己。但凡不可重復,必須有大量的閱讀和對同儕寫作的觀察,以及在對象中投注不同的自己。不可重復是一個很高的寫作要求,在怎樣的意義上不重復?
趙園:我已不記得說過這樣的話。事實是,我的確不曾重復考察同一題目、同一對象,有點像“打一槍換一個地方”。這半是“為己”,為了激發活力、潛能。對象的不同,也改變與豐富著自己,使朦朧的意識清晰,不具備的知識,經由不同的題目而擴充。我不太和別人較長論短;由別人那里汲取啟發、獲取靈感是有的。不同的面向、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材料,足以使我自己發生變化。我很享受這種被學術工作豐富、自己感到日見飽滿的過程,不以為學術勞作必然會斫傷性情。
項靜:您在《自選集》自序里提到過生活在專業中的感覺,也寫到了“認同”所構成的限制:“我們至今仍在所研究的那一時代的視野中。”您還說到學術有可能是一種積極的生活方式,經由學術讀解世界,同時經由學術而自我完善。對您更重要的是,學術有可能提供“反思”賴以進行的空間。這是一種人生選擇,也主要是一種紙上的生活,您對這種生活一直非常信賴嗎,有沒有產生過虛無感?有沒有想象過其他的生活方式,比如那種實踐型的,參與性的知識分子生活?譬如您也積極寫提案,寫過一些針對現實發言的文章。
趙園:無所謂“信賴”。至今我已經可以相信,從事學術工作,是適于我的一種選擇。在不間斷的閱讀與寫作中,有過對自己的失望,也有過“學術疲勞”,卻談不上“虛無感”。為什么從事學術就要面對關于價值、意義的追問,就有可能產生“虛無感”,而其他職業則不這樣?對“以學術為業”的偏見由來已久,與對知識分子的偏見、成見不無關系。我所過的,也不盡是“紙上的生活”。使我關心甚至焦慮的問題很多。你由我的隨筆中應當可以感覺到這一點。什么是“實踐型、參與型”的?于建嶸、孫立平、溫鐵軍嗎?我佩服他們,但并不以為那種方式適于自己。他們有各自的專業,他們的參與、實踐與專業相關。我有自己的“參與”方式。除了你提到的“提案”,我已經說過的批評性隨筆外,你不以為分析“戾氣”,分析“井田”等等是參與?對“實踐”、“參與”不妨有寬泛的理解。我不將做“公知”作為目標,也不相信自以為“公知”者都能稱之為“公知”。“公知”與專業活動并非必然對立。與其有其志而無其力,不如實實在在地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
對于知識分子的偏見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甚至更早。“象牙塔”、“故紙堆”仍然被作為現成的標簽。將專業精神與現實關懷對立,也來自偏見。不必要求別人作非此即彼的選擇。明清之際“三大儒”(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都既是優秀的學者、思想家,又深度參與了他們時代的政治。將知識人類型化,而且是簡單、粗糙的分類,再進一步道德化,此優彼劣,只能更加擠壓知識人的生存空間。如果身在高校或研究機構,卻又對專業精神鄙夷不屑,我會懷疑其人在職業倫理方面出了問題——何不去選擇別的職業?
項靜:您在社會科學院工作。社科院作為一個科研機構,不同于高校和其他單位。您平時的生活是怎樣的?
趙園:我讀書,寫作;有機會就出去走走。比如今年春天,就在臺灣中研院與那里的學者交流。我偶爾會會朋友。盡管大家都老了,走動已不能像1980年代那樣頻繁,但友情依舊。甚至我能隨時向有的朋友求助。與朋友一起,我們幾乎不討論學術,談論的是中國,話題極其廣泛。即使對朋友,我也不茍同。和老伴也一樣,不討論學術,談天說地,還常常要聊聊電影。電影是我們共同的愛好。1980年代我們就曾參與電影界的活動。不再寫“觀后感”了,就邊看電視邊評論。
還有一些小朋友。和小朋友在一起話題也很廣泛,常常談的是“社會問題”。即使討論學術,也并不都是我在施教,他們也會向我提供建議或幫助。今年春天不慎骨折,《家人父子》出版后,就有小友主動“勘誤”,那本書重印時,就據此做了修訂。
項靜:您平時是怎么規劃工作時間的?是有固定的時間嗎,還是比較隨性?
趙園:我的生活秩序比較刻板。這或許因為我出生在教師家庭,自己又教過中學。如果沒有人來訪或其他事,每天的工作時間是固定的。近些年日老一日,工作時間不能延長,只能提高單位時間的效率。工作時極其專注,精力高度集中。其他時間則會在附近走走,或隨意讀點什么,比如讀社會新聞。不是在網上讀,而是讀紙媒,在這方面很老派。對于年輕人的生活方式,也盡力去了解。比如去年圣誕節,就和老伴到不太遠的“愛琴海”購物中心感受“節日氣氛”。一下子看到了那樣多的“90后”,覺得很震撼。
項靜:最后一個問題,看您寫了那么多城市文學的文章,您現在還會思考這個話題嗎,今天的城市文學好像已經跟過去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尤其在年輕一代的寫作中,地標性的表達幾乎開始有意識地淡薄,這可能是在回避前輩們刻意樹立的那種城市寫法和意識。
趙園:我已經無暇關注“城市文學”。《北京:城與人》之后,始終關心的,是城市,尤其近幾十年來以“城市改造”名義的破壞。我的周圍,有實際參與城市建設的小朋友。我認同他們的思路,關心他們的項目。這種人才,既是專業型的,又是你所說的“實踐型”、“參與型”的,將二者結合得很成功。我只能“坐而言”,他們則能“起而行”。對于這樣的朋友,我只能說“雖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編輯/張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