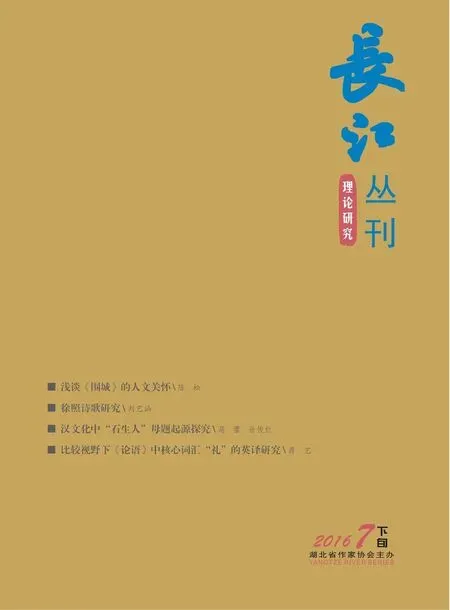略論孔子的幸福范式:德性實踐
——兼論孔子與亞里士多德幸福范式之異
嚴家強
略論孔子的幸福范式:德性實踐
——兼論孔子與亞里士多德幸福范式之異
嚴家強
孔子的幸福范式包含著入世、出世和純粹德性實踐等三個層面;亞里士多德的幸福論范式則通過探討了幸福與善、幸福與德性、幸福與快樂三種關系得出了三種幸福生活:享樂的幸福生活、政治的幸福生活、思辨的幸福生活。顯然,在亞里士多德那里思辨德性的追求是幸福的終極目的;而對孔子而言,德性的實踐性才是幸福的終極目的。
孔子 亞里士多德 幸福范式
一、孔子的幸福范式
從關于孔子思想的著作里,孔子并沒有給我們詳細而明確地論述過幸福。但是詳讀《論語》,我們能在字里行間找到孔子關于幸福的觀點,可以分為三個層面。
(一)入世
統觀《論語》,孔子對于入世改變自己和社會的觀點是明顯的,也認為人只有在實現其對于社會的意義的過程中才能實現其幸福生活。“子張學干祿。子日:‘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余,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1]“《集釋》《史記.弟子傳》:作問干祿。《讀四書大全說》:干祿之學隨世而改,于后世為征辟,為科舉。《論語補疏》:圣人以事功為重,故不禁人干祿。”[2]大多數學生到孔子身邊學習六藝,多希望獲得一種謀生之技藝,尤以做官為主,并非純粹之為知識而學知識和為道德而習道德,世俗之功利才是大多數學生追隨在孔子身邊之目的。對于孔子而言,干祿雖然不是其主要目標,但通過做官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是其人生的一個主要追求。學生通過習得六藝而安身立命,獲取世俗之事功來實現自身的人生價值,從而體驗幸福;孔子則通過游說諸侯傳達自己的政治理念,希望得到重用和推廣,繼而改變當下的社會大勢,從而實現自身的人生價值體驗幸福。當然,對于”“小人”之生活追求孔子是不提倡的,“子曰:‘君子不器。’”[3]也就是說,勞作性的、技術性的工作在孔子的眼里意義是很小的,只有“小人”才會追求,而君子都應該去謀求對整個國家的根本性變革做貢獻和努力。但不管如何,人要實現人生價值,獲得屬身之幸福,入世的事功是不可或缺的。
(二)出世
當把孔子作為一個具體的社會存在個體看待時,可以感覺到其除了推崇積極入世的生活,努力實現自我的社會價值外,依然對自我的個體價值剝落于社會價值有很多的向往。學生曾點的志向讓孔子頗為認同,“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4]由這可以看出孔子幸福論的另一個方面。在別的學生提出或高或低的政治志向的時候,曾點提出了這個頗為懸殊的答案,卻讓當時的孔子心生感慨。孔子所經歷的,胸懷大志,滿腹經綸卻不受重用,偶爾內心失落在所難免。而曾點所描述的人生“人與自然融為一體”,出離了世俗生活的種種,在追求人自然之本性的舒展中,獲得一種淡然、恬靜、愉悅的幸福體會。這何嘗不是孔子希望獲取的人生幸福?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5]由此篇可見,對于君子而言,山水、淡然、恬靜、愉悅都是值得追求的東西,而且追求的過程和結果都是善的。山水之樂的訴求,相對于孔子一直所追求的政治理想和進行的政治實踐活動,出離了世俗功利,也超脫了世俗功利,人在這樣的追求中得到莫大的釋放而實現一種本真的回歸。回歸本真的生活使人體會到萬物一體的無拘無束感、安穩寧和感,還有什么樣的生活比這種生活更吸引呢?
(三)純粹德性的實踐
安于貧困和志于求道是純粹德性實踐幸福論兩個核心的觀點:“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6]在孔子看來,一個人如果為世俗的利益生活所束縛,他不可能獲得終極的幸福;只有能夠做到自主地摒棄世俗功利幸福而追求純粹的德性生活,人才算是真正達到最終的幸福境界。純粹德性實踐幸福把精神追求提到了最為突出的地位,強調最高幸福不應該被感性欲望所束縛,進一步凸顯了人不同于一般生物的本質特征。在理性對感性的超越中,人作為道德主體的內在價值,也得到了更為充分的展示。減少感性欲望的束縛不僅是達到純粹德性實踐幸福的途徑,而且也是純粹德性實踐幸福的一個方面。相對于約制感性欲望,理性行動上的求道生活對于孔子的德性實踐幸福論更為重要,具有更為終極的意義和價值。君子“志于道”可以說是個體人生的終極追求所在,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7],可見道之重要。那么道是什么?按照《論語》所陳,也就是孔子所認為的“為而無所求”的人生理想和實際行動了。所以說個體的終極幸福,是為了行應當之事,竭盡全力,不顧己身。從德性推到其德性的實踐性,這也即是孔子幸福范式的終極目的。
二、孔子與亞里士多德幸福范式之異
(一)兩者幸福論的主體性傾向不同
孔子關于幸福的論述在主體性傾向上是偏向于情本體,也就是感性占據了重要的位置。入世的幸福論強調主體感性欲望的滿足;而出世的幸福論強調的是主體對感性欲望的超脫,但并不脫離主體的感性體驗,只是一種對于幸福生活淺層感性體驗的剝離,而回歸到身體與自然的融合上來尋求一種內心的寧靜與平和來達到超越物質欲望的幸福體驗;再次是純粹德性的實踐幸福,看似強調壓制感性欲望而回歸純粹德性的實踐才能獲取最高幸福,但依然認為主體應該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在社會責任的履行上要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實現一種對于自身情感和道德感的滿足,也就是為而無所求的情感傾訴。如果是理性主體,不可為而為之是違背其思考原則的,這也就是主體的情本體在主導主體的純粹道德實踐活動,通過這種情感性的純粹道德實踐活動來獲得最高幸福。相對比與孔子突出了主體的情本體性,亞里士多德的幸福論則更為強調主體的理本體,也即是在尋求幸福生活的主體性傾向上理性占據著更為重要的位置。亞里士多德從理性的角度先是明確了主體獲取幸福的外在條件——健康的身體和中等的財富;再從理性的角度規定了個體只有參與城邦的建設,投身于政治活動中才能獲得更高的幸福。個體在政治活動中實現對感性的制約而逐步訓練理性思維的能力,由此而使得主體的社會活動更符合政治德性的要求;最后亞里士多德認為沉思的生活是最好的生活,是最高的幸福。在德性論上,亞里士多德強調理智德性比倫理德性要高,而沉思就是理智德性在生活上的表現形式,所以按照幸福是至善的觀點,那么沉思所彰顯的理智德性就是至高的幸福的表象。
(二)兩者的幸福論在層次上有所不同
孔子的幸福論有入世幸福論、出世幸福論、純粹德性實踐幸福論等三個層面,亞里士多德的幸福論則包含了三種幸福生活:享樂的幸福生活、政治的幸福生活、思辨的幸福生活。孔子的入世幸福論既有一般世俗生活幸福的內涵,也有從事政治生活獲取幸福的內涵,所以從內容層次上涵蓋了亞里士多德關于享樂幸福和政治幸福的論述;而孔子的純粹德性實踐幸福論與亞里士多德的思辨幸福論在內容層次上也是相當;顯然,亞里士多德的幸福論中缺少了孔子所表述的出世幸福論的層次。出世之幸福,強調的是一種介于初級和最高的中間層級,是中國傳統哲人所體會到的天人合一的和諧幸福感。這種天人合一的幸福感并不是超驗的,而是可以通過感官感知與體驗的,凸顯了人的自然本性與人的社會本性的融合,它相對于簡單的感官欲望的滿足必然是更高一層的。
(三)兩者的幸福論關于“最高幸福的實現路徑”的觀點不同
孔子把純粹德性的實踐活動作為最高的幸福活動。純粹德性的實踐活動需要個體節制感性欲望,而把更為純粹的德性生活作為最高的人生訴求,而且這種純粹德性的習得應該是讓主體感到滿足和幸福的。純粹德性的實踐活動并不僅僅是停留在理性思維的層面進行轉換,實現理性對于感性的超越,而且還得再次回到現實的實踐活動中實現情感對于理性的再次超越才能真正達到最高的幸福狀態。這種從克服感性到理性,再通過情緒的力量實現從理性到實踐的轉變,就是孔子實現最高幸福的路徑,也即是孔子“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以及“為而無所求”的德性實踐理念,并通過這個理念實現自身的最高幸福。亞里士多德也把純粹的德性實踐活動作為最高的幸福活動,“既然幸福是靈魂的一種合乎完滿德性的實現活動,我們就必須考察德性的本性。”[8]純粹德性的實踐主體在自由選擇的前提下壓制感官欲望,把純粹的德性生活作為最高幸福來追求,但是這種追求不一定能讓主體感到滿足,卻可以讓主體理性得到幸福。亞里士多德把純粹德性區分為倫理德性和理智德性,倫理德性對應的是正義、節制、勇敢等實踐性的道德品質,而理智德性對應的則是思辨的理性活動。亞里士多德認為理智德性比倫理德性更高級也更自足,所以追求理智德性的思辨生活因其高級性和自足性也就成為主體最高的幸福生活。這種從感性到理性,再從理性到實踐,然后又從實踐回歸理性思辨的路徑就是亞里士多德實現最高幸福的路徑。顯而易見,孔子對于最高幸福的追求是通過實踐來獲取的,而亞里士多德對于最高幸福的追求則是通過思辨來獲取的。
[1]李澤厚.論語今讀[M].北京:三聯書店,2008:68.
[2]李澤厚.論語今讀[M].北京:三聯書店,2008:68.
[3]李澤厚.論語今讀[M].北京:三聯書店,2008:61.
[4]李澤厚.論語今讀[M].北京:三聯書店,2008:313.
[5]李澤厚.論語今讀[M].北京:三聯書店,2008:179.
[6]李澤厚.論語今讀[M].北京:三聯書店,2008:114.
[7]李澤厚.論語今讀[M].北京:三聯書店,2008:113.
[8]亞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譯.尼各馬可倫理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1102:5~6.
(作者單位:廣東機電職業技術學院)
嚴家強(1980-),男,廣東陽春人,在讀博士,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倫理學、馬克思主義理論、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