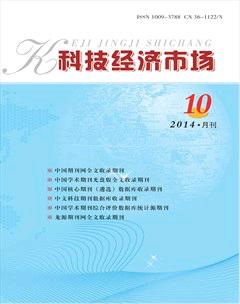ZigBee技術在煤礦井下人員定位中的研究
高永峰,吳房勝,于進杰
摘 要:近年來,我國煤礦事故頻發,煤礦安全讓人擔憂。礦井中井下人員的管理非常困難,地面工作人員不能隨時了解井下人員的分布情況及作業情況,很難進行人員定位,一旦事故發生,對井下人員的搶救非常困難。針對此問題,本文研究了一款基于 ZigBee 的井下人員無線定位系統。該系統以 CC2430/CC2431芯片為核心,利用 RSSI 定位算法,實現井下工作人員的實時定位,使地面人員隨時了解井下作業人員的分布狀態、作業情況等,使井下人員定位管理的有效性與可靠性大大提高,具有極大的市場經濟價值。
關鍵詞:ZigBee;井下;定位;RSSI算法
0 引言
本文以ZigBee 技術為核心技術,對系統開發進行了說明,并闡述了人員定位系統的總體結構圖、軟硬件系統設計方案以及上位機設計方案。最后組建了一套仿真系統,實現了實時定位的效果。本系統在 ZigBee 架構下,以 CC2430/2431 單芯片為核心,開發出的無線定位網絡系統,具有定位準確、造價低廉、便于攜帶、體積微小、結構簡單等特點,能夠很好地解決井下作業人員的位置信息問題。
1 定位原理及系統架構
1.1 定位原理
本系統采用RSSI(接收信號強度指示)定位算法,該算法測距是節點最實用的測距方法之一,不需要另加硬件設備,方法實現簡單。其工作原理是在已知發射節點信號功率的前提下,獲取接收節點的接收到的功率,利用測量接收到的信號功率來計算定位節點距參考節點的長度,并算出傳輸過程中的功率損耗,通過信號傳播衰減模型將傳輸損耗轉換成節點之間的長度,進一步采用三邊定位法測出定位節點的位置。
定位原理圖如圖1所示,CC2431無線定位引擎是以RSSI定位技術為基礎,由參考節點與定位節點兩部分構成。參考節點是已知位置的靜態節點,這個節點知道自己的位置并能夠將其位置以數據包形式通知給其他的節點。定位節點獲取參考節點發來的數據包信號,以參考節點位置坐標以及相應的RSSI值為參考,將其寫進定位引擎,然后由定位引擎計算得到自身的位置。參考節點傳輸給定位節點的數據一般由參考點的坐標參數豎直位置 Y和水平位置 X構成,而RSSI值由定位節點計算得到。
1.2 系統架構
結合礦井現場環境,采用ZigBee無線傳感網絡技術和RSSI精確定位算法,本系統的井下人員定位由監控中心、參考節點、網關節點、通信模塊以及定位節點等部分構成,井下人員定位結構體系如圖2所示。下面將對其各個模塊進行簡要說明。
(1)監控中心
定位系統中最高層是監控室的監控電腦。一般監控室與礦井的距離比較遠,所以監控電腦通常利用以太網與井下每個節點互相聯通。利用監控電腦上運行的監控軟件,監控人員可與井下每個節點實時通信,準確獲取井下各節點的設備參數、環境以及分布狀況等信息。一旦獲取到的節點數據有異常情況,監控軟件便馬上報警,監控人員可馬上通知井下工作人員,組織井下工作人員迅速撤離。監控軟件將獲取的井下各節點數據保存在數據庫中,對采集的數據進行分析與處理,對事故進行準確的預判。
(2)參考節點
定位裝置的參考節點分為主控芯片模塊、供電模塊、傳感器模塊和無線通信模塊。其中,無線通訊模塊、供電模塊以及處理器模塊與網關節點中與其對應的模塊的作用大致一樣。傳感器模塊主要采集監控區域內數據(如瓦斯氣體濃度)并將其轉化成固定格式的數據,傳輸給監控中心。
(3)網關節點
定位裝置的網關節點分為處理器模塊、供電模塊、串口模塊以及無線通信模塊。其中,處理器模塊為主控模塊,主要控制節點的功耗、同步定位執行以及ZigBee的路由協議等。
(4)通信模塊
通信模塊處于中間層,傳輸模式為無線和有線相結合。無線傳輸是利用ZigBee 無線網絡技術實現定位節點、參考節點與網關節點三者之間的通信。定位系統有線傳輸是通過串口轉換成以太網和監控主機互相連通,該模塊是將多路串口采集的數據利用以太網轉發傳輸給監控中心,或者將來自監控主機的數據通過串口轉發給網關節點。
(5)定位節點
定位節點是由主控芯片模塊、供電模塊以及無線通信模塊組成。通常是將電子標簽嵌入到礦工安全帽中或者制成便攜式卡片。
2 硬件設計
井下定位系統包括下位機與上位機兩個主要部分。上位機監控軟件安裝在地表的監控電腦上。下位機的定位系統利用CC2430模塊實現。下位機和上位機之間通過以太網進行連接。CC2430是全球第一個滿足ZigBee技術標準的2.4GHz射頻芯片,該芯片兼容IEEE802.15.4 協議標準,內嵌51系列單片機的核,并將ZigBee RF前端、存儲器以及微控制器集于一身。ZigBee 標準規定了其無線網絡包括定位節點、參考節點以及網關節點三種設備,其中,網關節點是網絡的協調器,是無線定位系統的核心,CC2430網關射頻模塊電路如圖3所示。
3 軟件設計
網關是整個ZigBee無線網絡的核心主要完成信息的無線接收和發送;無線傳感器網絡的建立;接收上位機發送來的數據,并轉發給各個節點,故本文主要介紹網關的軟件設計,網關的工作流程如圖4所示。網關利用以太網與地表上的監控主機相連。首先接收由監控主機提供各個節點的配置信息,并將接收到的數據傳輸給網絡中相應的節點實現初始化;另外,接收各節點反饋的有效信息并利用以太網傳送到地表上的監控主機。管理人員通過監控主機能夠掌握每個工作人員的具體位置以及每個節點的性能狀況。
4 系統測試
為了完善的開發和設計完整的井下人員定位系統,本文建立了一個簡單的無線定位仿真系統,并進行了定位系統的測試,本系統下位機的開發軟件采用 IAR Embedded Workbench 嵌入式集成開發軟件。
本系統仿真系統由5 個CC2430模塊組成,其中包含網關1個、參考節點4個;1 個CC2431模塊作為盲節點。CC2430/ CC2431模塊實物圖如圖5所示。為了正常的運行和調試 IAR 軟件所編寫的程序,該仿真系統采用的ZigBee 調試器為SmartRF04EB 調試器。
在系統啟動之前前,首先要在電腦上安裝協議棧ZStack-1.4.2-1.1.0,然后用IAR軟件打開已經編好的程序編譯,利用USB線纜將主機與SmartRF04EB協議分析器連接,然后利用分析器的JTAG接口用專用線纜連接到CC2430模塊上,將程序燒錄到模塊芯片中,再進行參數的配置,實現系統的搭建其中IAR編程界面如圖6所示。
上位機采用美國TI公司的Z-Location Engine監控軟件對每個節點測試,打開實驗平臺的定位軟件,使用Chipcon公司提供的定位引擎對下位機進行測試,實驗結果如圖7所示。
參考文獻:
[1]李燕濤. 基于ZigBee的井下人員定位系統的研究[J]. 西安科技大學碩士論文,2012(6).
摘 要:近年來,我國煤礦事故頻發,煤礦安全讓人擔憂。礦井中井下人員的管理非常困難,地面工作人員不能隨時了解井下人員的分布情況及作業情況,很難進行人員定位,一旦事故發生,對井下人員的搶救非常困難。針對此問題,本文研究了一款基于 ZigBee 的井下人員無線定位系統。該系統以 CC2430/CC2431芯片為核心,利用 RSSI 定位算法,實現井下工作人員的實時定位,使地面人員隨時了解井下作業人員的分布狀態、作業情況等,使井下人員定位管理的有效性與可靠性大大提高,具有極大的市場經濟價值。
關鍵詞:ZigBee;井下;定位;RSSI算法
0 引言
本文以ZigBee 技術為核心技術,對系統開發進行了說明,并闡述了人員定位系統的總體結構圖、軟硬件系統設計方案以及上位機設計方案。最后組建了一套仿真系統,實現了實時定位的效果。本系統在 ZigBee 架構下,以 CC2430/2431 單芯片為核心,開發出的無線定位網絡系統,具有定位準確、造價低廉、便于攜帶、體積微小、結構簡單等特點,能夠很好地解決井下作業人員的位置信息問題。
1 定位原理及系統架構
1.1 定位原理
本系統采用RSSI(接收信號強度指示)定位算法,該算法測距是節點最實用的測距方法之一,不需要另加硬件設備,方法實現簡單。其工作原理是在已知發射節點信號功率的前提下,獲取接收節點的接收到的功率,利用測量接收到的信號功率來計算定位節點距參考節點的長度,并算出傳輸過程中的功率損耗,通過信號傳播衰減模型將傳輸損耗轉換成節點之間的長度,進一步采用三邊定位法測出定位節點的位置。
定位原理圖如圖1所示,CC2431無線定位引擎是以RSSI定位技術為基礎,由參考節點與定位節點兩部分構成。參考節點是已知位置的靜態節點,這個節點知道自己的位置并能夠將其位置以數據包形式通知給其他的節點。定位節點獲取參考節點發來的數據包信號,以參考節點位置坐標以及相應的RSSI值為參考,將其寫進定位引擎,然后由定位引擎計算得到自身的位置。參考節點傳輸給定位節點的數據一般由參考點的坐標參數豎直位置 Y和水平位置 X構成,而RSSI值由定位節點計算得到。
1.2 系統架構
結合礦井現場環境,采用ZigBee無線傳感網絡技術和RSSI精確定位算法,本系統的井下人員定位由監控中心、參考節點、網關節點、通信模塊以及定位節點等部分構成,井下人員定位結構體系如圖2所示。下面將對其各個模塊進行簡要說明。
(1)監控中心
定位系統中最高層是監控室的監控電腦。一般監控室與礦井的距離比較遠,所以監控電腦通常利用以太網與井下每個節點互相聯通。利用監控電腦上運行的監控軟件,監控人員可與井下每個節點實時通信,準確獲取井下各節點的設備參數、環境以及分布狀況等信息。一旦獲取到的節點數據有異常情況,監控軟件便馬上報警,監控人員可馬上通知井下工作人員,組織井下工作人員迅速撤離。監控軟件將獲取的井下各節點數據保存在數據庫中,對采集的數據進行分析與處理,對事故進行準確的預判。
(2)參考節點
定位裝置的參考節點分為主控芯片模塊、供電模塊、傳感器模塊和無線通信模塊。其中,無線通訊模塊、供電模塊以及處理器模塊與網關節點中與其對應的模塊的作用大致一樣。傳感器模塊主要采集監控區域內數據(如瓦斯氣體濃度)并將其轉化成固定格式的數據,傳輸給監控中心。
(3)網關節點
定位裝置的網關節點分為處理器模塊、供電模塊、串口模塊以及無線通信模塊。其中,處理器模塊為主控模塊,主要控制節點的功耗、同步定位執行以及ZigBee的路由協議等。
(4)通信模塊
通信模塊處于中間層,傳輸模式為無線和有線相結合。無線傳輸是利用ZigBee 無線網絡技術實現定位節點、參考節點與網關節點三者之間的通信。定位系統有線傳輸是通過串口轉換成以太網和監控主機互相連通,該模塊是將多路串口采集的數據利用以太網轉發傳輸給監控中心,或者將來自監控主機的數據通過串口轉發給網關節點。
(5)定位節點
定位節點是由主控芯片模塊、供電模塊以及無線通信模塊組成。通常是將電子標簽嵌入到礦工安全帽中或者制成便攜式卡片。
2 硬件設計
井下定位系統包括下位機與上位機兩個主要部分。上位機監控軟件安裝在地表的監控電腦上。下位機的定位系統利用CC2430模塊實現。下位機和上位機之間通過以太網進行連接。CC2430是全球第一個滿足ZigBee技術標準的2.4GHz射頻芯片,該芯片兼容IEEE802.15.4 協議標準,內嵌51系列單片機的核,并將ZigBee RF前端、存儲器以及微控制器集于一身。ZigBee 標準規定了其無線網絡包括定位節點、參考節點以及網關節點三種設備,其中,網關節點是網絡的協調器,是無線定位系統的核心,CC2430網關射頻模塊電路如圖3所示。
3 軟件設計
網關是整個ZigBee無線網絡的核心主要完成信息的無線接收和發送;無線傳感器網絡的建立;接收上位機發送來的數據,并轉發給各個節點,故本文主要介紹網關的軟件設計,網關的工作流程如圖4所示。網關利用以太網與地表上的監控主機相連。首先接收由監控主機提供各個節點的配置信息,并將接收到的數據傳輸給網絡中相應的節點實現初始化;另外,接收各節點反饋的有效信息并利用以太網傳送到地表上的監控主機。管理人員通過監控主機能夠掌握每個工作人員的具體位置以及每個節點的性能狀況。
4 系統測試
為了完善的開發和設計完整的井下人員定位系統,本文建立了一個簡單的無線定位仿真系統,并進行了定位系統的測試,本系統下位機的開發軟件采用 IAR Embedded Workbench 嵌入式集成開發軟件。
本系統仿真系統由5 個CC2430模塊組成,其中包含網關1個、參考節點4個;1 個CC2431模塊作為盲節點。CC2430/ CC2431模塊實物圖如圖5所示。為了正常的運行和調試 IAR 軟件所編寫的程序,該仿真系統采用的ZigBee 調試器為SmartRF04EB 調試器。
在系統啟動之前前,首先要在電腦上安裝協議棧ZStack-1.4.2-1.1.0,然后用IAR軟件打開已經編好的程序編譯,利用USB線纜將主機與SmartRF04EB協議分析器連接,然后利用分析器的JTAG接口用專用線纜連接到CC2430模塊上,將程序燒錄到模塊芯片中,再進行參數的配置,實現系統的搭建其中IAR編程界面如圖6所示。
上位機采用美國TI公司的Z-Location Engine監控軟件對每個節點測試,打開實驗平臺的定位軟件,使用Chipcon公司提供的定位引擎對下位機進行測試,實驗結果如圖7所示。
參考文獻:
[1]李燕濤. 基于ZigBee的井下人員定位系統的研究[J]. 西安科技大學碩士論文,2012(6).
摘 要:近年來,我國煤礦事故頻發,煤礦安全讓人擔憂。礦井中井下人員的管理非常困難,地面工作人員不能隨時了解井下人員的分布情況及作業情況,很難進行人員定位,一旦事故發生,對井下人員的搶救非常困難。針對此問題,本文研究了一款基于 ZigBee 的井下人員無線定位系統。該系統以 CC2430/CC2431芯片為核心,利用 RSSI 定位算法,實現井下工作人員的實時定位,使地面人員隨時了解井下作業人員的分布狀態、作業情況等,使井下人員定位管理的有效性與可靠性大大提高,具有極大的市場經濟價值。
關鍵詞:ZigBee;井下;定位;RSSI算法
0 引言
本文以ZigBee 技術為核心技術,對系統開發進行了說明,并闡述了人員定位系統的總體結構圖、軟硬件系統設計方案以及上位機設計方案。最后組建了一套仿真系統,實現了實時定位的效果。本系統在 ZigBee 架構下,以 CC2430/2431 單芯片為核心,開發出的無線定位網絡系統,具有定位準確、造價低廉、便于攜帶、體積微小、結構簡單等特點,能夠很好地解決井下作業人員的位置信息問題。
1 定位原理及系統架構
1.1 定位原理
本系統采用RSSI(接收信號強度指示)定位算法,該算法測距是節點最實用的測距方法之一,不需要另加硬件設備,方法實現簡單。其工作原理是在已知發射節點信號功率的前提下,獲取接收節點的接收到的功率,利用測量接收到的信號功率來計算定位節點距參考節點的長度,并算出傳輸過程中的功率損耗,通過信號傳播衰減模型將傳輸損耗轉換成節點之間的長度,進一步采用三邊定位法測出定位節點的位置。
定位原理圖如圖1所示,CC2431無線定位引擎是以RSSI定位技術為基礎,由參考節點與定位節點兩部分構成。參考節點是已知位置的靜態節點,這個節點知道自己的位置并能夠將其位置以數據包形式通知給其他的節點。定位節點獲取參考節點發來的數據包信號,以參考節點位置坐標以及相應的RSSI值為參考,將其寫進定位引擎,然后由定位引擎計算得到自身的位置。參考節點傳輸給定位節點的數據一般由參考點的坐標參數豎直位置 Y和水平位置 X構成,而RSSI值由定位節點計算得到。
1.2 系統架構
結合礦井現場環境,采用ZigBee無線傳感網絡技術和RSSI精確定位算法,本系統的井下人員定位由監控中心、參考節點、網關節點、通信模塊以及定位節點等部分構成,井下人員定位結構體系如圖2所示。下面將對其各個模塊進行簡要說明。
(1)監控中心
定位系統中最高層是監控室的監控電腦。一般監控室與礦井的距離比較遠,所以監控電腦通常利用以太網與井下每個節點互相聯通。利用監控電腦上運行的監控軟件,監控人員可與井下每個節點實時通信,準確獲取井下各節點的設備參數、環境以及分布狀況等信息。一旦獲取到的節點數據有異常情況,監控軟件便馬上報警,監控人員可馬上通知井下工作人員,組織井下工作人員迅速撤離。監控軟件將獲取的井下各節點數據保存在數據庫中,對采集的數據進行分析與處理,對事故進行準確的預判。
(2)參考節點
定位裝置的參考節點分為主控芯片模塊、供電模塊、傳感器模塊和無線通信模塊。其中,無線通訊模塊、供電模塊以及處理器模塊與網關節點中與其對應的模塊的作用大致一樣。傳感器模塊主要采集監控區域內數據(如瓦斯氣體濃度)并將其轉化成固定格式的數據,傳輸給監控中心。
(3)網關節點
定位裝置的網關節點分為處理器模塊、供電模塊、串口模塊以及無線通信模塊。其中,處理器模塊為主控模塊,主要控制節點的功耗、同步定位執行以及ZigBee的路由協議等。
(4)通信模塊
通信模塊處于中間層,傳輸模式為無線和有線相結合。無線傳輸是利用ZigBee 無線網絡技術實現定位節點、參考節點與網關節點三者之間的通信。定位系統有線傳輸是通過串口轉換成以太網和監控主機互相連通,該模塊是將多路串口采集的數據利用以太網轉發傳輸給監控中心,或者將來自監控主機的數據通過串口轉發給網關節點。
(5)定位節點
定位節點是由主控芯片模塊、供電模塊以及無線通信模塊組成。通常是將電子標簽嵌入到礦工安全帽中或者制成便攜式卡片。
2 硬件設計
井下定位系統包括下位機與上位機兩個主要部分。上位機監控軟件安裝在地表的監控電腦上。下位機的定位系統利用CC2430模塊實現。下位機和上位機之間通過以太網進行連接。CC2430是全球第一個滿足ZigBee技術標準的2.4GHz射頻芯片,該芯片兼容IEEE802.15.4 協議標準,內嵌51系列單片機的核,并將ZigBee RF前端、存儲器以及微控制器集于一身。ZigBee 標準規定了其無線網絡包括定位節點、參考節點以及網關節點三種設備,其中,網關節點是網絡的協調器,是無線定位系統的核心,CC2430網關射頻模塊電路如圖3所示。
3 軟件設計
網關是整個ZigBee無線網絡的核心主要完成信息的無線接收和發送;無線傳感器網絡的建立;接收上位機發送來的數據,并轉發給各個節點,故本文主要介紹網關的軟件設計,網關的工作流程如圖4所示。網關利用以太網與地表上的監控主機相連。首先接收由監控主機提供各個節點的配置信息,并將接收到的數據傳輸給網絡中相應的節點實現初始化;另外,接收各節點反饋的有效信息并利用以太網傳送到地表上的監控主機。管理人員通過監控主機能夠掌握每個工作人員的具體位置以及每個節點的性能狀況。
4 系統測試
為了完善的開發和設計完整的井下人員定位系統,本文建立了一個簡單的無線定位仿真系統,并進行了定位系統的測試,本系統下位機的開發軟件采用 IAR Embedded Workbench 嵌入式集成開發軟件。
本系統仿真系統由5 個CC2430模塊組成,其中包含網關1個、參考節點4個;1 個CC2431模塊作為盲節點。CC2430/ CC2431模塊實物圖如圖5所示。為了正常的運行和調試 IAR 軟件所編寫的程序,該仿真系統采用的ZigBee 調試器為SmartRF04EB 調試器。
在系統啟動之前前,首先要在電腦上安裝協議棧ZStack-1.4.2-1.1.0,然后用IAR軟件打開已經編好的程序編譯,利用USB線纜將主機與SmartRF04EB協議分析器連接,然后利用分析器的JTAG接口用專用線纜連接到CC2430模塊上,將程序燒錄到模塊芯片中,再進行參數的配置,實現系統的搭建其中IAR編程界面如圖6所示。
上位機采用美國TI公司的Z-Location Engine監控軟件對每個節點測試,打開實驗平臺的定位軟件,使用Chipcon公司提供的定位引擎對下位機進行測試,實驗結果如圖7所示。
參考文獻:
[1]李燕濤. 基于ZigBee的井下人員定位系統的研究[J]. 西安科技大學碩士論文,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