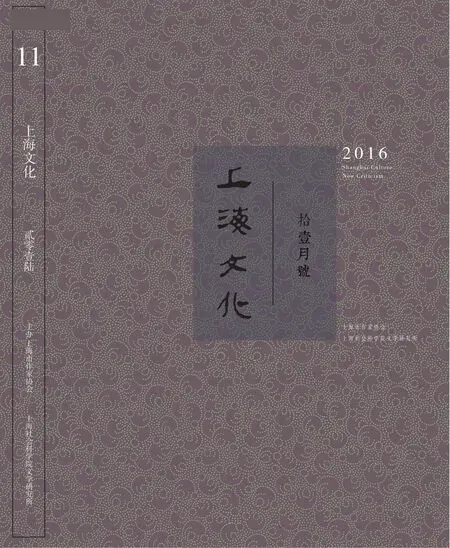伊麗莎白·畢肖普*
海倫·文德勒 葉 美 譯
?
伊麗莎白·畢肖普*
海倫·文德勒 葉 美 譯
畢肖普詩集《地理學Ⅲ》中的詩歌,其引人注目的品質是在家庭生活和陌生性之間持續地情感轉換。換任何一位詩人,這種交替行為都會被看作是有爭議的,但畢肖普能做到自然而然而非刻意區分,凝神注視而非故意取舍。所以盡管她的旅行詩歌總是帶給我們異國情調之感,但其實陌生感并不是只依靠書寫異國情調才能獲得,同樣要獲得親切感不必一定要寫此時此地。(因為在她的詩歌中,熟悉的事物經常用房子、家庭、愛人、家來命名,所以對畢肖普而言,實際上她關心的是家庭生活而不是那些熟悉的事物。因為反常事件其實很容易發生在家庭生活內部,甚至會最令人不安地出現在客廳的壁爐旁邊,所以同樣可以說談論陌生性比談論異國情調更真實可信)。
為了展示其詩歌中家庭事物和陌生性完美結合時相互之間是如何滲透的,必須回溯詩集《旅行問題》中的一些詩作。《六節詩》中的構成元素幾乎完全一目了然——房屋、祖母、奇跡小火爐、歷書。但眼淚這一陌生元素最終使整個房屋顯得怪異。盡管祖母藏起眼淚,只說了句:“該喝茶了”,孩子還是感覺到了她噙著的淚花,并將它們通感到各處——茶壺跳動的水珠,屋頂的雨,祖母的杯中茶。
……而孩子
正凝神茶壺上微小堅硬的淚珠
如屋頂滂沱的雨水
在熾熱的黑色火爐上瘋狂起舞。
……歷書
在孩子和老祖母頭上
懸停,半張著翅膀
她的茶杯溢滿深棕色的淚水。
孩子對世界的感受只呈現在他的畫作里:一棟線條僵硬的房子。(我說“她”,是從詩作里的親屬關系來推測,其實孩子的性別不確定)。孩子需要表達出她感受到的眼淚,所以她在畫中“添上……一個人,胸前扣著紐扣,仿佛完美的淚珠” ,當“小月亮們從歷書的書頁間/淚珠似的,滑落到孩子/在屋前精心布置的花床中時。”
《六節詩》結尾的三行詩,聚集了這幅拼貼畫的所有元素:
該種植眼淚了,歷書說。
朝向神奇的火爐,祖母俯身歌唱
而孩子畫下另一座隱秘的房屋。
孩子父母的缺席是這些眼淚心照不宣的原因,雖然表達含蓄卻一目了然。因為祖母的所有言行,孩子的一直沉默,神奇小火爐勇敢的歡唱,房屋的冰冷難耐,和其冷清的氛圍都無疑代表了孩子家庭生活經驗中反常事件的存在——反常這個詞,尤其對孩子有效。當詩中開始出現家庭住宅時,所有事情都不應該不可捉摸。而事實是家庭住宅經常令人不可捉摸,沒有什么比發生在家庭生活內部更叫人費解的了,這給畢肖普提供了反復抒寫的詩歌主題之一。
書寫家庭生活使畢肖普的詩歌表達非常特別。當她明白自己已經長大成人,她也常常像孩子一樣說話。《六節詩》就是一個典型例子,詩中她以永恒的孩童式的口吻講述了一則故事。不僅采用寓言式的措詞,而且讓人物關系保持固定,尤其是排列式的結尾,歷書、祖母和孩子三者不變的身份猶如一副中世紀的繪畫,其中歷書代表支配一切的宿命,祖母代表了老派規則,孩子代表青年信仰。最后三行不動聲色地記錄了悲傷、歌唱、宿命、奇跡的同時存在,可是盡管它們的關系是并列且“地位平等”,但最終強調的卻是不可捉摸的事物,即使發生在家庭生活內部,也會使這首詩成功地并入了陌生性的軌道。
詩集《旅行問題》中最后一首從另外的角度打破了平衡,最終朝向家庭生活。這首取名為《加油站》的詩歌一開始看起來毫無美感,至少在這位敘述的目擊者眼里。加油站骯臟、浸滿油漬、彌漫著油味;父親一身臟西裝;他的兒子們蓬頭垢面;一切都看起來“骯臟透頂”;甚至有“一條黏糊糊的狗”。敘述者,雖然內心懷著“高雅人的恐懼”,但卻不能從不斷涌現的生活細節中移開視線,因為這里雖然是個加油站,卻非常不可理喻地讓人感受到家庭生活的樂趣。“他們住在加油站嗎?”講述者疑惑不解,竟然看見門廊處有“一套破爛,浸滿/油漬的柳條家具”,狗“非常舒服地”躺在草席沙發上,連環漫畫,鋪坐墊的小凳和“一盆碩大的多毛秋海棠”。我們發現自己對這個最沒有希望的地方產生了幻想,使人心懷對家庭生活的幸福憧憬,這憧憬是作為意義的證明,作為“愛”的證據而出現的。是否我們的宗教信仰只是我們安居樂業天性的一種表達?
這些毫無用處的植物
這些不合時宜小矮凳
哦,哦,上面還鋪著坐墊
為什么,它們原本不該出現在這里……
坐墊曬著某人的刺繡手藝。
某人澆灌后植物才繁茂,明亮
或粘上了油跡的緣故,也不是不可能
某人精心地擺放了金屬罐
看起來整齊地一字排開
這樣上面字母可以連著讀出來
埃索-索-索-索
它們一直排到轟響的機動車那里
某人愛著我們大家。
從形而上學方面發出疑問并從神學方面來討論,詩歌表達了塵世中人類“可怕但愉快的”行為之一就是要馴化周遭環境,即使是像加油站或是漆著“跳動玫瑰花蕾的”巴西卡車這樣純粹的工業機械之地。
家庭生活容易因為遭遇死亡而陷入危機。一般來說,家庭成員是親密的不可分割的整體;美國文學中寫家庭生活的精髓之作是《雪困》。當死亡入侵家庭內部,古老習俗規定尸體要先停放家中,此時死亡在強迫家庭成員屈服它蠻橫的權威。史蒂文斯的《冰激凌皇帝》將家里冰冷、緘默的尸體與葬禮上烤肉行為荒誕地聯系起來,可以說,當烤肉味香飄進廚房時,人們在死者面前大吃大喝的原始沖動被看作沒有同情心,粗魯和野蠻的,即使是在我們已“文明化了的”社會里。畢肖普《新斯科舍省的第一次死亡》,還是孩子的詩人對家中的會客廳里“小表親阿瑟”棺材進行了一番聯想:
寒冷,寒冷的會客廳
母親擺放阿瑟
在膠版復印品下
那里有愛德華,威爾士王子,
亞力桑德拉公主
喬治國王和瑪麗皇后。
再下面的桌子
站著一枚被阿瑟叔叔
即阿瑟的父親
打中并制作成的潛鳥標本。
孩子無法追憶死亡的全部細節。但卻對棺材記憶如新,熟悉的事物在她眼里都開始變形:潛鳥標本活了過來,他的沉默看起來是自愿的,它的紅玻璃眼珠在觀察:
自從阿瑟叔叔的一粒
子彈射中了它,
它不曾說一句話。
它保持自己的原則,沒有譴責人類……
阿瑟的棺木猶如
沾滿糖霜的小蛋糕,
被紅眼睛的潛鳥從覆滿積雪的
冰凍的湖面直直地盯視。
成人們串通一氣,說與死者的交流仍舊可能,他們吩咐孩子說:“和小表親阿瑟/說再見,”要求其將一束山谷百合送到死者手心。孩子參加了這場荒誕的表演,她先是想象會客廳的寒氣使它成為杰克·弗羅斯特的領地,當他畫“加拿大楓葉林”時也在畫阿瑟的紅頭發,接下來想象膠版復印品中的“一對豪華的皇家情侶”已經“邀請了阿瑟作為/宮廷最小的侍衛。”阿瑟的死亡帶來了會客廳中彌漫著壓抑情緒,這導致孩子建造了由客廳、棺材、尸體、膠版復印品、潛鳥、霜人、楓葉林和百合組成的格式塔。孩子的壓力過大,以至于懷疑和沮喪感控制不住地涌上心頭——不是擔心他最終的命運,哦不,孩子確信阿瑟變成了“宮廷最小的侍衛” ,那是一個令人困惑的,半是宮殿,半是天堂的,人丁興旺的大家族;相反,她的困惑是他怎么到達那里。
但阿瑟怎樣才能抵達那里,
緊握一束小百合的他
眼睛閉得緊緊地
外面道路都深埋雪中?
家庭生活是脆弱的,它最終會被死亡帶來的陌生感擊潰。死亡來臨之時,甚至即便在它發生之后,對陌生環境的馴化工作仍在繼續,這一切都是超越家庭生活保證的替代,某些人堅信我們真的在這個世界上,在我們母親的房屋里,堅信“某人愛著我們大家”。在家庭生活以一種形式遭到打擊后,用另一種形式重建它的努力就已經開始。畢肖普詩歌中對死亡的定義是將要放棄馴化世界,然而再次試圖重建更多形式的親密感,反之,對生命的定義就存在于從陌生化到親密感,從未知到已知,從隔膜到鐘愛的情感轉化中。
任何家庭生活都不安全。生命的中途我們就可能遭遇死亡,所以在畢肖普的詩歌中,恰恰就是在熟悉的事物中間,我們感覺越熟悉的事物其實越神秘。這種隔膜帶來的痛楚,就是《在會診室》的主題,其發生在看似安全的家庭生活內部。1918年,一個七歲孩子,一邊在等待牙醫診室里的姑媽,一邊讀著《國家地理雜志》。場景平淡無奇:“全是成年人/御寒套鞋和長大衣,/燈光和雜志,”但兩件事情使孩子焦躁不安,首先是雜志上的一幅畫:“裸體黑女人們脖子上/成圈地纏上金屬線/像燈泡卡口。/她們的胸令人驚恐。”第二個是嘴里突然發出“哎噢!疼痛的叫喊/—和姑媽康蘇埃拉聲音一樣”。孩子頭暈目眩,感覺自己的喊聲是以“和其他家庭成員相似的聲線”發出的,并馬上意識到作為人類族群之一,她和她們相比的獨特性和共性何在。
但我感覺:你是一個我,
你是其中的一個伊麗莎白,
你是她們中的一員。
為什么你也是其中的一員呢?
我和她們多么相似——
皮靴,手臂,我感覺我有著
和其他家庭成員相似的聲線,甚至
還和《國家地理雜志》上
那些嚇人,松垮垮的乳房相似—
就是它們把我們連在一起
或昭示著我們就是一個整體嗎?
在《有一個孩子向前走去》這首詩里,惠特曼也談及了一個相似的瞬間,也充滿了形而上學的疑惑:
……那種真實感,那種唯恐最后成為泡影的憂慮,
那些白天黑夜的懷疑,那些奇怪的猜測和設想,猜測那現象是否屬實,
或者全是些斑點和閃光
那些大街上熙熙攘攘的男女,他們不是些閃光和斑點又是什么?
這是惠特曼的風格,瞬間的迷失后他讓自己沉浸在海洋和天空的自然世界。這也同樣是畢肖普的風格,在候診室滑向“黑色,洶涌的層層起伏的/波浪下方”之后,她也返回一成不變的清醒的現實,盡管這現實的選擇被感覺所支配。
戰爭在繼續,外面是
伍切斯特,馬薩諸塞州,
是夜晚,是積雪和寒冷,
是1918年二月的
第五天。
孩子渴望在自己的世界里掌握最不熟悉的事物,渴望在候診室中把《國家地理雜志》中的異域事物與身旁人們的膝蓋、褲子和襯衫聯系起來,通過這種方法她把令人恐懼的陌生感和熟悉事物——她自己、姑姑和“家庭聲音”共同編織在一起。最后,野蠻人會被馴化了嗎?她自己會變成了不可知論者了嗎?同時發生的這兩件事,壓垮了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她感到渾身癱軟。語言辜負了六歲的孩子。“啊——我說不出任何/話來——多么‘令人難以置信。’”
這種輕描淡寫其實每個字都鏗鏘有力,畢肖普在詩歌中常常這樣做。事實是作為孩子的她,被意外事件所震驚,“熟悉”和“陌生”這兩個概念已經丟失了所有意義。“安德森夫人的瑞典孩子,”史蒂文斯說,“也許也曾是個德國人或西班牙人”。卡洛斯·德拉蒙德·德·安德拉德的一首詩歌曾被畢肖普翻譯成英文(他的三音步詩體可能影響了《在會診室》):
Mundo mundo vasto mundo,
Se eu me chamasse Raimundo
Seria uma rima, nao seria uma solucao
如果一個人的名字和宇宙的名字同韻,就像“Raimundo”與“mondo”同韻,這就會在自我和世界之間出現一種和諧,并且把世界馴化成適合人類居住的行為好像就是可能的。但德拉蒙德說,它只是一個韻,不是一種解決辦法。《在會診室》中的孩子發現她不理解這個世界,她太年輕了,不能用意志控制世界或是用愛馴化世界,她滑入了黑暗的深淵。
在《詩》這首詩中(“大約和舊版鈔票一般大小”)詩人無心地盯視著他叔祖父創作的一副小畫,并且開始了對世界馴化這個主題的另一番思考。她無心地盯視——也就是,直到她相信自己曾住在畫中的風景的那一刻的到來:“天堂,我認出了這個地方,我知道它!”,在這首杰作中,“這個地方”被描寫了三遍。第一遍的語言形象,精確、激昂、風趣:我們認為,這種描述是純粹的視覺快樂,相對來說是客觀敘述。(“這一定是新斯科舍;只有那/可以看見三角木房/漆著笨拙的棕色暗影”)。下面的詩句就是對風景的第一遍描述:
榆樹林,低矮的山坡,一個細瘦的教堂尖塔
——那是一抹藍灰色——會不是嗎?前景中
一群細小的牛在水草上
每只牛刷刷兩筆,但一定是牛;
兩個微小的白鵝在藍色的水里
背靠著背都在吃草,一個斜斜的枝條
上面站著一只野生鳶尾,渾身白色兼黃,
從顏料管中擠出來的顏色鮮亮的線條
空氣新鮮,寒冷;那是早春的清冷
透明得像是塊玻璃;半寸藍天空
下面是青灰色的暴風云。
然后敘述被相認中斷——“天堂,我知道它!”,隨之而來的是雙重的變形:思緒沖出了畫框,把畫中的場景拋入一個背景久遠的、記憶中的鄉村風景,并且以一個本地人的口吻說出畫中的件件事物的名字。
天堂!我認出這里,我知道它。
這是后面——我幾乎記起了農場的名字。
谷倉位于草地后方。就在那里
輕輕一抹的鈦白色。塔尖的陰影處,
那里畫筆輕柔,人眼幾乎看不見的地方
一定是長老會教堂。
那是格萊斯皮夫人的房子嗎?
那些特別的鵝和牛
都在我的時間之前大方地生活著。
雖然主體和繪畫之間存在著聯系,不過我們還是把它當做一幅畫,被認出其價值的人所描述——這里鈦白色輕輕一抹,那里精心地寥寥幾筆。并且場景一直向后移動——那些屬于另外一個時代的鵝和牛。但是在詩歌結尾時詩人將自己和畫家聯系起來。他們倆都愛上了地球上這個微不足道的一角;它曾在他們的生活中存在過,在他們的記憶和藝術中存在過。
藝術“模仿生活”并且藝術就是生活
生活和對生活的記憶被壓縮得多么厲害
他們彼此相互侵占融合,難以區分?
生活和對生活的記憶已經漸行漸遠
朦朧,在一塊布里斯托爾畫板上
朦朧,但多么生動,細節多么打動人心
——我們擁有的自由越小,
我們對塵世的信賴越少。不會多。
在遙遠的世界某處,有一小塊土地曾被居住,被馴養、被記憶、被想象、被紀念,甚至因此而永垂不朽。稱永垂不朽是因為在第三遍描述這幅畫時,不僅僅是用眼睛來觀察——不管是用鑒賞家的眼睛或是用懷念往昔的當地居住者的眼睛——而是被心靈所照見,因曾經在其中生活過而有所觸動。不再有任何提及畫筆,筆刷或顏料或優質木板的文字;我們身心已經完全融進場景中。
……不會多。
說到我們和他們共同
生活場景:嚼草的奶牛
挺拔,顫抖的鳶尾花,河水
依舊因春天的融雪而轟響,
尚未砍伐的榆樹,還有那些鵝。
盡管在場景中,件件事物給人的深刻印象部分是因為用了現在分詞,(嚼草的奶牛、顫栗的鳶尾花、轟響的河水),同時也因為對前面章節的名字的反復重提(奶牛、鳶尾花),現在去除了“染料的”修飾,(“每只牛刷刷兩筆”,“從顏料管擠出”),從前面兩次重復的“融雪后暴漲”的“河水”,尤其是從“尚未砍伐的榆樹”的預言中。最不可能的是,“尚未砍伐”這個詞那時拒絕在記憶的場景中讓身心全部投入其中。這個既是孩子也是詩人曾經生活過的世界,現在看起來只是一個為一幕劇草草準備的舞臺布景——戲劇演出一旦結束,背景就會被拆除,幻覺也跟著消失。這首詩已經把讀者帶入了我們稱之馴化的過程,首先通過對奇特的地形的相認,然后對熟悉事物的相認,再后來情感由陌生變成鐘愛,最后把讀者從已陷入的親密感中解放出來。馴化隨之而來,幾乎不可避免,那些已被摧毀的事物,嚴格地說是災難,這是《一種藝術》中的主題:
母親的表不見了,我弄丟了它。還有,瞧!我擁有的
三棟愛宅中的最后一棟,或倒數第二棟也不見了……
兩座美麗,可愛的城市,我也弄丟了。還有許許多多
我曾擁有的其他領地,比如兩條河流,一個大陸……
并不難掌握
盡管它看起來(寫下它!)像是災難,
那是一種對抗災難的腔調,帶著無所畏懼的反諷。
針對馴化和喪失的整個循環過程,更直接的敘述可以參見《克魯索在英格蘭》這首長篇獨白詩歌。克魯索安全地返回到英格蘭,他的自傳體回憶錄非常詳細地揭露了,只要愛是缺失的,對自然的馴化就不會完美,也揭示了獨自一人在殖民過程中的艱難過程。
……我已經做了
有關其他島嶼的噩夢
那些和我的島嶼相連的,數量
多得數不清的,連成一片的島嶼,
好像青蛙的卵變成島嶼的
蝌蚪,意識到我不得不
一個個在上面住下來,直到
最終標記出它們的植物群落
動物群落,和地貌。
克魯索在對自然的馴化過程中(制作長笛,蒸餾家釀啤酒,甚至從紅漿果里提煉染料)產生了快樂的情緒(我感覺我深深愛上了/島嶼上各種小小的工業),但除了海龜,山羊和海龍卷的陪伴,社交生活的缺失導致他產生自我憐憫的心里和渴望被承認的希望的落空。陷入哲學思考的克魯索給一個火山命名為“絕望之峰”,既表達了他的憂傷,也表達了他的期望。島嶼的風景已經被馴化所改變,都是“人工改造過的”,但只有星期五到來后,馴化才真正轉向家庭生活:“僅僅當我想我再不能忍受下去了/哪怕再多一分鐘的時間,這時星期五來了。”無法用語言表達自己欣喜之情的克魯索只說出索然無味,因此也是最深刻的話。
星期五是漂亮的。
星期五是漂亮的,我們是朋友。
……他有一個漂亮的身體。
愛逃避語言。克魯索以地理學家的精確眼光詳細描述了火山、海龜、云、熔巖、海龍卷和海浪的面貌,但家庭生活實現前,他只會打手勢和做些簡單的描述。
最后,畢肖普在概括性的敘述中,先是重申在對宇宙的馴化中,人類的生活才有意義,之后思考了一旦馴化領地丟失,意義也會隨之喪失。
那里架子上放著刀——
它彌漫著意義,像一尊耶穌受難像
它在繼續存在……
憑記憶我知道每一個裂口和刮痕……
現在它不再看著我。
鮮活的靈魂已經枯萎。
我的眼睛停留在上面,然后又移開。
和駐足在存在和使用中的馴化的意義不一樣,家庭生活的意義是神秘且永恒的。結尾的獨白說:
本地的博物館征求我
將一切留給他們:
長笛、刀、干癟的鞋……
有人怎么會想要這些東西?
——而星期五,我親愛的星期五,死于麻疹
十七年前正值三月到來之際。
馴化最終朝向的目的是心靈,它一旦生根發芽,就會永遠保持自己“鮮活的靈魂”。
對家庭生活永恒的和堅不可摧的忠誠,甚至沒有受到死亡的影響,是畢肖普把詩歌意象轉向主題時,力爭要達到的行為。但我認為在《麋鹿》這首詩中,對生命經驗的講述更為深刻,這首詩沒有提及人類持久的排斥感,而是依次展示了一系列深刻的,莫名其妙的滿足感,每一種都彌足珍貴。這首詩中,土地的馴化是一層意思,家庭生活的美好是另一層,非人類世界崇高性的存在是第三層意思。
詩歌的前半部分,描述了世界地形中一個美麗無比的地方,即樸素又奢華。新斯科舍的潮汐、日落、村莊、霧、植物群、動物群和人們安靜地布置在這首詩中,好像為了一次最后的告別,當講述者旅行結束前往波士頓時。這首詩,像一幅鄉村風景畫, “有點過時的”樣子。
巴士開動。光線
逐漸加深;霧
暗中浮動,咸味,稀薄地
靠攏過來。
它的冰冷,球形水晶體
凝結,滑落又棲息
在白母雞的羽毛里,
在灰色光滑的卷心菜
在西洋玫瑰
和十二使徒的羽扇豆上;
甜豌豆緊挨著
濕的白繩子
白涂料的柵欄上;
熊蜂安靜地爬行
在毛地黃里面。
夜晚正式來臨。
精美的,惹人注目的,對白色的吟詠,懸垂、停落、接近、爬行的夜晚合唱曲,每個分句都妙筆生花,全部是告別的氛圍,對母雞、甜豌豆、雄蜂的瞬間相認全都在言說著溫柔,渴望的靈魂,通過這種方式,風景被清晰地描繪了出來。
當黑暗降臨,醒著的靈魂慢慢被誘惑進“一次夢幻的流浪/…/一個溫柔的,聽覺的,遲鈍的幻覺。”中間部分的章節體現了向童年的回歸,當講述者想象巴士里壓低的聲音,說著“陳年舊事”。
祖父母的聲音
不間斷地
談著話,漫長的時刻:
一些名字被提及
事情終于被澄清
以他們獨有的方式說著話
在羽絨坐墊中
安詳地,持續著……
現在,現在一切都好
剛好睡覺
就像所有的夜晚一樣。
生命,在這首詩所描繪的世界中,目前只包含兩種元素:鐘愛的風景和鐘愛的人,他們都已經被馴化過了,并且這些人都過著家庭生活。祖父母在聊著村莊的人情世故:
他說,她說
某人拿到了退休金;
死亡,死亡和疾病,
這年他重新結婚,
這年(一些事)發生,
她在分娩那天死去。
那個兒子已丟失
當縱帆船被發現時。
是的,他酗酒
他越來越糟,
當阿莫斯甚至在商店
也開始祈禱,但
最終家人不得不
把他送進瘋人院。
“一點不假……”那個特殊的
肯定詞,“一點不假……”
突然,倒吸一口氣,
帶著嘆息,和認命的樣子。
這一節,鄉村談話別具一格,它帶來的悲傷也和前面描述性的唯美風格不同,畢肖普把自己和《抒情歌謠集》的華茲華斯連在一起。一瞬間,家庭情感就是一切。阿莫斯瘋了,兒子葬身大海,母親去世,女孩變得越來越壞——這些都在《邁克爾》和《荊棘》中有所描述。一連串名字喚起的是強烈的家庭紐帶,它們變成了詩歌的一種形式,而新斯科舍的“草地、山巒、白樺樹”的風景則是另一種形式。我們知道,周圍的世界是怎樣的;我們也知道“生命就是如此”(就像嘆息聲“是的”所暗示的那樣)。這首詩看起來結束了,但就在講述者下意識地準備打瞌睡,發生了意外,月光下巴士停了下來。一只麋鹿在乘客中間產生驚奇的感覺,它“高如一座教堂/普通得如一只馬,”乘客們“嘀咕著驚叫/天真,溫柔地。”麋鹿遲遲沒有離開。
她磨蹭著時間
查看巴士,
莊重地,超脫塵世的樣子。
為什么,為什么我們感覺了
(人人都如此)這種甜蜜的
快樂的激動?
這種快樂是什么?
《大多數》中,弗羅斯特使用了這個寓言的變體。與畢肖普的詩一樣,有一個造物被看見從“密不透風的森林”走了出來。但弗羅斯特的野獸辜負了我們的期望。詩人所祈求的是“對應的愛,最初的反應”,但“墜落的化身”證明那不是“人類”,也不是“附加在他身上的某人”,而是一個巨大的雄鹿,一出現就消失了。弗羅斯特的造物是男性的,畢肖普是女性的;弗羅斯特是粗暴之力的代表,畢肖普是“安全如一匹馬般”的造物”;弗羅斯特的是一次挑戰,畢肖普是一個保險安慰。在這兩首詩歌中,從森林中走出并漸漸接近的造物,都扮演的是在前華茲華斯時代上帝扮演的那個角色,而在華茲華斯那里這個角色是人類扮演的——一個寄生的人,一個古老戰士,一個乞丐。這些人類存在物,當它們出現在華茲華斯詩歌中時,部分符號化的,部分非人類的,就像寄生的人部分是雕像,部分是海獸,并且就像《肉體的寧靜和腐爛》的老人是“不知不覺陷入”一種平靜狀態,它更像是動物所具有的而不是人類的屬性。惠特曼說:“我認為我可以改變并與動物同住。”預示了一種現代性,也就是在尋找人類替代物時,不是從神那里,而是從動物中。動物的生命是一種純粹的存在,有著它們自己的宏偉端莊,它向詩人保證了存在的無窮無盡。畢肖普的麋鹿同時是母性的,神秘的,溫順的。如果巴士的乘坐者,在他們人類的工具中,注定活在鄉村世界里災難和疼痛的知識里,在瞥見某個高貴的龐然大物,即使是一個模糊的,荒誕不經的一個,他們就會感覺輕松的快樂,這個怪物存在于他們的敘述和嘆息之外,這完全是“另一個世界”。當巴士開動,“黑暗再次降臨”時,“模糊的麋鹿氣息”只留下“酸酸的汽油味”中。
《麋鹿》是一首純粹的直線性詩歌,伴隨著巴士旅行的開始,我們被要求全神貫注于整個旅程。每一個依次出現的事物轉瞬即逝——我們先見到鄉村風景,然后是人群,最后是麋鹿。但這種想要整體地講述——感覺這首詩完全是深思熟慮出來的——寓言地表達,都顯示著事物的排列井然有序,而不是任意為之。這首詩從成人眼中熟悉的鄉村風景開始,然后是在童年時瞥見的沒完沒了的禮節,再到對人類悲傷的敘述,最后到另一個世界的快樂存在,它從密不透風的森林中走出來,允許自己被注視。那種熟悉東西的背后,無論是可見的還是人們所熟悉的事物,都存在于陌生性和神秘性之中。正是這種神秘性引起那些嘀嘀咕咕的交談,間或夾雜著被人類的興衰沉浮所激起疼痛的嘆息聲“是的”。它保證了詩人可以大有作為。它依靠的恰恰全部是對馴化的沖動。盡管人類的努力是朝向對荒野的消除,但知道地球上的存在物比我們人類的已知范圍還要大,沒有什么比這更讓人興奮的了。伊麗莎白·畢肖普的那些關于馴化和家庭生活的詩歌,在最后的分析中,依靠的恰如其分的對神秘替補物的闡釋,它用他們自己的方式,賦予一種快樂,它比人類創造的熟悉世界的福祉陌生得多。
編輯/張定浩
* 本文“Elizabeth Bishop”,原名Domestication,Domesticity,andtheOtherworldly(《馴化,家庭,超脫的塵世》),譯自Helen Vendler,Parf of Nature, Part of us:Modern Amerian Poe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pp97-110. first appeared in World Literature Today, Winter 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