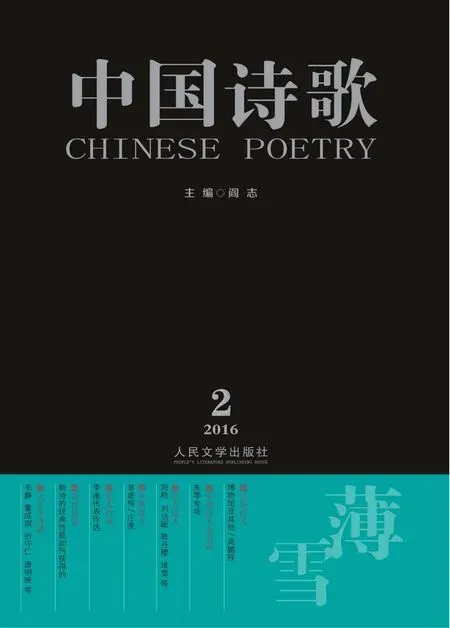拒絕背后的堅守與信念
——李南論
□劉 波
拒絕背后的堅守與信念
——李南論
□劉 波
從拒絕詩歌運動開始
“我拒絕與任何詩歌運動合作。”李南如是說。之前,我一直找不到進入李南寫作的突破口,偶然看到這個句子,在理解上有了轉機:不合作,才是李南的個性。這種不合作并非突然在她身上發生,而是有著天性使然的成分。李南從小就不是一個讓父母省心的“乖孩子”,一直以“問題女孩”的面目出現:從20歲開始,她每年會獨自遠行一次,抽煙,寫詩,聽搖滾,青春的叛逆在她身上一一應驗,而感情經歷上,她也是波折起伏,磕磕絆絆。總之,在成長過程中,束縛其個性的規則、秩序和范式,她都會本能地予以抗拒。這一切都成為了她后來寫詩時獨有的精神資源,當然,這一切也構成了她詩歌的全部。如此反叛的個性表現在創作上,對于后來的李南來說,就是把名利看淡,在書寫中追求終極真相。
李南給自己規定:不參加詩歌運動。她踽踽獨行于寂寞的詩歌之路上,不受思潮影響,不為流派左右,她失去了名利場的光環,卻收獲了內心的強大。所以,八十年代初就開始寫詩的她,中間雖有幾年停止創作,但時間并不長,前后算起來,其詩齡也有二十多年了。可如今李南并沒有大紅大紫,不是她寫得不好,而是她拒絕了太多功利化的世俗誘惑,還給了詩歌一片潔凈的空間。她將那些非詩的東西都屏蔽掉,讓自己只剩下愛、純粹、悲憫和作為自由公民的孤獨。
當下,不少人追求的人生目標,很可能就是浮躁的本末倒置,因為那個東西“有用”,而詩歌在很多寫詩的人那里,其實是無用的。雖然這些人也挺勤奮,沒幾年就“著作等身”了,可是回頭看看,他們到底寫了些什么?似乎什么都沒寫,只是留下了一堆沒有特點的平庸文字而已。按這樣的標準推算,李南寫詩幾十年,不說“著作等身”,至少也有好幾本詩集了吧。然而,事實并非如此。除了1994年在國內公開出版過一本《李南詩選》,2007年在美國出版過一本詩歌集子《小》,在刊物上零星發表過詩作,此外別無其他。她不僅對出詩集很謹慎,甚至連投稿都不多,不高產也就理所當然了。對此,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但李南清楚地知道自己寫作的趣味和目的。
李南對自己有個要求:生前不花錢出詩集。這對于大部分寫詩的人來說,也許是個苛刻的原則。這似乎只有兩種人能實現:一是你有權有錢,出版社愿意給你出詩集;二是你成為一個著名詩人,著名到能有幾千個讀者甘愿掏錢買你的詩集。否則,一個詩人很難保證不花錢出詩集。李南公開出版的兩本詩集,她個人并沒有出錢。之所以敢定下如此原則,她必有她自信的一面,另一方面,也在于她給自己劃定一個底線,越出了這個底線的事情,就不能做。不管前方有多大的誘惑,包括參加詩歌運動可以一舉成名,包括自費出詩集然后去評獎,她統統拒絕。這就是個性,這種個性沒有給李南帶來世俗的名利,但為她的詩人身份定格了尊嚴。
有了這種不合作以及那些拒絕,李南給自己限定了方向:你只有一條路往前走,朝著那個水平和高度,認真用力地寫,此外別無他途。一個人的決絕,有時可能會從某種程度上成就自己,李南失去的是世俗名利,可她收獲了一個詩人的坦蕩、胸襟與無悔。在寫詩經年后,詩人曾表白過心跡:“媽媽說,詩人/風花雪月的情種/最沒出息——/尤其是在這個年代。//媽媽啊,可我偏偏愛上了/這門傳承已久的技藝/從不指望它掙錢、糊口,改變/我命定的軌跡。//我愛它,是當它張開歡樂的嘴唇/就有了人間秘密。/而我要站在永恒的光年中/聽神說話。//媽媽,我偏偏愛上了/這些水手的船、勇士的劍/我愛這些神奇的漢語,勝過/法布爾愛他的昆蟲。”(《心跡》)詩人與媽媽對話,一語道破天機,什么讓她對詩歌孜孜以求,不離不棄,那種神秘性和高貴感,還有漢語的神奇,都吸引她去付出,去為了精神與世俗抗爭,去為了境界而改變軌跡。
李南的詩歌是一種有尊嚴的寫作,想必看過其作品和了解其生活的人,都不會太過質疑。富有尊嚴,才是當下詩人身上最為匱乏的品質。有人雖然在寫作,但他始終趴在地上,卑微地寫,屈辱地寫,茍且地寫,諂媚地寫,各種形式都有,無非是為了迎合,無非要成名得利。李南在寫作上一直很自律,她的節制與低調,她的不張揚和求真意志,我覺得這也是個性。有人說,這樣才是最沒有個性的。個性是特立獨行,是內斂叛逆,而李南恰恰又具備這幾點特征:抽煙,愛搖滾,頻繁換工作。在河北,她如此生活,肯定有人不理解:找個工作好好干,踏實一些,總會有出頭之日。但是李南沒有這樣“守規矩”,她需要有自由,哪怕為了自由去喝“西北風”。所以,她才不合作,才拒絕和抗爭,這種決絕的態度也或多或少地遭遇過誤解。在很多人能夠忍受之處,李南卻不能忍受。雖然在每一份工作上,她都做得很精彩,可終究沒能“堅持”下來,因為有很多體制的束縛,她無法容忍,追求自由的本性是她的權利。其實,她能找到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就夠了。在這個多元化社會,怎么活?如何活?關乎個人的性情。李南對自己的世俗生活很投入,擁抱時尚和先鋒;同樣,她也在竭力尋找個人的精神空間,既敏感于生活,又警惕被生活所裹挾和征用。“寫詩沒有改變我個人的命運,但詩歌改變了我對命運的認識,我將對它心存感念。”(李南《與詩友通信》)這是她多年來沒有放棄詩歌的理由,因為尋找生活出路不是借口,相反,她以寧靜、純粹的寫作來回報生活。
2011年,已近知天命之年的李南,被授予“盛世文成2011年度《青年文學》詩歌獎”。在獲獎感言中,她有一段話是這樣說的:“在現實生活中,有許多奇怪的對抗,文明與粗野,良知和惡行,尊嚴與屈辱,美與丑等,這一切事物的內在關系,都需要詩人通過詩歌的形式向世人秘密言說。在這個每個人都很精明很大膽很能忽悠很能賺錢的社會里,那些真正的詩人,像一群彈盡糧絕的戍邊戰士,在被人遺忘的角落,捍衛著此在的最后尊嚴。由此,我愿意向每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詩人表示最崇高的敬意,是他們高貴的靈魂日復一日地承受著寂寞和孤獨,給這個世界帶來了愛和美的希望。”或許,這段話最能代表李南對自我的警惕,對他者的理解,對時代與社會的認識,對真實的內心生活的體驗,這也是她能始終不渝地堅守詩歌現場的使命所在。
李南對自己是有要求的,這樣也就決定了其思考必須超越低俗,其寫作也就自然地拒絕平庸。她不會隨意下筆,也不會將作品輕率示人,這與她的節制和低調一脈相承。李南身上有矛盾的一面,或者說有雙重性,但是,她的寫作與生活,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又是統一的,那就是對虛假和凡俗的反抗,這并非要求得不朽,乃性格使然。這樣的性格對于寫作之人來說,恰屬難得。她帶著理想去追求詞語的變幻,從而執著于一種信念,享受自己的活法。
大和小,輕與重
說了那么多與李南詩歌文本無關的話題,看似與其寫作無涉,其實并非可有可無。對于一些慣于炒作的詩人,他們的生活與寫作大都捆綁在一起,我們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去挖掘更多。而對于李南來說,了解她的生活、想法,以及她的不合作和拒絕,是真正進入其詩歌的前提。她何以在自己的寫作里不顯山露水,不刻意張揚?因為她要最本真地接近自我和他者的心靈,去“為讀者提供生活與思考的有效信息和變異的語言組合形式”。(李南語)
了解李南且讀過其詩作的人,可能會有疑問:她那么心高氣傲,那么桀驁不馴,她的寫作應該很仗義,很硬實,或者說很刻薄,很陰險,然而,我們沒有讀到這樣的現實。相反,我們從李南的詩中看到了小與大的對峙,也洞察到了輕與重的分量。對于女性詩人,我們可能想當然地就認為李南的詩偏于小,偏于輕,因為她的細膩高于其身上所具有的粗獷,但她又是有力的,這種力量在于她多年對自我、時代和人生社會的思考。李南寫作的精神源頭,除了她自我的天賦和秉性,還有就是異域的影響。俄羅斯白銀時代詩人茨維塔耶娃和阿赫瑪托娃,這兩位夜鶯為李南帶來了暗夜中的希望:雖然她時常遭遇孤獨,但孤獨并不總是與虛無相關,它有時也是一種信念,讓詩人去思考、表達和釋放。她所能提供給我們的,就是那些帶著體溫的句子,不管何時何地讀,都能讀出味道,體驗感覺,也就是說,它們不會讓你失望,能讓人產生信任感。她雖然在寫自己的人生,但她從俄羅斯白銀時代女詩人那兒所傳承的精神之源就足以讓人敬重,她有理由寫出深刻的文字,開闊的風范。
李南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就是她詩歌中的“小”,這不是小女子的“小”,而是一種人生信念,一份生命感覺。“小的枝丫、萌發小的心愿/小的嘴唇、吐出小的諾言/小啊,讓我在月光下/垂下肩膀。/天宇的飛翔中,恒星是小的/恒星的旋轉中,人群是小的/人類的步伐下,有更小的/螻蟻、芝麻、塵埃……/小啊!常常讓我羞赧和悲戚/面對著大/我沒有別的想法。”(《小》)一個小枝丫的意象,讓人想到了小的心愿,一連串意象羅列都顯得順理成章,皆源于常識的想象:有大必有小。做事為文,我們總愿意往宏大處用力,卻很少想回到小的生活中。大是一種理想,小也是一種現實,詩人面對大,需要小來獲得平衡,這并不是羞恥之事,而是一種處世原則。所謂從一粒沙子中見世界,以此來理解李南的“小”,當不失為有效的角度。除了這種帶著生活想象的“小”,她還有更為切實的感想:“我注意到民心河畔/那片小草它們羞怯卑微的表情/和我是一樣的。//在槐嶺菜場,我聽見了/懷抱斷秤的鄉下女孩/她輕輕的啜泣//到了夜晚,我抬頭/找到了群星中最亮的那顆/那是患病的昌耀——他多么孤獨啊!//而我什么也做不了。謙卑地/像小草那樣難過地/低下頭來。//我在大地上活著,輕如羽毛/思想、話語和愛怨/不過是小小村莊的炊煙。”(《小小炊煙》)詩人由民心河畔的小草發出感慨,到槐嶺菜場輕輕啜泣的懷抱斷秤的女孩,再到孤獨的患病的昌耀,她一路想來,從白天到夜晚,走過了時間,也經歷了思緒的流轉,但那不是表層的想象,而是一種內在的精神跋涉。相對于那些大場面,渺小個體的活著才顯得更真實。在活著面前,詩人的謙卑是有必要的;面對世間那么多損害、不公和屈辱,她心存憐憫;即便你是在以“思想、話語和愛怨”的方式活著,相比于那些歷史的大,現實的苦也不過是一縷縷小小炊煙。這才是詩人立足于“小”的智性言說。
李南一度對“小”情有獨鐘,似與她堅強的個性不符。“小”缺乏力量,惟有“大”才是力量的象征。其實,我們從李南筆下的“小”中正好發現了“大”,大的思考,大的境界,大的情懷。這有關力量的大,她一樣都不缺,只不過,她沒有直接寫大,而是通過那些“小”事“小”情,寫出了真正的大。小與大,在李南筆下并非矛盾沖突,而是一對辯證美學,但并不事關形而上的哲學,而是入心入理的人生體驗。《下槐鎮的一天》就是對大與小的詩歌美學最生動的驗證,帶著偶然與宿命交織的色彩。當然,詩人不尚大,但她有一個優秀詩人獨特的手藝。“我愛黯淡的生活,一個個/忙碌又庸常的清晨/有時是風和日麗,有時是大雪紛飛/我愛庸常中涌出的/一陣陣濃蔭。/這些美妙的遐想/常讓我在人群中停住腳步/看一看繚亂的世事/想一想/閃光的夜晚。”(《我愛黯淡的生活》)這首詩里有“小”的生活,忙碌,庸常,這就是生活本身,你無法再往小處去寫;可是,詩人內心有時也會隱藏想象和思考之門,一旦開啟,美妙的遐思,智慧的創造接踵而至,這些又足夠大。現實的小,思想的大,其實就是經典詩歌的格局。李南正試圖靠近這大與小的自由切換狀態。
在李南的寫作中,除了大與小這一對辯證元素,還有輕與重,追求境界的詩人都可能會遭遇這對選擇性命題。與我們從李南詩歌中看到“小”一樣,很多人會覺得“輕”也是其寫作的追求。的確,輕逸的筆觸和意蘊,李南詩歌中并不缺少。比如,“現在,我的生活只有奔跑和遺忘/在我散步的民心河上空/記憶跟隨著鳥群飛遠、飛遠。//我緊閉著嘴,寂靜又孤單/并且永遠寂靜又孤單。”(《記憶有時也斷流》)從現實到內心,這是記憶的流程,正是輕逸所能化解的孤獨。再比如,“我的詩只寫給親人、摯友、同道/和早年的戀人。//他們沿著文字穿行/總能把紅艷艷的果實找出。”(《我的詩只寫給……》)詩只獻給無限的少數人,惟有他們懂得詩人的心思,也只有他們才能共鳴于詩人何以要用孤獨換取精神世界的安寧,這并非誰都能理解的現實。同樣是沉默和孤獨,詩人也有她表現重的一面,“跟風說起宿命。/給松柏彈奏一支離別曲/當我懂得了沉默——/大夢醒來,已是中年!”(《時間松開了手……》)時間是輕的,但對人來說,它有時很重。詩人筆下歲月的秩序,你無法繞過,更不可回避,需要迎難而上,去找到活著和寫詩的理由,也找到“自己的影子”。由輕到重的轉化,也會體現在詩人的寫作里:“塵土和悲哀,曾經是/我的生活/現在,它們不是。//現在我喜愛落日凄迷時/懷著平和與沉靜/透過模糊的淚水/來看遠處一列列/站起的山峰。”(《十一行詩》)真正的輕,恰恰能與重形成一種張力,在這種詩意表達中,局部的變革并不影響整體的美感。
大與小,輕和重,當然也包括快與慢,屬于文學中老生常談的話題了,但在李南這里,它們正好構成了其詩歌美學重要的兩極,它們的交織與融合,沖突和對話,最終所凝結的就是美和力量。它們契合了一個詩人各種人生階段的思想探險:你為生活付出了什么,生活也對你報以回饋。所以,她的寫作雖然有各種沖突,但仍然顯得誠摯、肯切、純粹,從中可見出李南非同一般的藝術旨趣、美學品味與人文修養。
鄉愁意識與宗教情懷
李南詩歌中所蘊含的詩性,何以與他者不同?或者說她對詩歌的認知和理解,何以高于一般寫作者?她看待人生的角度,寫作詩歌的態度,都有一種超越之感,這不僅是文字魅力的佐證,也是她以人性寫作贏得讀者認可的緣由。語言和真理,她從未放棄過。她的寫作何以常帶憂傷,悲中積愁?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因為她內心存放的不僅有自我的拒絕和警惕,還有家國與時代的鄉愁。
鄉愁意識,似乎是很多詩人與生俱來的書寫經驗,李南也不例外。與很多身在故鄉寫故鄉的詩人不一樣,李南是身在異鄉寫故鄉,這才是名副其實的鄉愁。詩人帶著更多現實參照去描述和審視她的故鄉,所謂“有故鄉者有恒心”,就是如此。她用異鄉的情緒對接故鄉的精神維度,留給我們的,卻是一種帶著隱隱痛感的、漂泊的靈魂書寫。從細節到整體,李南的鄉愁經驗都顯得自然,高邁,那不是做作的表演,而是真性情的流露,在異鄉的呼吸中嗅出故鄉于己的倫理之味。
很多人寫鄉愁,總帶著一種抱怨的情緒,即便寫故鄉,也如同“生活在別處”,一種刻意的背離感不時流露,所以無休止的沉郁哀傷,就顯得做作。但在李南的鄉愁詩中,她直接表白情感、困惑以及迷茫:“陜西是我籍貫,青海是我故鄉/而這兒該把它叫什么?”詩人對自己生活了幾十年的地方,竟然不知道叫什么,如同一個過客。“這兒是外省,這兒是他鄉/這兒既沒有世親也找不到仇敵。”(《這兒是外省,這兒是他鄉》)尋找故鄉的靈魂沖突,讓她無法給自己定位,這種情感糾結正是詩人鄉愁意識的來源。真正把鄉愁意識把握到極致的寫作,應該是以私人的方式進入,以公共的方式出來,你必須將個人獨特的鄉愁寫出一種普適性,讓更多人產生共鳴,這才是正大一途,李南就做到了。她的經歷豐富,視野開闊,內心清醒,她以追問自我的方式出示那些難解的困惑、尷尬與蒼涼心態,當為清醒者的自白書,一個有故鄉的詩人那種對存在發問的高潔之意,瞬間躍然紙上。
“我常常羨慕他們,用手指指/遙遠的方向/說,那是故鄉//我沒有故鄉,夢中一馬平川/繞過一棵棵樹/獨自來到藍色大海的另一端//哦,青山作證/我也有沉重的鄉愁/當世界沉沉睡去,我的故鄉/在說也說不出的地方。”(《故鄉》)這是詩人直接寫故鄉的詩作,其中所流露出的濃郁鄉愁,不是在于她有故鄉,而是在于她對故鄉異于常人的認知。李南祖籍陜西,生在青海,后來隨母落戶河北,在離鄉的記憶中,無根之感會時時反映在她的文字中,這也構成了她精粹的詩意。“沒有夢想的水源只有/回不去的故鄉/沒有愛。只有閃光的片斷/疾病與貧寒,潦草的一日三餐/這么多年/他們總算都挨過了。//我驚詫于這些硬朗的生命/現在我也注定在這中間/但這原本不是我——/而是大多數人民/和田野里的蒿草一樣/普遍而不值錢。”(《活著》)如今,活著也成了一種鄉愁。故鄉回不去了,但怎樣生活仍是根本,不管你持何種姿態,都必須面對這場來自命運的綁架之旅。人生如過客,惟有鄉愁讓人可將這精神的潛流重新拉回到生活的現場,繼而找到一個切實的方向。
除了鄉愁意識,李南的詩歌中還滲透著深厚的宗教情懷,她那高貴的詩意,正源于她的悲憫和敬畏之心,源于她厚重的人文關懷以及看不見的理想和抱負,那是其詩歌富有思想性和命運感的體現,也是她的寫作承載詩意的重要平臺。
一個敏感之人,隨著年齡的增長,總會有一些東西抓住你的內心,讓你不那么輕言接受,也不輕易放棄,這種東西就是信仰。在缺少宗教信仰的中國社會,詩歌有時就是一種信仰,它擔負起了我們與世界的溝通之責。而對于李南來說,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在她筆下成為了一種人文情懷。“我曾經錯過了:一個陌生人/一場漫天大雪,和一座開花的果園。/我也不稀罕眼淚、朋友、金耳環/一切世俗的小事兒。//我固執地展開翅膀,飛越一道道山梁/又走了一程程路。/回首我亂麻一樣的生活,/真不如這些我錯過的,和我不稀罕的。”(《懺悔》)這是人生的懺悔,其實也是宗教的實踐。人生就是一場場邂逅與錯失組成的聯體,你信什么,不信什么,都由自我決定,在此,信仰充當了平衡生活的角色。你懺悔什么,向誰懺悔,又是一場情感和精神的角力,個體內部的宗教對自我進行審視,呈現自然轉換的路徑,這種由此岸抵達彼岸的方向,直接關聯于詩人的眼光和視野,關聯于她持守什么樣的個人情懷。
在那些閃著幽暗之光的句子中,處處充盈著宗教的氣息,你如閱讀過,感受過,體驗過,定有各種自省與反思之情,縈繞心間,揮之不去。她有懺悔:“羞愧啊!面對古老黑暗的國土/我本該像杜鵑一樣啼血……”(《羞愧》);她有要求:“答應我,你不許在暮色中唱起哀歌/不許把紅色的事物看成血。/答應我,我們要把美德在大地上傳播/還要在這個世界再活一輩子”(《遙寄江南》);她有對話:“也因為你啊,/我還能夠在罪惡的人世間邊走邊唱”(《因為你》);她有傾訴:“一只離婚的喜鵲,它有袖珍版的痛苦/兩個有緣無分的人彼此思念/我無力寫出亂世間的道德和溫情”;她還有反思:“對于一個已經夠倒霉的人/我們不能再向他身上投石塊”(《成長》)。這所有的表達,都關乎個人的宗教,它們指向的不是往上的玄秘感和飄浮感,而是詩人向下的厚重感和力量感,其中不乏往事與隨想般的溫潤、體貼,以及依靠直覺感悟的飽滿和敏銳。
在宗教和信仰介入的寫作中,詩歌與自我到底是什么關系?“我試圖說出更多:山河的美、宗教里的善/人心的距離和哀傷如何在體內滋生。/你撒種——我就長出稻子和稗子/我們不穿一個胞衣,但我們命中相連。”(《詩歌和我》)真善美,正是宗教的教義所在,它們讓人找到精神的歸宿,而它們一旦進入到詩歌中,又能形成體現生命之重的價值,讓自我重新回歸到發現愛與真的表達。
從愛出發的公民精神
李南詩歌的宗教情懷,其實,還是源于一種愛,這里有大愛、智愛與博愛,雖然詩人沒有明確道出,但留給我們的是對愛無限想象的空間。有愛的人,他處理世界的方式,至少不會太偏離本心,如何做到持平公正,是一個人良知與正義的體現。李南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先是公民,然后才是詩人。”她身上獨特的求真氣質,也為其詩歌寫作帶來了不俗的品格,她的這種獨特,不是異端,也非極致,就是一種對自由、愛和正義的追尋。她那種不屈不撓的堅毅,讓自己的文字中擔負著解析這個時代的使命和責任。
愛源于責任,這種責任是任何一個公民都必須恪守和承擔的,否則,我們難以使前行之人的思路清晰明了。甚至可以這樣說,李南那些帶著血性的文字,其實都可以當作其擔負公民責任的生動注腳。在這樣一個時代,當他人都竭力躲避意識形態的是非時,李南作為一位有良知的女性,愿意站出來言說真相,講出實情,并以詩歌的方式留存這段艱深的歷史,試圖記錄那些被人漠視和冷處理的記憶。雖然李南以她的清醒,不得不面對這些現實和精神難題,但她極少去抱怨,所以她的文字少有那種控訴的戾氣和乖謬,她要守護的,還是理性的公民意識與藝術之愛的信念。“人到中年,需要掌燈,讀懂一本書的精髓/愛過的人,他不肯輕易地說出這一切/只有愛著的人,才離愛情最遠”(《愛情是燈塔》),這是愛情之愛,人到中年才明白這一愛的真諦并不晚,這種愛的距離考驗的正是詩人鄭重的內心,你無法調侃,惟有面對。愛短期丟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沒有能力再愛,詩人也期待,“總會有一個人/手提馬燈,穿過遺忘的街道/把不被允許的愛重新找回。”(《總會有一個人》)這找回的其實是一種古典之愛,且是有限度的愛,隨著個人經歷和理想而不同。詩人在書寫大自然時說,“愛春天,甚至還愛上她的缺陷——/化工廠的黑煙囪,和/小小貪官的酒氣。”(《如果我路過春天》)這種愛,在多元的寬容中隱藏著諷喻的色彩,是詩人富有力量的見證。
當然,詩人還有更廣博的愛,這種愛才是生活之愛,靈魂之愛。“你若問起我喜歡和愛——/我喜歡細數梧桐葉上的光斑/等待耶穌的救贖。/我喜歡和白蘭在小雨中散步/思念遠方的人/喜歡聽那些闡釋自由的音樂/我愛年老的阿赫瑪托娃,和她/唱出的最后一支歌。/我向往背包客生涯,每一條路都通向未知/可我知道這一切都將無法完成。/城市里燈火通明,野外的樹冠那么茂密/記憶的傷口那么疼。”這是詩人在《八月某一天》中的懷想,這樣的愛雖然如此近,如此真切,可仍然無法立即實現。即便如此,詩人仍然沒有放棄去愛,那或許才是她全部的良心所在。
內心充滿愛,才會有思想困惑;身上有責任,才會存在精神坎坷。在面對時代的提問時,李南對社會現實的介入是大氣的,有力的。因為她對自己有要求,所以,從其警醒的深度就可看出她獨立的立場:“少女熱衷于星座/中產者忙于移居海外/只有養蜂人走遍山坡/只有沿途的風,認真吹拂……//我的國家看上去枝繁葉茂/我的人民卻枯槁如經霜的草木/誰令我們喝下這致幻的迷劑/如同倒影中的納西斯//《詩經》和《雅歌》,麥香和薔薇/有誰不喜歡自由和春天的氣息?//讓新的謊言在空中變為泡沫吧!/聯合艦隊劈開海浪,并迎著海浪前進。”看看詩人怎樣書寫盛世:她直接調出了自己的公民責任感,在融合了藝術的努力后,其詩作呈現出了召喚和審視的力量。“我學會了把苦難慢慢地吞咽,再藝術地還原于生活。把寫作的視角由內心的幽怨轉向對人類命運的關注。”(李南《與詩友通信》)這里沒有慣常的喧囂,也無主流的唯諾、弱勢的逃避,她讓自我與內心合拍,達至一種思想的深邃。
李南不僅對現實有著切膚之痛,而且對歷史也常懷探尋真相的渴望。在很多年輕人的文字中,你可能看到一種孤憤、扭曲的仗義之言,而在李南的詩歌中,雖然也有憤慨,但不受他人左右而盲目地隨眾,始終持有一種堅韌的理性和執著。最根本的是,她有的文字謙和但不卑微,有的文字快意而不輕浮,總之,就是要讓自己沉下來。“這就是我的祖國:/迷信和戰爭走過它每一寸肌膚/這就是我的人民:在風中,他們命若琴弦”(《我去過許多地方……》)這些激烈的言說背后所呈現的,均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善意,即便有著批評式的話語表情,也并非為了批判而批判,不是最終目的。在此,詩人有她質樸的愿望:“我想要一個干凈的春天/沒有風沙,飛鳥把花粉撒向各地。/我想要一個溫暖的回憶/青澀的少年啊,在樹下飲酒,彈琴。/我想要一個豐富的人生/沿著神跡行走,河水洗凈了榮辱。/我想要一個公平的世道/百合芬芳,遮掩了法律卷宗里的血腥。”(《春天。心愿》)這就是真正的公民意識,她的愿望可大及國事家運,也可小到自我得失,但都不偏離詩人最本真的內心定律。“一群人向這邊走來。/他們睜大希望的眼睛,在議論著什么。/南風吹過,飛鳥的翅膀傾斜/在黑暗的國度中我認出了他們。/弱小的。掙扎的。貧窮與疾病如影相隨。/這群人和我在山腳下相遇——/他們全都是我的同類:這些信主的、信佛的,和什么也不信的。”(《一群人》)這雖然描繪的是一幅場景,但由場景延伸出來的,依舊是我們的精神之困,那是詩人眼里的真相,她必須勇敢地言說出來,這是她的責任,更是她的道義。
公民意識,在當下是一種富于底氣的表現。作為一個人,李南有挫折感,也存失敗感,但她并沒有變得頹廢或者鄉愿犬儒,只是在一種道德力量的感召下,毅然決然地去追求“體驗更新”之路。雖然李南說詩歌不是哲學,但她有時確和思想相聯,她拒絕被收編的意志,抗拒被奴役的膽識,都是思想之成熟的表現。在我們的詩歌現實里,漂亮的文字不缺乏,完美的技巧也不缺少,而惟獨稀缺的,是詩歌的真精神,其中最為匱乏的,當是詩人的尊嚴、思想,以及他們作為公民的責任和膽識。作為一個寫出了尊嚴和信念的人,李南無愧于這個時代詩人的身份和榮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