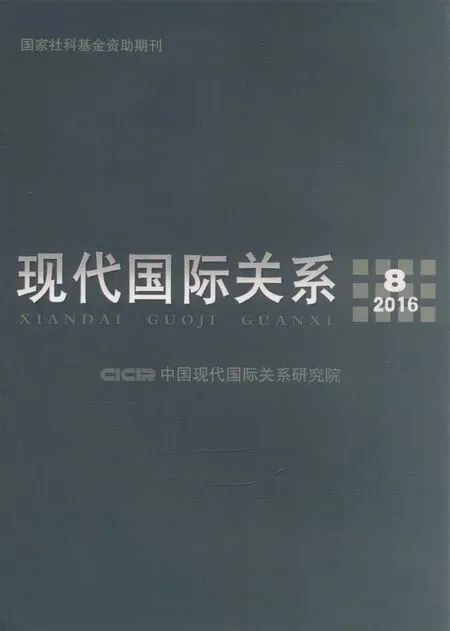歐洲的危機還遠未結束
王 朔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歐洲所副所長)
歐洲的危機還遠未結束
王 朔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歐洲所副所長)
歐洲現正處水深火熱之中,不僅經濟持續低迷,更遭難民危機、恐襲頻發,再加上英國脫歐,可謂麻煩一個接著一個,沒完沒了,這個一直被許多人視為富裕、安全的“天堂”似已風光不再。雖然金融債務危機在歐洲已暫告段落,但經濟危機猶存,更不斷衍生出其他層面的危機,進而造成歐洲當前的困局。應該說,歐洲的危機還遠沒有結束,或從某種意義上說,僅僅是剛開了個頭。
首先,這場金融海嘯應當被視為整個西方資本主義的危機。其爆發的原因,從表面上看,無非就是虛擬經濟過度膨脹后泡沫的破裂。但事實并非如此簡單,反危機也絕不可僅視為一個單純的經濟治理問題。一般而言,經濟增長需要條件,其無非就是科技的革命,亦或生產關系的革命。始于20多年前的這一輪新的全球化,帶來的是生產的全球配置和勞動生產率的普遍提高,不僅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加速發展的可能,也支撐了世界經濟的多年持續增長。但問題也由此產生,那就是隨著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西方在全球化中的主導權被弱化,去工業化和產業空心化日趨嚴重。僅以法國為例,其制造業在經濟中所占比例已不足10%,且企業60%的產出都來自海外。因此,一些掌握金融主導權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尤其以美國為代表,愈加看重從金融業中攫取超額利潤,導致金融衍生產品市場急速膨脹,可謂“手指一點,黃金萬兩”。本來以實體經濟為依托的虛擬經濟被無限放大,甚至逐漸脫離了實體經濟,成為一個獨立運作的體系。由于資本主義固有的逐利性,金融資本家們將實體經濟拋在一邊,實體經濟則由于缺乏足夠的資金支持,難以實現真正的科技革命,盈利水平自然更無法與虛擬經濟相提并論。此消彼漲之下,最后的結果必然是產生了一個巨大無比的金融泡沫,而一旦泡沫破裂,隨之而來的自然就是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嘯。
其次,金融海嘯又給歐洲帶來債務危機,更直接誘發了一場經濟危機。正所謂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當西方資本主義面臨困境之時,歐洲作為其中一員自然無可幸免,而且損失更大。歐洲銀行業因投資美國次貸損失極其慘烈,甚至超過美國,其具體數字到現在也沒有完全披露。要知道,僅德意志銀行一家就擁有75萬億美元的衍生品,幾近德國GDP的20倍。由于歐洲的銀行大部分都實行商業銀行和投行并行的混業經營,一旦投資出現問題必然涉及社會穩定,政府肯定不能坐視不管,而救助的結果就是政府財政赤字和債務水平的急速飆升。希臘終于第一個倒下,接著“歐豬五國”應運而生,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全面爆發。如果說金融危機更多是銀行業受牽連,那么這場債務危機給歐洲的打擊則可以說是全方位的,因為危機不僅涉及個別成員國,更是歐洲一體化自誕生以來面臨的最嚴峻挑戰,歐洲甚至會因此重陷內亂。因此,債務危機發生后,歐盟成立了一系列反危機機制,包括歐洲金融穩定機制(EMS)和銀行業聯盟,歐洲央行也突破政策底線推出直接貨幣交易(OMT),防止歐元區成員國銀行倒閉和政府破產,特別是歐盟還收緊了一直以來有所松懈的財政紀律,要求成員國緊縮預算,以防債務再次過度積累。從結果上看,債務危機雖被遏制,歐元區也暫無解體之憂,可是增長的難題又隨之而來。自危機以來,歐洲的經濟持續疲弱,增長率一直在1%左右徘徊,始終難有起色,與此同時的卻是失業的高企以及政府稅收的減少和負擔的加重。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要想動用財政手段已沒有可能性,增長唯一可以依賴的就僅剩下貨幣政策了。而目前歐洲央行的主導利率已經降到了零,隔夜存款利率為-0.4%,已然沒有降息空間,只能通過量化寬松的非常規貨幣手段。歐洲央行當下仍在繼續每個月800億歐元的量寬規模,而目前看效果有限,通脹水平仍幾近于零的水平。因為貨幣政策畢竟只能解決量的問題而無法解決資金的流向問題,就像金融機構即便從央行拿到了錢,在通脹走低、企業盈利預期不明的情況下,也不愿意向企業進行投資,企業甚至也不愿意借錢來擴大再生產,最后錢仍然在金融系統里循環,而不是進入實體經濟,這從歐元區主要成員國國債收益率持續下跌就可見一斑。而企業在投資不足的情況下,自然缺乏足夠的動力進行技術創新,也就難以產生所謂的科技革命,致使增長的內生動力進一步喪失。事實上,歐盟的政策思路是相互矛盾的,既要成員國刺激經濟,又要求緊縮財政,既不得不寬松貨幣,又擔心產生新的金融泡沫。可以說,現有的一切經濟政策已經走入了死胡同,以至于人人都在談危機后的“長期經濟增長停滯”問題,但似乎誰都沒有什么好辦法。
再次,經濟危機自然會帶來社會矛盾的激化。就歐洲來說,許多問題本來就有,只是經濟危機將其進一步放大和凸顯。比如外來移民融入難就是一個老問題。許多穆斯林移民本就處于社會底層,與本土社會一直存在隔閡,政府雖然向來標榜平等自由和多元文化并存,但反移民的極右思潮也一直都有。經濟好的時候,問題還不是那么突出,但經濟不好的時候,一切都成了問題。本來屬于一些治安、福利、就業等性質的社會問題,現在卻上升到了民族宗教沖突的層面,穆斯林移民與本土居民之間變得異常對立。尤其是一些二、三代年輕移民,本就生為歐洲人,頭腦中存有的是歐洲的民主價值觀,但卻因為穆斯林的身份被排斥,使其不得不通過宗教尋求精神依托,最后的結果就是激進思想抬頭,甚至引發反政府、反社會的恐襲。可以說,現在整個歐洲社會的緊張情緒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隨時都可能擦槍走火。近來德國就連續發生了多起惡性事件,有的與穆斯林有關,有的則不是,許多都屬于“激情作案”,可以說正是這種社會危機的一個直接反映。
最后,社會危機又必然會演化成為政治層面的危機。社會矛盾激化的另一個表現,就是全歐范圍內極右勢力的迅速壯大,法國的國民陣線、德國的選擇黨、英國的獨立黨等紛紛崛起,甚至開始登堂入室,進軍地方政府和國民議會。傳統主流政黨卻因為經濟政策無效、社會矛盾叢生而越發不被民眾信任,選民基礎日益流失,最終在政治大眾化、碎片化的氛圍下,不得不唯選票至上,不但不愿負起責任解決問題,還故意利用甚至操縱民意以保執政地位。英國脫歐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英國的“疑歐主義”可謂由來已久,但理性地分析,無論如何其留歐的利益都比離歐要大,而事實的結果卻恰恰相反。英國保守黨政府出于自身政治利益考慮,將英國在危機之后面臨的許多現實問題巧妙轉嫁到了歐盟身上,似乎一切問題的根源就是歐盟,離開了就什么都解決了。但我們都知道,這其實只是一種說辭罷了。幾乎所有人都沒能猜對公投的結果,甚至包括卡梅倫自己,因為這種全民公投本身就是缺乏理性和不負責任的,如果公投能解決所有問題,還要政府何用?2015年歐亞集團曾列舉了2016年世界十大政治風險,排在首位的就是歐洲,現在看這一預言已經成為現實。西班牙議會選舉已經搞了兩輪還是難以組成政府,意大利的倫齊因為搞憲法改革可能面臨倒臺,而2017年法國、德國又將面臨新一輪大選。歐洲的政客們大都自身難保,哪里又能有什么辦法來解決這些日益尖銳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矛盾呢?
未來的歐洲恐怕還要亂上一段時間,畢竟這場危機說到底是西方資本主義模式出了問題,自然也不是僅僅靠一兩項政策或是某一個人就能解決的。如果說1929~1933年的那場危機最后的結果是席卷全球的世界大戰,那么是時候去認真思考一下了,畢竟法國前總統密特朗那近似于遺囑的警告“民族主義等于戰爭”是那么令人警醒。既然這種金融資本主義已經走到了盡頭,那么似乎也只有破而后立了。關鍵在于危機之后是否還會走回頭老路,亦或痛定思痛另辟蹊徑,這是異常艱難的一個抉擇。因此,歐洲乃至整個西方更多的麻煩可能還在后頭。○
(責任編輯:黃麗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