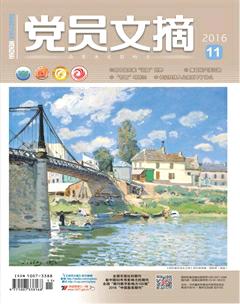當“空巢青年”成為一種心態
王一
“空巢老人”,這樣一個缺乏陪伴的群體總是讓人唏噓。可是最近另外一個流行起來的詞卻讓人覺得更加悲涼——“空巢青年”。
原本應該熱情洋溢、在追夢路上揮灑青春的青年們,怎么就成了“孤獨、寂寞、獨來獨往”的悲情群體了呢?
孤獨,還是孤獨
凌晨1點,看著房間里一片狼藉,周云晴終于忍不住哭了。
這是29歲的她來到上海的第五年,也是獨居的第五年,她已經習慣了生活的圈子里除了同事就只剩自己——
一個人上下班、一個人吃飯、一個人逛街、一個人出門旅行、一個人生病直至痊愈……
一個月前,為了換個住處,周云晴又獨自和房東、中介、裝修隊打起了交道。這天深夜,周云晴獨自打包的行李剛剛運到新家,卻因為搬家工人臨時加價,她與他們大吵了一架。她想找人撐腰,結果,來回翻了幾遍手機通訊錄,竟然不知道能夠打給誰。
五年來,周云晴第一次問自己:“我會永遠一個人嗎?”
在北上廣等大城市,像周云晴這樣的獨居青年越來越多。或主動或被動,獨居正在成為越來越多青年人的一種選擇。
根據歐睿信息咨詢公司的報告,中國獨居人數從1990年占全國人口的6%上升到2013年的14.6%。上海,則是全國獨居比例最高的城市,每4戶中就有1戶是只有1位家庭成員的,北京的比例則是20%。
除了離異、喪偶,以及基數很大的“空巢老人”之外,在大城市的獨居者中有一群像周云晴一樣的年輕人,他們被稱為“空巢青年”。
“這里有滿大街便利店、咖啡廳和快餐館,還有滿大街和我一樣一個人生活的年輕人。”在上海獨自居住兩年的90后女生李麗如說,“這里,沒有任何人會來干涉我,也讓我充分體會了空巢的孤獨。”
一個人也要好好過
李麗如把自己的生活總結為“數字生活”:20平方米,這是她居所的面積,每個月付房租要用掉一半的工資;30個,這是她平均每月在網上買東西的訂單數量,大到微波爐、洗衣機,小到垃圾袋、泡面,都通過網購解決;40分鐘,每天吃飯,她會用近40分鐘的時間,從周圍50多家外賣里精挑細選;1000次,她在手機里安裝了統計手機使用次數的應用軟件,結果是,平均每天點擊手機1000次。
盡管只有一個人,但李麗如的椅子、靠墊、碗筷都是雙份的,“一對,視覺效果才好”,但另一套從沒用過。在李麗如的家,你會感受到每一個角落都透著“一個人也要好好過”的決心。但這決心過大了,反而顯得有點焦慮。
李麗如從事的是筆譯工作,所以經常可以自己安排時間,她覺得很自由。但在沒有工作的日子里,她早上醒來不知如何是好,既沒有什么安排,又孤身一人。一開始她以看電視、手機視頻轉移注意力,不去想為什么要這樣生活,但后來卻發現這更增加了沮喪與孤獨。
在李麗如眼中,“空巢青年”的不出門和“宅男宅女”的不出門還是有不同的。“空巢青年”不出門不是因為抗拒社交,他們別提有多渴望社交了,渴望到什么地步呢?覺得上班都還不錯,至少有人說說話。
李麗如也深知,自己應該離開房間到外面與人交際,卻缺乏動力。一切都和大學時代完全不同,人們不會路過來敲門,而交朋友也越來越難,每個人都很忙。
夜深,李麗如看著對面樓房窗戶里的燈一盞盞亮起,就覺得每個獨居在大城市的年輕人都回到了他們的房間,就像安托萬筆下的小王子又回到了每個人的小星球上……
當別人談論起“空巢生活”,李麗如常常愿意這樣說:每一個人都有很大的可能性被單獨留在這個世界上,“我們都必須學會一個人面對世界,面對自己,面對孤獨”。
關鍵看自己的態度與方式
“空巢青年”乍聽之下略感凄涼,不過如果只用一個“慘”字來形容,也確實偏頗。不必羞于承認,這個群體確實滋生了一些孤獨、迷茫、悲傷的社會情緒,但其中的可愛個體也并非一味在顧影自憐,不少人認為空巢生活實際上維持了他們的個體尊嚴和自主性。
同樣是面對空巢,你會發現,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態度與方式。
有一種“空巢青年”是“無人與我立黃昏,無人問我粥可溫”型,他們會無限放大自己的空巢感:每天面對著四面墻,一遍遍刷手機等社交網絡的回復;周末癱在床上,看視頻,看完美劇英劇日劇就手足無措了,然后開始懷疑人生。
還有一種是“喝個下午茶,隨便干點啥,空巢生活樂開花”型,他們其實還挺享受自己的狀態,并且會自我約束,能夠掌控自己的生活秩序。即使一個人,也會早上7點鐘起床準時出現在健身房;會化好看的妝,也能換燈泡;周末睡到自然醒,下午去游泳,晚上去散步;一個人去看電影,一個人去看展覽。
來到大城市工作本是一種積極的生活選擇,但無人相伴的城市生活又的確讓人悲觀,心態的不同會讓年輕人對生活狀態作出大相徑庭的評估。
從本質上來說,“空巢青年”更像是“北漂”“蟻族”等詞語的某種更新和進化,因為這些詞語背后觸及的問題都是一樣的:大城市病、高房價、階層固化、獨生子女……而其中,“社會流動性增強”是多位學者對“空巢青年”現象作出的共同解釋。
“現在很多孩子都離開家了,看似人們觀念中的‘關系斷了,‘孤獨變成了一種集體性的社會心理。從這個角度看,與其說是‘空巢青年,不如說是‘脫巢青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田豐說,“準確地講,單身青年是客觀存在的社會事實,但‘空巢青年取代單身青年的流行更像是一種社會心態。”
對于如何讓青年走出空巢,田豐給出這樣的建議:國家應該鼓勵發展社會組織,鼓勵個體去承擔社會角色。用以興趣、公益取向為主的社會組織替代原本的家庭,用這樣的有機體去化解個體的孤獨。
李麗如也保持樂觀,她說:“我們很容易將自己遭遇困境的全部原因都推給社會,這固然有某些合理之處,但也可能忽視了對自我的反省,因為困境的某一部分其實源自我們自身,并且要改變困境從來都離不開自我反省。”
(杜啟榮薦自2016年8月29日《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