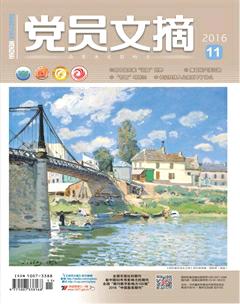毛澤東詩詞中的長征
徐廷華
長征前后是毛澤東詩詞創作的一個高峰期。詩人著力創作的幾首詩詞,生動再現、描述了紅軍長征中那些崇高壯烈、激動人心的戰斗場面和情景。
細數毛澤東長征詩詞作品,大體有《十六字令三首》《憶秦娥·婁山關》《念奴嬌·昆侖》《七律·長征》《清平樂·六盤山》《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沁園春·雪》等七首。
這些詩詞的一個共性就是大手筆、大氣勢、大胸襟,借物抒懷、托物抒情、寄情于物。寫于長征中的開篇之作《十六字令三首》,就是代表作之一。
“山,快馬加鞭未下鞍。驚回首,離天三尺三。”寫山的高聳連天。“山,倒海翻江卷巨瀾。奔騰急,萬馬戰猶酣。”寫山既像江海中的波濤澎湃,又似萬馬奔騰在戰場。“山,刺破青天鍔未殘。天欲墮,賴以拄其間。”寫山的堅強無敵,立地頂天。三首詩看似寫群山,寫山的奇險,實則是在歌頌我們偉大的紅軍是中國革命的擎天柱石,歌頌紅軍正在開創的偉大業績。
此外,《憶秦娥·婁山關》中的“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清平樂·六盤山》中的“天高云淡,望斷南飛雁。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中的“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都是國人耳熟能詳的詩句。
《七律·長征》是毛澤東在長征期間創作的最為經典的一首:“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后盡開顏。”全詩極其精煉地概括了紅軍長征的戰斗歷程,逼真地表現了紅軍的偉大形象和樂觀主義精神,展現了一幅雄偉壯麗的歷史畫卷。
這首詩寫于1935年秋天,中央紅軍已走過最艱難的路程,即將與陜北紅軍勝利會師。1935年9月28日,在通渭的榜羅鎮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第二天到通渭縣城開干部會,毛主席詩興大發,講話時即席吟誦了這首后來十分出名的《七律·長征》詩篇。正如后來毛澤東在為這首詩所作的注釋中說的:“過了岷山,豁然開朗,轉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在中國作家中,只有成仿吾、馮雪峰等少數幾人參加過長征,他們對長征詩的理解最深刻、最直接、最有說服力,特別是對“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兩句,有感同身受的體驗,是毛澤東這首詩的驗證人。成仿吾曾在一篇文章中回憶:“巧渡金沙江成功,終于擺脫了數十萬敵人的追擊與堵截,是我軍在這次空前的戰略轉移中取得的有決定意義的勝利,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一次偉大勝利。”
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夕,斯諾根據他在陜北蘇區的采訪手記完成了新聞報道集《紅星照耀中國》的寫作,當年10月,由英國倫敦維克多·戈蘭茨公司出版。書中第五篇《七律·長征》的結尾處,作者這樣寫道:“我用毛澤東主席——一個善于領導征戰又善于寫詩的叛逆者——寫的一首關于這次長征的舊體詩作為結尾。”接著,他抄錄了毛澤東的《七律·長征》詩。1938年,美國蘭登書屋出版了《紅星照耀中國》的美國版。這樣,毛澤東的這首《七律·長征》,就隨著這本書在西方的暢銷而走向世界了。
1957年,毛澤東的《七律·長征》正式發表于《詩刊》創刊號上。發表時,頸聯中的原出句“金沙浪拍懸巖暖”改為“金沙水拍云崖暖”。這一改動,毛澤東在文物出版社1958年9月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詩詞十九首》書眉上批注說:“浪拍:改水拍。這是一位不相識的朋友建議如此改的。他說,不要一篇內有兩個浪字,是可以的。”毛澤東所說的這位“不相識的朋友”,是指在東北師范大學任教的羅元貞教授。
那時《七律·長征》已廣為傳誦,羅教授讀后,覺得詩中的“細浪”和“浪拍”中有兩個“浪”,顯得重復,應該把后一個“浪”改為“水”字。于是,1952年元旦,羅元貞在寫給毛澤東主席的賀年信中,附帶提出了自己的上述建議。毛澤東收到信后,感到所提意見十分中肯,當《詩刊》正式發表時,就采納了羅元貞的意見。后來,羅元貞為毛澤東改詩的消息不脛而走,從此,他便得到毛澤東“一字師”的雅號。
從1935年寫成這首詩至今,80多年來,《七律·長征》產生了極其深遠而重大的影響,詩中的詞句被廣泛引用到與長征有關的各種事物中,也成為一種值得關注的文化現象。僅以長征題材圖書的題名為例,就不下千余種。
創作于長征末期的《沁園春·雪》,是毛澤東初到陜北時所寫,也代表了毛澤東詩詞創作的高峰。
(曹世明薦自2016年8月12日《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