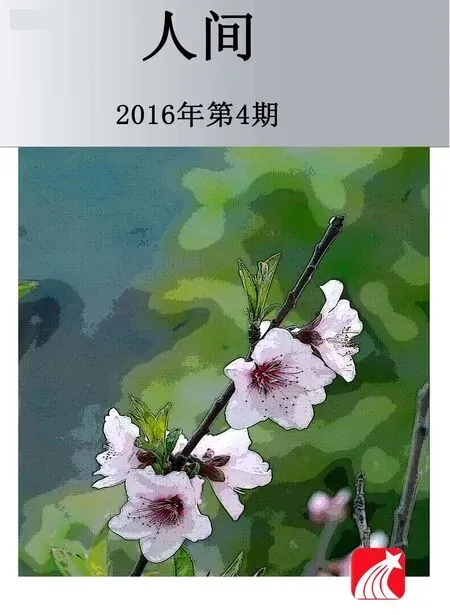朱熹與唐仲友交惡原因及其思想史意義
林育丹(華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0)
?
朱熹與唐仲友交惡原因及其思想史意義
林育丹
(華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0)
摘要:1182年,朱熹連續六次上書彈劾唐仲友,彈劾的結果是兩人都離開官場潛心學術研究。兩人在學術上都有很大的造詣,也有很大的學術分歧。而在后世的學術發展過程中,朱熹成為了家喻戶曉的儒學大家,唐仲友卻鮮為人知,這樣截然不同的命運不禁讓人深思。在學術的長河中,有分歧才會有前進,有容乃大才是學術前進的動力。
關鍵詞:朱熹;唐仲友;彈劾;學術;政治
南宋乾道、淳熙年間,南宋的政權處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其學術研究也是空前繁榮,同時產生了許多不同的學術派別,有朱熹的理學,陸九淵的心學、呂祖謙的性命之學、陳亮的事功之學,更是有唐仲友的經制之學。當然,朱熹之學最為興盛,而唐仲友的經制之學也是博大精深,當時深受一些文人的賞識,其門徒也常有數百人之多,所以朱、唐二人在當時可以說是學術的兩大巨擎。但由于朱熹六次上書彈劾唐仲友,最終導致二人的命運發生巨大的轉變,也影響了整個學術界的轉變。朱熹六次上書彈劾唐仲友的這場舊案,學界持有不同的看法,都試圖為這宗舊案找到真正的原因。其中有人偏袒朱熹,也不乏有一部分人為唐仲友喊冤叫屈,當然也有大部分人是站在一個比較公正的角度去看這場舊案的。本文筆者試圖綜合查閱現存各家文獻,還原一個真實的案件,尋找其中真正的原由。
一、朱熹六劾唐仲友
唐仲友,字與政,南宋金華人,十五歲中進士。據周學武《唐仲友年譜》記載:“唐仲友紹興六年后通判建康府,上萬言書論時政,收到孝宗的贊賞。隆興元年十二月,詔試館職。二年十二月,除秘書省正字。乾道元年二月監南岳廟,六年十一月復除秘書省正字。七年七月,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八年五月遷著作佐郎,八月知信州。淳熙三年五月,于信州任上,薦鄭建德應制科。其何時移知臺州,今不可考。”至淳熙九年,與朱熹的公案正式發生了,此時唐仲友位居臺州知州,朱熹是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朱熹是唐仲友的頂頭上司。
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七月,朱熹在任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因在巡視途中遇到臺州流民,問其因,得知為當時臺州知州唐仲友催稅急促,不顧民生所致。為此朱熹在七月十九日上書彈劾唐仲友,接下來三個月連續六次上書彈劾唐仲友,“朱文公文集卷十八按知臺州唐仲友第一狀(七月十九日),第二狀七月二十三日),第三狀(七月二十七日),卷十九第四狀(八月八日),第五狀(八月十日),第六狀(九月四日)”(《朱熹年譜長編》)。
朱熹六次上書彈劾唐仲友,期間唐仲友也有上書為自己辯護,為期三個月的彈劾對于朱熹和唐仲友來說都不是好的結局。對于朱熹彈劾唐仲友,當時的宰相王淮則認為只是“此秀才爭閑氣耳。”(《朱熹年譜長編》),故在朱熹上書彈劾的前面三次奏折都沒有采取重視的態度。見前面三次上書都沒有回應,朱熹繼續第四次的上書,這一次朱熹的態度遠比之前的三次來的強硬,也不顧王淮之前對他的引薦,直接就在奏折中表明彈劾唐仲友不成是因為有人從中偏袒。“臣竊見仲友本貫婺州,近為侍御史論薦,又其交黨有是近臣親屬者,致臣三奏,跨涉兩旬,未奉進止。深慮本人狡猾,別有計會,兼恐所司觀望,或致滅裂,切乞圣明照察,嚴賜戒勑施行。”(《朱子全書·按唐仲友第四狀》)。在朱熹第四次上書彈劾時,孝宗皇帝才對這一場的彈劾事件做了一番處理,革了唐仲友的官職,并把此官職給予朱熹。但是朱熹并沒有接受這樣的安排,而是辭官歸鄉,“事下紹興府鞠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授先生。先生以為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曰‘所劾贓吏,黨羽眾多,并當要路,大者宰制斡旋于上,小者馳騖經營于下,若其加害于臣,不虧余力······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于患害。’”(《朱子全書》)。
因為這一次的彈劾,唐仲友退出官場閉門講學,致力于學術研究,唐氏的一生在學術上有很大的造詣。但后來朱子之學占據了主導的地位,唐仲友作為朱熹的政敵,朱氏弟子也認為這場公案是后來慶元黨爭的起因,其學術成果也沒能很好的保存并流傳給后世。
二、朱熹彈劾唐仲友的罪狀
縱觀朱熹上奏的六篇狀詞,朱熹彈劾唐仲友的罪證多達五十多條,涉及面很大,如:違法促限催稅、有染于營妓、買賣官位、易換報恩寺住持、私自刊印書籍等等。
(一)不顧民生、催稅緊急。
上書狀告唐仲友催稅緊急,不顧民生疾苦是朱熹上書彈劾唐仲友的第一條罪證。“奏為臺州催稅緊急,戶口流移,知臺州唐仲友別有不公不法事件,臣一面前去番究虛實奏聞事。”(《朱子全書·按臺州唐仲友第一狀》)在此狀中,朱熹因其在離開紹興府前往白塔院的路上遇到了逃荒的難民,故問其詳才知是但是擔任臺州官員的唐仲友不顧民生疾苦,催稅急促,導致民不聊生。
因朱熹在第一狀時也只是路上聽聞,不敢定其真偽,故朱熹親自去調查虛實。在第二狀中更是細訴了唐仲友違法促限催稅的做法,“今巡歷到本州天臺縣,據入戶遮道陳訴,本縣夏稅絹一萬二千余匹、錢三萬六千余貫,緣本州催稅嚴峻,六月下旬已納及絹五千五百余匹、錢二萬四千余貫。而守臣唐仲友嗔怪知縣趙公植催理遲緩,差人下縣追請赴州。”(《朱子全書·按臺州唐仲友第二狀》)身為一方長官,理應為一方百姓謀福利,但是唐仲友身為儒臣沒有體恤人民疾苦,催稅不容刻緩,這是朱熹在上書第一狀、第二狀彈劾唐仲友的罪證。
(二)貪污枉法,私交營妓。
在第一狀、第二狀上書彈劾唐仲友而沒有得到回應后,朱熹并沒有就此罷休,而是繼續收集唐仲友的罪證。在第三狀中羅列了唐仲友在任臺州知州時的種種罪證,而其中最嚴重的當屬控告其貪污枉法、私交營妓嚴蕊這兩條。
“及先據本州通判申,并據士民陳狀,皆稱仲友到任以來,少曾出廳受領詞狀,多是人吏應褒、林木接受財物,方得簽押,無錢竟不得通。”(《朱子全書·按臺州唐仲友第三狀》)除此之外,在其狀書中還舉證唐仲友私收鹽稅、收買心腹為自己謀利益。
在其生活作風上,“仲友又悅營妓嚴蕊,欲攜以歸,遂令偽稱年老,與之落籍。多以錢物償其母及兄弟。” (《朱子全書·按臺州唐仲友第三狀》)唐仲友素與營妓嚴蕊有私交,在公共場合也是毫無顧忌,更是試圖為嚴蕊落籍,將其占位己有。這樣一個生活作風上的污點,對于任何時代的官員都是很大的沖擊,對于處在南宋的唐仲友當然也不例外,那么朱熹在第三狀中控告唐仲友私交營妓無非是想一擊使唐仲友名聲掃地。
(三)私自刊印書籍。
在朱熹控告唐仲友的眾多罪證中,還有一條罪證的其私自刊印書籍。“仲友到任以來,關集刊字工匠在小廳側雕小字賦集,每集二千道。刊板即成,般運歸本家書坊貨賣。”、“凡材料、口食、紙墨之類,並是支破官錢。又乘勢雕造花板,印染斑袺之屬凡數十片,發歸本家綵帛鋪,充染帛用。”(《朱子全書》第二十冊)
除此之外,在朱熹上書彈劾唐仲友的奏折中還羅列了唐仲友在職時其他種種罪證,例如私造兵器、違法招兵、私開染坊等,在朱熹彈劾唐仲友的罪證之齊全,小至唐仲友交友,大到其私收賄賂,讓后人看到都有種難以置信的感覺。可見朱熹在彈劾唐仲友之時是經過大量收集唐仲友罪證的,而朱熹收集唐仲友罪證的方法是否可靠,內容是否都是真實的,我們暫不考慮,筆者更加想要探究的是朱熹彈劾唐仲友背后的正真原因。
三、朱熹彈劾唐仲友原因探析
800多年以來,關于朱熹彈劾唐仲友的起因有很多種說法,都試圖真實的還原案件的真實原因,為這場舊案的兩位主人公尋找一種公正,又或者在這場舊案中尋找我們可以借鑒的道理。
(一)源于營妓嚴蕊,陳亮挑撥。
在朱熹上書的第三狀中確有控告唐仲友和營妓嚴蕊私交之事,后世也有人認為嚴蕊就是這場舊案的起因。宋人周密在其著作《齊東夜語》中,對嚴蕊的品行才華更是大加肯定與贊揚,也對其在這場舊案中的處境給予了無限同情。而對于嚴蕊也是有不同的說法,在朱熹的狀詞中,嚴蕊是被指認為唐仲友私交的營妓,唐仲友與嚴蕊在公共場合都不曾有所顧忌,甚至于唐仲友欲以嚴蕊年紀大的原因要為其脫去妓籍,將其占為己有。
在《宋元學案·說齋學案》中卻有不同的記載:“同甫游臺,狎一妓,欲得之,屬說齋之脫籍。不遂,恨之,乃告晦翁:‘渠謂公尚不識字,如何為監司。’晦翁銜之,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按臺。既至,說齋出迎稍遲,晦翁益以同甫之言為信,立索印,摭其罪具奏。”這里就牽涉到了一個人——陳亮,如果按照《宋元學案·說齋學案》中記載所言,陳亮在此處就是一個小人,由于他想為嚴蕊脫籍,自己又沒有能力,就托付給唐仲友。后因唐仲友沒有幫他,他就去朱熹面前搬弄是非,以至于朱熹對唐仲友懷有芥蒂。這種說法可信的程度不高,陳亮作為一位學術上有很高造詣之人理應不會做這等小人之事。
對此,陳亮自己也有解釋。在朱熹彈劾唐仲友之時,唐家、何家均托陳亮出面求情通融,但陳亮采取:“只因相勸,不應相助,治人合在秘書自決之。”在陳亮的書信中也有關于這場舊案的言論,“亮生平不曾會說人是非,唐與正乃見疑相譖,是真足當天光之死矣。”(《癸卯秋書》陳亮);“以秘書壁立萬仞,雖群陰之中亦不應有所拖帶。至于人之加諸我者,常出于慮之所不及,雖圣人猶不能不致察。”(陳亮《癸卯秋與朱元晦書》),這些書信當中陳亮表達了自己對于這場彈劾的看法,而對于外界加諸于陳亮的罪證,陳亮也是采用不予理睬的態度。此后,在朱熹回復陳亮的信中,也可看出朱熹對陳亮人格的評價是非常之高的,不會是搬弄是非之人。
在這一場舊案中,筆者認為嚴蕊只是朱熹檢舉唐仲友的一個罪證,而不是其導火線,若是導火線,朱熹也不可能是在上書的第三狀才檢舉唐仲友這一罪證,而應該是在第一狀中就有所陳訴。案件的導火線也更不可能是因為陳亮從中搬弄是非所致。
(二)朱、唐二人學術分歧。
對于朱唐交惡,也有部分學者認為是兩人的學術分歧所引起。兩宋時期,士大夫之間早有因學術分歧而排除異己的先例,那么朱熹彈劾唐仲友是出于學術分歧也是正常現象。
在朱熹彈劾唐仲友的狀告當中,最引人深思的是為何會有狀告唐仲友私自雕刻刊印書籍。且不說唐仲友是否利用官銀刊印書籍,根據歷史文獻的記載,在南宋時期利用官銀刊印書籍的也不只是唐仲友,很多官員都有這樣的做法。唐氏對荀子和揚雄尤其推崇,而朱熹則認為荀子“全是申韓”,揚雄則“全是黃老”,這是兩人在學術思想上的不同之一。
唐仲友的“經制之學”是南宋“浙學”的三大學派之一,“經制之學”是一門專以研究國家機器組織結構以及憲章制度沿革演變為宗旨的學問,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實用性,其文獻基礎為三代的禮樂文明。黃宗羲云:“三代彌文縟典,皆為有司之事,仲友乃創為經世之學。繭絲牛毛,舉三代已委之芻狗,以求文、武、周公之心,而欲推行之于天下。” (黃宗羲《黃宗羲全集》)全謝山云:“方乾、淳之學初起,悅齋典《禮經》制本;與東萊、止齋齊名。” (黃宗羲:《宋元學案》)皆道破了唐仲友經制之學的由來、要義及基本特色。
唐仲友的學問有在地方為官的經歷為基礎,結合當時的社會現實注重于實用,對于孟子和荀子也是吸收其合理的成分,沒有采用全盤肯定或否定的態度。唐氏對理學政治思想清談不務實之風有批評的言論,如:“浮偽之士,類以大學自居;實用之才,多以固陋見笑。”《說齋文鈔卷·學論》
朱熹作為南宋儒學的集大成者,秉承“格物致知”的性命道德之學,對整個“浙學”持著反對的態度,但是當時在政治上“浙學”的地位和影響力都遠大于朱熹的性命之學。但其具體的處置方式也有所不同,對于唐仲友可以說是達到不可相容的態度,這與兩人的性格特征也是有聯系的,兩人都是屬于性格孤傲,相對偏激之人,互相僵持也屬正常了。
由學術上的分歧導致到兩人政治上的分歧,從而朱熹會在成為唐仲友的頂頭上司之后就連續六次上奏彈劾唐仲友,在政治上唐仲友施加壓力。或許這樣的推論有失偏頗,但也不可否認朱熹在彈劾唐仲友的原因上沒有打壓學術異己的想法。
這樣一場舊案,留給后人無數的猜測,后人也在這個基礎之上不斷發揮想尋求其中正真的原因。在朱熹彈劾唐仲友之后,唐仲友離開官場,學術上有很大的造詣,也是門徒眾多,可是到后來唐仲友的著述卻面臨失傳,這不免讓人深思中國思想史上的包容性問題。有容乃大,一家之言的強大不足以振興中華文化,而應該是百家爭鳴的局勢才能夠使學術發展得更加穩健繁榮,中華文化走得更遠。
參考文獻:
[1]朱傑人.朱子全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3]脫脫.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85
[4]黃宗羲.宋元學案[M].北京:中華書局.1986
[5]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M].北京:中華書局.2012
[6]黃宗羲.黃宗羲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7]周學武.唐說齋研究[M].臺北:臺灣大學出版社1973
[8]俞兆鵬.從朱熹按劾唐仲友看南宋貪官與營妓的關系[J].南昌:江西社會科學2005.2
[9]毛策.唐仲友不是貪官[J].杭州:文學遺產.1989.1
[10]謝靈庚.唐、朱交惡辯證[M].北京:中國文化研究2009.0
中圖分類號:K2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64X(2016)02-007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