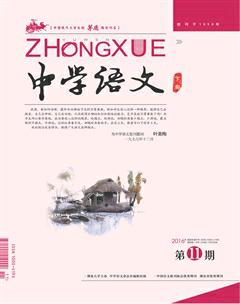文本在語文教學中的作用
張雅琳
之前,有人提出文本“工具論”,有人提出文本“人文性”,新課標又提出了“工具與人文的統一”。筆者以為,我們在反思二者孰輕孰重的同時,都應該首先考慮文本在語文教學思維中的重要性。
應該說,當前語文教材的文學色彩越來越重,即使是說明文、說理性的文章,也不是簡單地體現這些文體的基本特點,而是在這個基礎上更強調形象性、生動性。例如人教版高中語文第二冊第二單元是一個科技說明文單元,它除了具有說明文的基本特點之外,還十分強調文本的可讀性、文學性。那么,新課標的“工具性”又如何體現呢?我想,這一任務也要在文本的學習中去實現。我們只有通過“文本”這一形象、生動、質感的“案例”讓學生逐漸做到心領神會,正如朱熹《觀書有感》所言:“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我想這個“源頭”便是那些鮮活、生動的文本,學生通過對這些文本的具體學習,方有“清如許”的語文知識、語文能力和語文運用能力。
所以,語文教學最核心的應該是把握“文本”。這可以說是與其他文科學科形成鮮明的區別,例如歷史、政治課本只是知識的表述的與承載,無需學生對文本的強化,只要他能夠掌握知識點就行了。但語文若離開了課文,脫離文本的具體語境,學生即使對一篇文章理解了,也會限制他對文本進一步的學習,那么,知識還是死知識,不會舉一反三,所謂“人文性”只是一堆說教。如果這樣,語文能力便無從談起,“人文”教育也是空洞的,文學鑒賞也是味同嚼蠟。
新課標中說:“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所謂“用教材教”是在重視學生語感培養的基礎上,為了進一步把握語文知識,我們應該做必要的“延伸、聯系”。這種“延伸”不一定是能力的提高,而是為了更徹底地體驗文本中的情感思想、表達技巧和表現手法。比如講到《赤壁賦》中的“夜游赤壁”一段,可以聯系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的前五句,充分讓學生體味月色下赤壁那種“江天一色無纖塵”的境界。由此這般,學生才會進一步領悟結尾句中作者為什么會“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文本的“延伸、聯系”,是為了更好地把握文本,體味意蘊,掌握應用知識的能力,是為了啟發學生的聯想與想像思維。如果我們的延伸、聯系離開了文本,我們只能講故事,學生也只是聽熱鬧,何談對文本的進一步領悟,更談不上融會貫通、舉一反三。同樣的道理,我們聯系作品的創作、時代背景,絕然不能代替學生去詮釋、把握文本,背景也只是為了幫助我們理解。
用王國維的一句話來總結我對“文本”與“延伸”的理解:“入乎其內,故能感之。出乎其外,故能悟之。”我們走進文本,方能具體切實地學習語文,我們適當的延伸、聯系,方能對其有靈活深刻地把握、理解。
教師的教,學生的學,都必須緊緊圍繞著文本進行,只有在這個原則下,我們才有可能實現新課標所說的“工具與人文的統一”。所以,課堂交流最核心的便是學生與文本的交流。例如我們在講授《林黛玉進賈府》一文時,由于節選部分篇幅較長,人物眾多,場景變化頻繁,敘述近乎瑣碎,描寫亦趨鋪陳,如果我們僅帶著自己的理解,而忘了文本與學生的關系,學生是難解其中韻味的。因此,只有讓學生反復閱讀,走入文本,讓學生與文本進行初步交流,我們才能充分實現師生交流,學生才能有所借鑒地理解這部名著的內涵,才能感受這一文學經典的魅力。
時下,多媒體教學已經廣泛使用,它極大地改善了我們的教學條件與方式,彌補了傳統教學的諸多不足。對于我們拓展知識的外延,讓學生更充分地理解文本的內涵具有極大的幫助。但多媒體的使用與教學本身并不是完全交融,例如知識邏輯的推演不能用直觀代替,因為培養學生邏輯思維是教學的一個重要任務,知識的體驗不能被圖畫形象代替,因為培養學生的領悟能力更是教學的目的。所以。多媒體的使用必須做到與文本結合,這是多媒體語文教學應該處理的關鍵問題。
我曾觀摩了一節運用多媒體講授姚鼐的《登泰山記》的公開課,文中有一段對“泰山日出”極精彩的描寫:“戊申晦,五鼓,與子穎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云漫。稍見云中白若摴蒱數十立者,山也。極天云一線異色,須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回視日觀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絳皓駁色,而皆若僂。”此為本節課之重點,但教師只是疏通文意,點明時間變化,色彩對比,便用課件展示了幾張“泰山日出”的照片。語言的形象是通過抽象的語音符號間接實現的,必須通過想像為中介產生其形象的意義,它與圖像的直觀形象是有著思維性的不同,可以說,這種多媒體的使用是對語感、語境、體驗的淡化,是對語文思維的湮沒。
所以,我認為語文教學的多媒體使用必須首先考慮語文思維的獨立性,必須根據文本的特點來使用,必須根據與文本相關的延伸來使用,絕不能簡單地做到知識的明白、直觀與理解。我甚至可以說,盲目迷信地使用多媒體只是在語文課堂教改中搞“洋務運動”,真正變革語文教學首先得明確文本在語文教學思維的重要性,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使多媒體在當前教學中起到巨大的作用。
教師只有讓學生走進文本,他們才有在具體語境中領悟知識的可能;教師只有讓學生融入文本,他們才有切身地感受思想人文的可能;教師只有讓學生領悟文本,他們才有對語文產生濃厚興趣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