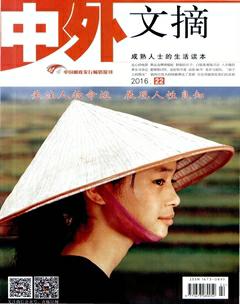老舍與胡風(fēng):“面子上的朋友”
□ 唐 山
老舍與胡風(fēng):“面子上的朋友”
□ 唐山
老舍要揍胡風(fēng)這個(gè)“狗東西”
胡風(fēng)原名張光人,湖北人,小老舍3歲,是著名的文學(xué)理論家、詩(shī)人。
胡風(fēng)的文壇地位源于魯迅。1935年,革命作家為建立抗戰(zhàn)統(tǒng)一戰(zhàn)線(xiàn),提出“國(guó)防文學(xué)”等口號(hào),而胡風(fēng)提出的口號(hào)是“民族革命戰(zhàn)爭(zhēng)的大眾文學(xué)”。圍繞“兩個(gè)口號(hào)”,左翼作家激烈爭(zhēng)論,其實(shí)質(zhì)是周揚(yáng)、胡風(fēng)兩派作家積怨的一次大爆發(fā),魯迅堅(jiān)決站在胡風(fēng)一邊,不惜為此疏遠(yuǎn)茅盾等人。胡風(fēng)從此被視為是魯迅的學(xué)生和魯迅精神的繼承者。
在此之前,胡風(fēng)與老舍已有不睦。
據(jù)學(xué)者吳永平在《胡風(fēng)對(duì)老舍的階段性評(píng)價(jià)》中稱(chēng),早在1932年12月,胡風(fēng)便在《文學(xué)月報(bào)》上發(fā)表了題為《粉飾,歪曲,鐵一般的事實(shí)》的長(zhǎng)文,將《現(xiàn)代》雜志第1卷上發(fā)表小說(shuō)的14位作家(張?zhí)煲怼徒稹⑸驈奈摹⑹┫U存、郁達(dá)夫等)全部打成“第三種人”,說(shuō)“他們的認(rèn)識(shí)大大地受了他們主觀(guān)的限制”,而老舍的《貓城記》亦在該刊發(fā)表,只是連載未完,胡風(fēng)未予評(píng)價(jià)。
對(duì)胡風(fēng)的批評(píng),巴金、蘇汶均撰文反駁,老舍沒(méi)有回應(yīng)。
吳永平認(rèn)為,1934年老舍在小說(shuō)《抓藥》中塑造了一名叫“青燕”的批評(píng)家即暗指胡風(fēng),說(shuō)他“只放意識(shí)不正確的炮”,并借農(nóng)民二頭的嘴罵道:“揍你個(gè)狗東西!”
誤以為老舍搶了飯碗
1937年11月,老舍逃至漢口,此時(shí)周恩來(lái)與王明正領(lǐng)導(dǎo)中共南方局,想成立一個(gè)文藝界的全國(guó)性民間群眾組織,即后來(lái)的“文協(xié)”(中華全國(guó)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huì)的簡(jiǎn)稱(chēng))。可由誰(shuí)擔(dān)綱,成了難題。
周恩來(lái)說(shuō),如果讓郭沫若、茅盾來(lái)負(fù)責(zé),張道藩那些人肯定不來(lái),甚至沒(méi)法“坐在一張桌子旁來(lái)開(kāi)會(huì)”。周曾提議胡風(fēng),但王明反對(duì),說(shuō)胡風(fēng)屬于“魯迅派”,是反對(duì)“國(guó)防文學(xué)”的。后馮玉祥建議說(shuō):不如讓老舍來(lái)當(dāng),他人緣好,無(wú)黨無(wú)派,又能吃苦。
胡風(fēng)參加了“文協(xié)”第一屆總務(wù)部主任的競(jìng)選,得票僅排第18位,老舍則排名第1,老舍此后連續(xù)7年任此職,胡風(fēng)則任常委、研究部主任,二人配合較多。
茅盾說(shuō):“如果沒(méi)有老舍先生的任勞任怨,這一件大事——抗戰(zhàn)的文藝家的大團(tuán)結(jié),恐怕不能那樣順利迅速地完成。”胡風(fēng)也說(shuō):“舉老舍這個(gè)有文壇地位、有正義感的作家當(dāng)總務(wù)股主任,這是符合眾望的。”但在私下,胡風(fēng)卻不是這么說(shuō)的。
1938年7月18日,胡風(fēng)在私信中說(shuō):“前天聽(tīng)說(shuō)老舍都被任為政治部設(shè)計(jì)委員,這當(dāng)然是郭沫若馮乃超之流招兵買(mǎi)馬的大計(jì)劃里面的一次。”
所謂“政治部設(shè)計(jì)委員”,是軍委會(huì)為延攬名人而設(shè)的“掛名拿錢(qián)”美差,月送車(chē)馬費(fèi)200元,郁達(dá)夫、陽(yáng)翰笙均在列,但老舍“決不拿政府的錢(qián)”,不肯加入。據(jù)吳永平考證,倒是胡風(fēng)因剛被“國(guó)民黨中央宣傳部國(guó)際宣傳處”(月薪百余元)辭退,很想當(dāng)“設(shè)計(jì)委員”而不成,便把怨氣撒到郭沫若、老舍頭上。
胡風(fēng)誤會(huì)了魯迅的意見(jiàn)
胡風(fēng)對(duì)老舍的創(chuàng)作一直不太欣賞。
1944年,重慶召開(kāi)“老舍創(chuàng)作二十年紀(jì)念會(huì)”,胡風(fēng)稱(chēng)老舍是“大眾生活的親切的同情者和大眾語(yǔ)言的豐富的擁有者”,似在褒揚(yáng),卻有保留。在文章中,胡風(fēng)稱(chēng)老舍抗戰(zhàn)前的創(chuàng)作是“舊風(fēng)流”,并對(duì)老舍抗戰(zhàn)中的創(chuàng)作提出批評(píng):“‘救急’的工作并不能和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工作截然分離。”

老舍(1899-1966)
抗戰(zhàn)爆發(fā)后,老舍主張“救急”,他說(shuō):“假若寫(xiě)大鼓書(shū)詞有用,好,就寫(xiě)大鼓書(shū)詞。藝術(shù)么?自己的文名么?都在其次。抗戰(zhàn)第一。”
對(duì)這種重實(shí)用不重藝術(shù)的傾向,胡風(fēng)認(rèn)為是“落進(jìn)了當(dāng)時(shí)一些理論家所犯的誤解”,所謂理論家,指的是郭沫若,郭同意“普及”為主,讓胡風(fēng)“氣得發(fā)抖”,稱(chēng)之為“愚民政策”。
胡風(fēng)不喜歡老舍,可能是受魯迅影響。1934年6月18日,魯迅在致臺(tái)靜農(nóng)的信中說(shuō):“如此下去,(林語(yǔ)堂)恐將與老舍半農(nóng),歸于一丘。”
魯迅讀過(guò)老舍的第一篇小說(shuō)《老張的哲學(xué)》原稿,是語(yǔ)言學(xué)家羅常培轉(zhuǎn)交的,據(jù)羅說(shuō):“魯迅先生的批評(píng)是地方色彩頗濃厚,但技巧尚有可以商量的地方。”
老舍初期創(chuàng)作有“鬧劇”傾向,他自己也曾檢討是為幽默而幽默,自然難入魯迅法眼,對(duì)于魯迅的看法,胡風(fēng)應(yīng)該很熟悉,或因此對(duì)老舍有了成見(jiàn)。
其實(shí),1936年5月,魯迅在接受美國(guó)記者斯諾采訪(fǎng)時(shí),明確說(shuō)沈從文、郁達(dá)夫、老舍是中國(guó)當(dāng)時(shí)“最優(yōu)秀的短篇小說(shuō)家”。
重念友情惜已晚
逼老舍炮轟胡風(fēng)的,是胡風(fēng)自己。
1954年7月,胡風(fēng)上“三十萬(wàn)言書(shū)”,對(duì)當(dāng)時(shí)的文藝政策提出多方面的批評(píng),麻煩的是,胡風(fēng)未經(jīng)老舍同意,便引用了老舍的觀(guān)點(diǎn),儼然老舍也是同道,事后證明,該文中被引言的人后來(lái)均遭嚴(yán)格審查。
據(jù)吳永平研究,關(guān)鍵時(shí)刻,毛澤東替老舍說(shuō)了話(huà),在《關(guān)于胡風(fēng)集團(tuán)的第三批材料》的按語(yǔ)中,毛澤東說(shuō)“原來(lái)他們對(duì)魯迅、聞一多、郭沫若、茅盾、巴金、黃藥眠、曹禺、老舍這許多革命者和民主人士都是一概加以輕蔑、謾罵和反對(duì)的”。

胡風(fēng)(1902-1985)
在此情勢(shì)下,老舍不能不撰文斥罵胡風(fēng)。
對(duì)胡風(fēng)失勢(shì),郭沫若早有預(yù)判,1952年7月胡風(fēng)調(diào)入北京時(shí),曾去郭沫若家拜訪(fǎng),郭建議說(shuō):“這是理論問(wèn)題,一時(shí)搞不清楚,我看你還是要求到西藏去吧。”如果胡風(fēng)聽(tīng)懂了郭沫若的弦外之音,后來(lái)的情況也許好得多。
老舍與郭沫若是在胡風(fēng)定案后才公開(kāi)發(fā)表意見(jiàn),雖語(yǔ)言激烈,卻無(wú)實(shí)質(zhì)內(nèi)容。胡風(fēng)的夫人梅志說(shuō):“當(dāng)時(shí)寫(xiě)的什么,胡風(fēng)也沒(méi)有當(dāng)回事。我們并不在意老舍當(dāng)時(shí)對(duì)我們的批判。”
1966年2月,胡風(fēng)出獄,分別給徐冰、喬冠華、陳家康、老舍、徐平羽寫(xiě)了告別信,在給老舍的信中,胡風(fēng)寫(xiě)道:“回憶到相濡以沫的涸轍之日,微末的悲觀(guān)竟未全消。當(dāng)此后會(huì)無(wú)期之際,不寄奉片言略表多年來(lái)對(duì)我關(guān)懷的感謝,尤其是對(duì)我規(guī)勸的歉意,實(shí)不易慨然向茫茫前途揮袂而去也。”
幾個(gè)月后,老舍自沉太平湖。
渡盡劫波未撒嘴
1951年元旦,胡風(fēng)為老舍的名劇《方珍珠》首演去老舍家祝賀,并與主要演員聚餐,可當(dāng)月12日,胡風(fēng)給夫人去信卻稱(chēng),他和老舍只是“面子上的朋友”。
魯迅曾說(shuō)“胡風(fēng)鯁直,易于招怨”“胡風(fēng)也自有他的缺點(diǎn),神經(jīng)質(zhì),繁瑣,以及在理論上的有些拘泥,文字的不肯大眾化”。
胡風(fēng)自認(rèn)為是魯迅的接班人,認(rèn)為新文學(xué)的發(fā)展必須警惕傳統(tǒng)封建主義的毒素,努力吸收外來(lái)形式,對(duì)于不接受這套理論的作家,胡風(fēng)表現(xiàn)得過(guò)于犀利,在胡風(fēng)的批評(píng)清單上,郭沫若、何其芳、艾思奇、胡繩、巴人、周揚(yáng)均在其中,胡風(fēng)還說(shuō)茅盾是“抬頭的市儈”。
茅盾說(shuō)“胡風(fēng)口袋里有一批作家”。這些作家也偏輕狂,如阿垅曾寫(xiě)道:“姚雪垠,簡(jiǎn)單得很,一條毒蛇,一只騷狐,加一只癩皮狗罷了,拖著尾巴,發(fā)出騷味,露了牙齒罷了。”在胡風(fēng)的同人雜志上,先后“整肅”過(guò)朱光潛、沈從文、茅盾、碧野、楊晦、沙汀、臧克家、袁水拍、陳白塵……胡風(fēng)與論敵的相通處,未必比相異處少。
胡風(fēng)在得知老舍去世的消息后,曾寫(xiě)詩(shī)悼念,中有“敢忘國(guó)亂家難隱,不怕唇亡齒定寒。勇破堅(jiān)冰深一尺,羞眠白日上三干”句。
1984年,胡風(fēng)撰文《紀(jì)念老舍同志誕辰八十五周年》,稱(chēng):“他(指老舍)的創(chuàng)作經(jīng)歷當(dāng)然也不是單純的,但他的和人民共命運(yùn)、為勞動(dòng)人民的解放傾注了自己的心血的追求精神,值得我們誠(chéng)懇地學(xué)習(xí)。”
褒揚(yáng)了老舍的精神,可對(duì)老舍的創(chuàng)作,仍持保留態(tài)度。
(摘自《北京晚報(b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