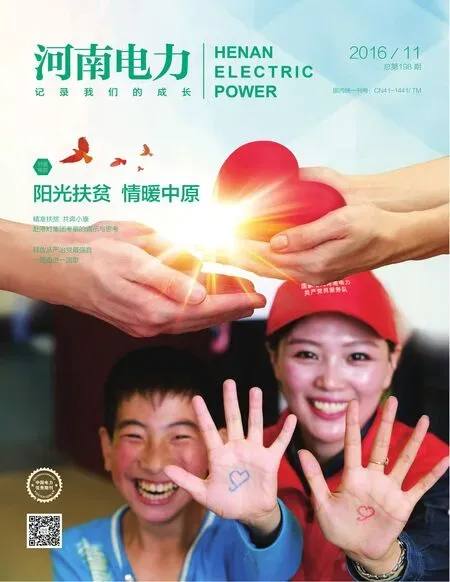淇河與許穆夫人
文/圖_申軍偉
淇河與許穆夫人
文/圖_申軍偉

《詩經》是我國的第一部詩歌總集,具體成書年代當在春秋中期,原是一部樂、詞合一的著作,分國風、小雅、大雅、頌四部分,是由民間歌謠、臣工士人創作,王室祭祀宮樂匯總而成。后來孔子曾修訂其音樂部分,反復引用,鼓勵門人學詩。因此在西漢獨尊儒術時,《詩》便上升為《詩經》,成為儒家的經典之一。
流經鶴壁境內的一條古老的河——淇河與《詩經》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淇河古稱淇或淇水,干流全長161.5千米。它不是一條普通的河,《詩經》中共有6首詩歌18次詠及淇河。
《詩經》中描寫淇河的篇章集中在國風中的《邶風》《鄘風》《衛風》之中。因為這三國都和淇河有著極為緊密的聯系。邶、鄘、衛都是周的諸侯國。周武王滅商之后,封紂王之子武庚祿父為諸侯,掌握商之遺民,但并不放心,于是將紂王的王畿一分為三,朝歌以北為邶,朝歌以南為鄘,朝歌以東為衛,由管叔、蔡叔、霍叔管理并監督武庚祿父,時稱三監。武王死后,周公旦監國攝政,管叔、蔡叔不滿周公大權獨攬,脅迫武庚一同造反。周公旦率周師征伐,三年乃定。殺管叔、武庚,蔡叔降為庶人,并將三國之地封給幼弟康叔,仍稱衛國。邶、鄘兩國存在時間只有數年,詩的內容也大都是衛國之事,但《詩經》中仍以這兩個曇花一現的國名命名,一直以來人們都推度不出其中的緣由。因此,很多人便將《邶風》《鄘風》《衛風》一概稱為衛國三風。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重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這篇《衛風·淇奧》是《詩經》中描寫淇河最著名的篇章。和《詩經》中其他描寫淇河的篇章不同的是:這篇詩中的淇河不再是一個地名,而是一個場景,一種意象。雖然只有幾句,但在兩千年前的典籍中,已是難能可貴了。
談到《詩經》,談到淇河,不能不說一說出生在淇河岸邊的愛國女詩人——許穆夫人。許穆夫人,春秋時期衛國人,衛宣公的女兒,衛懿公、衛戴公、衛文公之妹。約于周莊王七年(公元前690年)出生在衛國國都朝歌定昌。長大后因嫁給許國國君許穆公,故稱許穆夫人。
許穆夫人自幼酷愛學習,能歌善詩,少年時代曾到淇水、泉源一帶游玩,飽覽淇河兩岸的美好風光。當時周王朝已日漸衰敗,諸侯國之間兼并戰爭連年,衛國處在大國爭霸、群雄紛爭環境之中。許穆夫人成年后,才貌出眾,許國與齊國先后派人來求婚。她堅持把自己的婚事與祖國安穩相聯系,曾表示許國遙遠弱小,不能支援祖國,而齊國強盛且距離衛國較近,若與齊國聯姻,衛國一旦被侵可得到齊國的援助。但衛國國君缺乏遠見,將她許配給了許國的許穆公。
許穆夫人遠嫁到許國后,無時不在懷念著祖國。她在《竹竿》一詩中寫道:“籍籍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游,以寫我憂。”道出了她的思鄉之情。
當時,她的哥哥衛懿公嗜好養鶴,不理朝政,無視民疾,百姓怨聲載道,國勢漸弱,許穆夫人在許國聞知后心急如焚。正當她憂心忡忡思念祖國的時候,傳來北狄入侵,殺懿公,攻陷朝歌,衛戴公被迫廬于漕,國破君亡的消息。她悲痛欲絕,向許穆公提出援助衛國的請求。許國國君怕得罪狄人,僅派了使者到衛國吊唁。
許穆夫人率領身邊隨嫁的姬姓姐妹,毅然決然地駕車奔向衛國,共赴國難。可是,一些許國貴族竟然駕車要將許穆夫人追回。許穆夫人異常激憤,寫下了《載馳》嚴斥追趕者:“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悶。陟彼阿丘,言采其贏。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眾稚且狂。我行其野,艽艽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一位為拯救祖國奔走呼號的愛國者形象躍然紙上。
經過數百華里路程的艱辛跋涉,許穆夫人回到了衛國,隨即向她的長兄衛文公建議,向齊國求援。齊桓公答應了衛文公的請求,齊桓公使公子率車300乘、甲士3000人,以戍漕,幫助衛國收復失地。公元前658年衛國在楚丘(今安陽市滑縣東)再建都城,后逐漸強大起來,延續400多年。
許穆夫人寫下了許多詩篇,其中《泉水》《載馳》《竹竿》三首載入《詩經》(國風部分)。詩歌中體現的是許穆夫人熱愛祖國、不忘故土、執節不移的情愫。許穆夫人被稱為甲骨文之后華夏的第一位女愛國詩人,由于她出生在淇河岸邊,淇河也因此被稱為愛國之河。
(作者單位:鶴壁供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