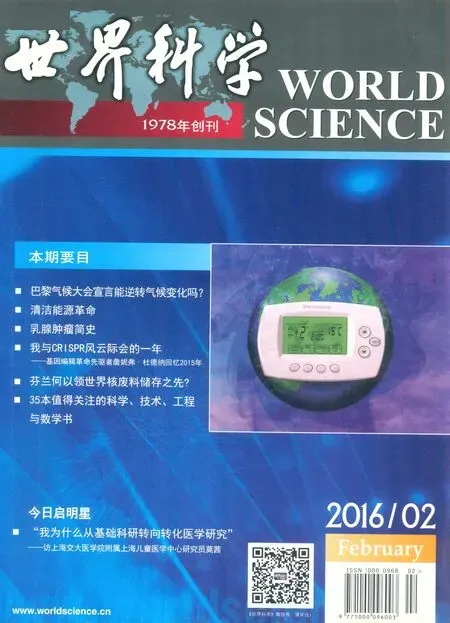我與CRISPR風云際會的一年
——基因編輯革命先驅者詹妮弗·杜德納回憶2015年
方陵生/編譯
我與CRISPR風云際會的一年
——基因編輯革命先驅者詹妮弗·杜德納回憶2015年
方陵生/編譯

●詹妮弗·杜德納(Jennifer Doudna),基因編輯技術革命的先驅者,重溫2015年與CRISPR的風云際會,談了在CRISPR風靡世界的一年里她的收獲與感想
大約20個月之前,我開始失眠。自從我和我的同事發表了一篇描述一種可以用來設計基因組且被稱為CRISPR-Cas9的細菌系統的論文以來,已有近兩年時間了。
世界各地的實驗室將這一技術應用于生物學研究領域的速度令我震驚,從修改植物基因,到改變蝴蝶翅膀的圖案,再到微調老鼠疾病的模式,凡此種種,不勝枚舉。但同時,這一技術快速成為改變基因組的工具這一事實對于其本身的哲學和倫理上的影響,我卻沒有去多想。
例如,基因組編輯是否應該用于非醫療性質的基因強化,這類問題離我所熟悉的研究領域很遙遠。所以我對自己說,這是生物倫理學家首先要考慮的問題。和大多數其他研究人員一樣,我只想利用這項技術幫助我在我的研究領域內取得成果。
迄今,用CRISPR-Cas9操縱細胞和生物體的應用越來越廣泛,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有人把這一技術應用于人類卵子、精子或胚胎的研究從而改變人類遺傳基因的做法似乎已不可避免。2014年春的那段時間里,我經常徹夜難眠,躺在床上想是否應該遠離這一場關于倫理道德的激烈爭辯,雖然它是由我所參與創建的這一技術所引發的。
CRISPR-Cas9工作原理
規律成簇的間隔短回文重復(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簡稱CRISPRs,是在細菌的遺傳密碼中發現的重復序列。它是通過將入侵噬菌體和質粒DNA的特殊片段整合到CRISPR中,從而創建入侵病毒的基因記錄。
如果重復遇到某種病毒,細菌就可以產生一段與病毒序列相匹配的RNA,這種“向導RNA”與切割DNA的Cas酶結合起來,可以發現并“隔離”匹配的病毒序列,從而阻止病毒復制。
通過對“向導RNA”的設計,研究者可以對Cas酶進行編程(普遍使用的是Cas9),使其與他們想要在細胞基因組里“替換掉”的特定DNA相匹配,從而觸發DNA修復過程,導致研究人員感興趣的基因序列發生改變。
令科學家群體興奮的CRISPR
“真令人難以相信,竟然如此成功。”這是2012年12月,我的一位一直在嘗試使用CRISPR-Cas9從事研究的同事發出驚嘆。這是我在實驗室里感受到的令人興奮的經歷,其他一些科研合作伙伴也從這項基因編輯技術中體會和分享著CRISPR給他們帶來的興奮之情。

一種新的分子分析工具通常需要幾年時間才能被普遍接受。然而,即使是在2012年后半年,在我和我的同事發表了我們最初研究的幾個月時間里,至少有6篇論文描述了CRISPR-Cas9在基因組修改工程中的應用。
2013年初,包括描述編輯人類干細胞基因組以及改變整個有機體(以斑馬魚為例)的技術等在內的數篇論文的發表,使我們預感到將有一場十分激烈的爭論發生。到2014年底,科學家們已利用CRISPR-Cas9技術做了許多事情,如用來提高小麥抗病蟲害能力,復制小鼠肺特定染色體易位的致癌效應和修改成年老鼠的基因變異(這種基因突變會導致人類遺傳性疾病酪氨酸血)等。
然而,CRISPR-Cas9的另一項潛在應用引起了更為復雜的倫理道德問題。2014年2月,研究人員描述了如何利用這一技術對獼猴胚胎基因組進行精確的修改。獼猴基因與人類基因非常接近,通常用于模擬人類遺傳疾病的研究。這種修改將導致獼猴胚胎發育過程中的大部分細胞基因發生變化,包括它們的卵子或精子,這種改變還將意味著對它們的后代的鏈式改變。
記者們爭相探尋我對這項研究的看法,這令我悚然警覺。在拜讀了這些論文之后,我從辦公室窗戶中嘹望遠處的舊金山灣,心中思考著,如果接下來記者聯系到我,并想知道我對人類胚胎基因編輯工作有何看法時,我要怎么說呢?“是否要不了多久,就會有人將這一技術運用在人類身上了嗎?”第二天早上在飯桌上,面對丈夫,我心中的疑問突然脫口而出。
與此同時,我收到了被潛在毀滅性遺傳疾病困擾的許多人的多封電子郵件。其中一封郵件中,一位26歲的女子說發現自己攜帶有BRCA1突變,當她70歲時患上乳腺癌的機率約為60%,她正在考慮是否要進行乳房和卵巢切除手術,她想知道運用CRISPR-Cas9技術治療是否意味著可以讓她避免患上乳腺癌,從而避免切術手術帶來的痛苦。
獼猴研究和與病人及其家屬的交流讓我忙得不可開交。每天都有描述CRISPR-Cas9研究的新論文出現,我的收件箱里塞滿了來自各地研究人員尋求建議或請求協作的郵件。所有這些都有可能對我的生活產生直接影響,然而我認識的大多數人與我的研究工作都沒有交集。包括我的鄰居、我的大家庭成員、我的父母和兒子的同學等,基本上都對CRISPR-Cas9都沒有什么概念。我覺得我和他們就像是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里。
在2014年底,雖然我一直不愿參與對這個問題的公開討論,但我的責任心改變了我想超脫事外的初衷。顯然,政府、監管機構和其他人都沒有關注基因編輯研究的飛速發展,除了使用這項技術的科學家,誰又會來公開討論它所產生的影響呢?
CRISPR引發的倫理道德爭論
我第一次認真介入這場倫理道德的爭論是1月份在加州納帕舉行的為期一天的會議上。我也是這一由創新基因組計劃主持并發起會議的組織者之一。與會的18人中包括有科學家、生物倫理學家、電影制片人以及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行政管理人員,我們一起討論了基因工程可能對衛生保健、農業和環境產生的影響,并重點討論了這項技術對人類生殖細胞系——卵子、精子和胚胎——的修改所產生的影響。
會議后不久,我們在《科學》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闡述我們觀點的文章,敦促全球科學界避免使用任何基因編輯工具修改人類胚胎并用于臨床,我們還建議召開公開會議,開展對非科學家人群的科普教育,進一步探討如何負責任地進行基因組工程的研究和應用。
納帕會議以來,我在學校、大學和企業,以及美國、歐洲和亞洲等地,共發表了60多次關于CRISPR-Cas9的演講,我曾在美國國會大樓前,與為美國總統提供科學建議的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談過這個話題;我也曾回答過加州州長和其他人提出的一些問題,這類討論將我從埋頭科研的寧靜氛圍里推到了由CRISPR引發的道德困境中。
作為一名生物化學家,我從來沒有用動物、人體或人體組織做過研究實驗,對于其他一些研究領域中固有的倫理困境,如克隆、干細胞和體外受精等,我都不甚清楚。但通過一些同事對我的提點,讓我對一些問題有了不同理解。例如,涉及人體或人體組織的實驗,各個國家對其的監管都有所不同,而體外受精所帶來的倫理困境在歷史上也由來已久。
2015年是我最忙最緊張,也是最令我沉迷的一年。有時我真希望自己可以走下這忙碌的“旋轉木馬”,僅僅幾分鐘也好,讓我有時間處理一下其他的事情。為了不影響我與實驗室成員的科研進展,我與他們在一起做研究的時間大多只能放在晚上或周末,或通過電子郵件交換意見。而照料我心愛的菜園,以及與13歲兒子一起到加州田野上踏青這類事也因此全都顧不上了。
在我的一位同事就CRISPR-Cas9的辯論“浪潮”即將到來提醒我三年之后,我仍然不清楚什么時候這一“浪潮”將會達到波峰。但在2015年結束之際,有些事情我已經可以肯定。
關于CRISPR更廣泛的對話
參加納帕會議的18名與會者都是美國人,大多數都是科學家,納帕會議只是關于CRISPR更廣泛對話的一個起點,但會議決議涉及兩個很重要的方面。
2014年七、八月份時,我開始產生了一些擔心,在科學家向更廣泛的群體普及相關知識之前,CRISPR-Cas9的使用要么本身是危險的,要么會被視為危險的。如果我的鄰居或朋友說:“這一切正在發生,而你為什么并沒有告訴我們?”我不會怪他們。從科學的角度來看,不久前發表在《自然》雜志上的相關評論,幫助傳達了這樣一個信息,即那些主導這項工作的人必須意識到,他們有責任就人們所擔憂的相關問題做出解釋。
4月份發表的一篇文章提出CRISPR-Cas9將被用來修改人類不能存活胚胎的基因,使得關于這些問題的討論更為迫切,從那以后,有關這個問題的大量聽證會和峰會紛紛在世界各地舉行。其中最突出是中國科學院、美國國家科學院和英國皇家學會在華盛頓聯合主辦的一個專門討論人類基因編輯問題的會議。
如今由于國際合作對科學發展的巨大影響,原則上科學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過自審制度改變全球科學事業的發展方向。我認為,讓公眾相信科學的最好辦法是鼓勵人們充分了解某項技術,并積極參與其應用范圍的討論。在這個科技知識和資源全球共享,并且發布和獲取數據資料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方便快捷的世界里,這一點尤顯重要。
此刻,讓我感到興奮的是基因工程對人類生活的潛在積極影響,以及我們對生物系統的更多了解。我的同事們經常給我發電子郵件,講述他們使用CRISPR-Cas9對各種不同生物體的研究,從培育抗蟲害的生菜,到降低菌類植物菌株的致病性,再到修改人類細胞,以期有一天能夠治愈困擾人類許久的諸如肌肉萎縮癥、囊性纖維化和鐮狀細胞性貧血等的多種疾病。
我認為,鑒于他們的研究工作有可能產生的社會、倫理和生態影響,科學家可以有一些超前的考慮。例如,為生物系學生提供一些關于如何在非科學家群體中普及科普教育的培訓,這也許能改變科研帶來的某些倫理困境。至少可以讓未來的研究人員更好地勝任他們的工作任務。例如,知道如何令人信服地描述某個研究目標,及如何判斷記者的動機并確保他們在新聞報道中準確表述,這些對于每一個研究人員的科研生涯都有很重要的意義。
[資料來源:Nature][責任編輯:遙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