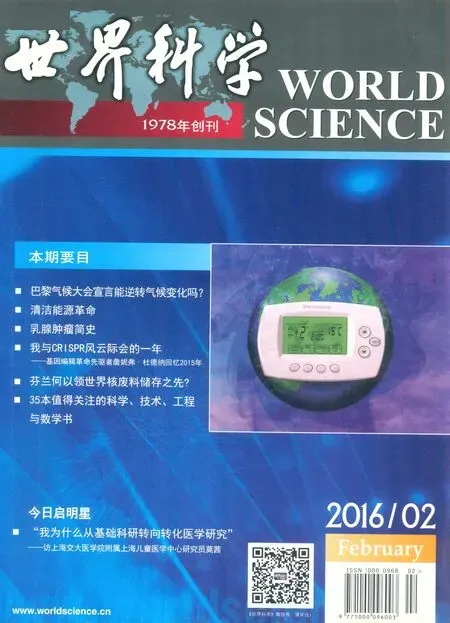諾獎藥品市場風波解讀
李升偉/編譯
諾獎藥品市場風波解讀
李升偉/編譯

●2015年秋,在納斯達克股市發生著剛剛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藥物的經濟學故事,主角是圖靈制藥公司32歲的CEO馬丁·謝科雷利。
2015年9月,在股市上,達拉匹林一夜藥價暴漲55倍,整個美國都震驚了。這個事件的主角馬丁·謝科雷利(Martin Shkreli)是圖靈制藥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原來是一家對沖基金公司經理,他宣布在他的運作下,已有62年歷史的抗寄生蟲老藥的價格從每片13.50美元猛漲至750美元,對此,沒有幾個人支持他、恭喜他令人驚異的敏銳商業才能。相反地,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們都對他表示了鄙視:藥廠CEO、美國總統的競選者、社會媒體評論者、專欄作家和期刊編輯,所有人都把謝科雷利描繪成最壞的強盜藥物大亨。據一家非常熱心的媒體稱,他已經“官方”地變成了美國最痛恨的人。
2015年2月,謝科雷利離開他備受爭議的Retrophin公司,創辦了專營藥物配送類資產的圖靈公司。8月份,他在融資了9 000萬美元私募基金后,從益邦實驗室以5 500萬美元的價格購買達拉匹林(乙胺嘧啶)的獨家經營權。這使得圖靈公司成為了獲得食品藥品管理局批準(因此可以醫保報銷)的治療弓形體蟲病的藥物達拉匹林的唯一供應商。
益邦公司自己剛剛在4月份花了7億美元購買了私募股權的美國電塔控股公司。電塔公司是于2010年從葛蘭素史克公司購得的這些權利,中間經過一家投資組合公司阿美達制藥公司。葛蘭素史克是該藥物的最初研發者,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葛蘭素和史克沒有合并時,他們就各自分別與維康實驗室有過聯系。在青蒿素獲得諾貝爾獎的30年前就開始用于了瘧疾治療,而乙胺嘧啶也是抗擊該病的關鍵藥物(配合用藥)。
引起這次社會媒體風暴的原因,不僅是謝科雷利增加藥價55倍的決策,還因為他故意傲慢地為自己辯護,稱自己是為了“正常的產業慣例”和研發需要。毫無疑問,謝科雷利令人討厭的為人和對沖基金經理的經歷點燃了這種批評。他被人們視為藥企局外人,給藥企行業帶來了不光彩的壞名聲。
在美國,負責管理生物技術制藥和制藥業的產業管理組織是生物技術產業組織(BIO)與美國藥物研究和制造商協會(PRMA),它們都與圖靈公司和謝科雷利保持著距離。百健公司的CEO喬治·斯卡格斯(George Scangos)插話說,謝科雷利給這個產業帶來了一場風暴。諾華公司的喬·基米尼斯(Joe Jimenez)指出,像圖靈這樣的公司其實“從通貨膨脹(時期)的生物技術評估中獲得了優勢和利益”。真正的“爛貨”打動了媒體粉絲們,但是,9月下旬以來美國總統大選中充滿希望的希拉里·克林頓、唐納德·特魯普(Donald Trump)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重磅加入,讓公眾看到了藥品定價改革的前景是更加真實的。
一周以后,更多的人有了理由來厭惡馬丁·謝科雷利,那就是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的頒發。納斯達克生物科技指數從9月18號到28號下降了18%,《星期日報》解釋原因,說是圖靈公司的操作引起了大規模“藥物定價”改革的需要。許多家公司的股價的境遇更加倒霉:30%~40%的下跌并不少見,尤其是那些沒有上市產品的企業。
制藥行業的秘密
圖靈公司擁有達拉匹林在美國的市場壟斷權,因為在2000年后,霍夫曼-拉羅赫公司(羅氏大藥廠)中斷了其對達拉匹林唯一的競爭藥物治瘧寧的生產。在美國之外,不存在乙胺嘧啶(達拉匹林是其仿制藥品名)的“短缺”;該藥品以幾分錢的成本生產著——生產商有印度孟買的伊普卡實驗室和中國上海、桂林等地的制藥廠——被廣泛用于全球的抗瘧疾和抗弓形體蟲病的臨床應用。這些仿制藥公司并不服務于美國市場,原因很簡單,進入成本過高,事實上形同禁止。按照2012年的《仿制藥使用者費用法案》,任何公司進入(美國)市場必須支付40萬美元的費用,只是用于得到FDA的審批和備案。他們還需要勉為其難地增加附加的成本用于準備和呈繳相關的數據資料。
其次,圖靈公司并不能從達拉匹林賺到大量的收入。如果達拉匹林可以得到其堅持不懈的750美元的價格,圖靈公司的這個2015年的新價格將使其增加將近8億美元的年度收入。事實上,不管如何,圖靈公司將是幸運的,可以在這個價格點上銷售藥品。與付費者就藥品價格進行的磋商總是在私下里進行的,任何對達拉匹林的補償報銷都可能使之與廣告價格相比大打折扣。謝科雷利個人主張,一半的美國病人能夠以一美元的價格得到該藥品。
第三點,可能是最重要的,通過電子商務進行藥品配送,也就是醫藥電商,使得上述美國以外的廠商能夠以每片7美元的價格提供達拉匹林。醫保的限制性條款可能使得報銷變得很困難:但是只是在這個瘋狂的國家,醫保方可以為每個病人支付10萬美元,以購買這種有60年歷史的老藥在圖靈公司的產品;而在歐洲、中國或印度,其同種處方藥品只需要700至1 300美元。
所以,如果這種藥品可以從聯機藥店更加便宜地得到,又何必這么小題大做呢?
一種理論認為,這與股票少有關系,與藥物定價更加沒有多大關系。作為一位前任的對沖基金經理,謝科雷利從短缺的通脹生物科技股票已經大撈了一筆,通過發明了一種機制,增加了圍繞藥品定價的道德公憤,但是也給了他一些要素來控制事件發生的時間。但是那只是一種推測而已。
如果把目光放遠大一些,隨著美國大選的進行,我們將很可能繼續看到更多關于藥品定價的口水戰。如同美國臨床腫瘤學會和臨床與經濟評審研究所這樣的組織將繼續推進藥品定價規范化的改革。產業界組織將繼續強調對保持現狀的需要。
作為生物技術與制藥的國際頂尖期刊,《自然-生物技術》雜志認可品牌制藥商有權利得到高產品價格,作為它們把創新藥物推向市場的投資的回報。但是,額外高出的價格只能對那些研發密集型的、一流實驗證明的治療產品是正當的。而且,許多正在發現和研發創新藥的此類公司也在市場上亂要價,一年比一年地抬高老藥品價格,多達400%到500%,尤其是那些專利失效的生物藥(生物制品)。這是制藥行業骯臟的小秘密。謝科雷利的罪過在于把人們關注的目光吸引到了陰暗處。
[資料來源:Nature Biotechnology][責任編輯:彥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