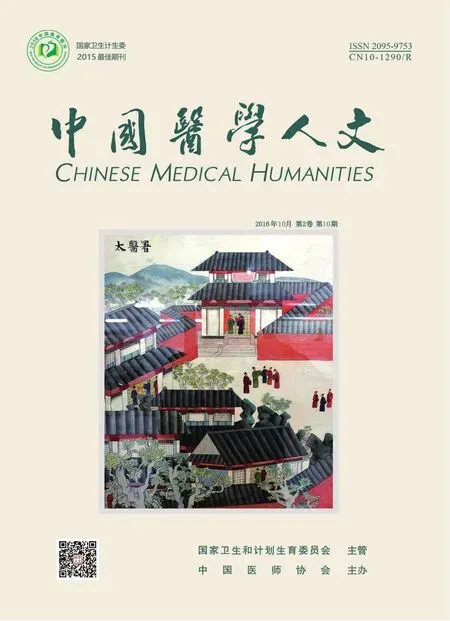醫院里的“牧師”——人文培訓專家盧文秋專訪
文/謝 姣
醫院里的“牧師”——人文培訓專家盧文秋專訪
文/謝姣
編者按:醫學人文不只是一個學科而是一種素質,是從醫者心懷天下、悲憫蒼生;是患者以禮相待、真心相托;是醫患之間相互信任、和諧相融。本期“大醫人文”欄目有幸采訪到天津市胸科醫院胸外科主任醫師,天津市胸科醫院副院長,天津醫科大學醫學人文學院兼職教授盧文秋,聽他給我們談醫院里的人文,醫院里的“牧師”。

盧文秋
“醫生這個行當介于上帝、佛與普通職業之間。大家到醫生這兒來,往往是帶著苦痛,帶著絕望,與其說是到醫生這兒來看病,不如說是到醫生這兒來尋找希望”(白巖松)。我們常說,醫生是治病救人,其實治病就夠了,為什么還要說救人?治病只是治療病狀,但是救人是一個綜合的概念。因此,心靈的撫慰和支撐原本就是這個行當極其重要的一個方面,而不僅僅是醫術本身。只有把生理上的治療技能和心理上的撫慰共同加在一起,才構成醫者仁心、治病救人這八個字的全部含義。醫生除了具有治病救命價值外,還應具有社會撫慰價值。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宗教基礎不濃厚的國度里,醫生不僅要扮演醫生的角色,還要扮演牧師的角色。患者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折磨,釋放往往來自醫生的撫慰,而這原本就是醫術的另一部分。盧文秋醫生在采訪中也表示,醫學跟神學一樣高尚。神學引領人類靈魂,醫學先是撫慰人的軀體再引領人的靈魂,醫生實際上是一個有醫學專業的“牧師”,牧師僅僅引領靈魂,而醫生不僅引領靈魂又撫慰創傷,醫治病痛。
醫學人文救贖
“原來并沒有這種刻意的人文醫學意識,只有說對病人好還是不好,這個人有人情還是沒人情,沒有具體的人文醫學的概念。”盧醫生如是說,“我從醫近40年,天天見到的都是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因為出身于很普通的勞動人民家庭,又經歷了上山下鄉當農民的過程,所以跟普通百姓的接觸比較多,就感覺到他們最需要的是理解、撫慰和同情。”10年前盧醫生剛接觸到醫學人文執業技能培訓,那時《健康報》刊登了有關醫學人文救贖的文章,指出醫學人文是解決醫患關系的必經之路,盧醫生對此很驚奇,他說,就好像黑夜里看到了黎明一樣。2000年盧醫生開始作為主管醫療副院長,他一直在思考:醫學要向哪里走,醫務人員應該往哪里帶。然而,單純地講做好人、有好心,似乎根本不可能。所以他開始注重管理,但是管理是一些生硬的東西,僅從規章制度、流程管理,只是隔靴搔癢,解決不了問題。此后就用法律手段,相關的法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執業醫師管理條例》《侵權責任法》等相繼出臺,盧醫生如獲至寶,逐漸發現單純地強調學法、懂法、用法,強化法律意識的時候,醫患關系就成了單純的法律關系了,矛盾對立就越來越多。而且,如果過分強調法律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到了底線,那根本談不上創造和諧醫患關系了。盧醫生說,很長時間以后才逐漸認識到醫學人文是創造和諧醫患關系的唯一出路,也是引導醫學回歸初心,回歸本質的唯一通道。
作者單位/中國醫師協會
“界外球”還是“界內球”
然而,醫學人文對于很多人來說只是泛泛而談,因為不明確是“界外球”還是“界內球”(王一方)。當他們真正認識到這是“界內球”的時候才會逐漸開悟。比如說,周末在醫院開一個醫學人文講座,很多醫生會認為,“咦,耽誤我學習,耽誤我業務。”“我做了五天的手術,今天好不容易休息一天,還去干擾我,我聽這有什么用。”對于有這些想法的人來說醫學人文就是“界外球”。這和我們現在社會的膚淺、浮躁都有關系。我們需要喚起人們醫學人文意識。衡量一個醫院的好與差不是看你的醫療設備、建設硬件有多好,是看你有沒有人文關懷,有沒有溫暖,是否和諧。國內的一個知名作家到美國梅奧醫院去就診,回國后總覺得欠情,每次去美國都想去看看醫院和那些醫生。盧醫生說,能讓人萌生感情的醫院,才是好醫院。醫院不單是治病的地方,還是處人的地方,是人與人之間互相關懷關心、互相撫慰的地方。好的醫生給人一種信任感,通過與他溝通,你會感覺到這個醫生有光環,很了不起。你看到的或許不是他的醫術,是人文關懷。醫術是個技術,是死的,在哪兒都沒有多大的差別。特別是當今互聯網時代,科技更沒有邊界,國外有個什么好的新藥,可能下個星期就到國內了。但是人文是整個世界,是全人類的一種共有的東西,你拋開這個,別說做醫生,做人都不合格。
在談到如今醫患關系的時候,盧醫生表示不擔心醫患關系,這只是社會轉型中的問題。現在的惡性醫患事件是我們的社會、政府、教育體系,包括我們父母對孩子的教育不到位的結果,因為你忽視了這方面,所以導致了今天的結果。如今的任務就是讓他們認識到這是“界內球”,不是“界外球”。人文講人性,如果能夠和個人聯系起來,比如通過與制度、體制、規定,包括晉升,對大夫的評價這方面聯系起來,或許能起到不一樣的效果。現在醫院評審評價要求對醫務人員定期考核技術并授權,授權里面都是些技術操作、學術類型內容,而缺乏人文素質要求。從這里來看,我們這種重技術輕人文的傾向還沒有得到改變,雖然人們開始意識到了這一點,但還需要真正把它注入到規培里面去,注入到定考里面去。盧醫生指出,真正把它做起來,將來會有改變。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是刻不容緩,時不我待。
缺的不是技術 是醫學人文
盧醫生在采訪中分享了這樣一個案例:有一個病人做心臟介入,之后出現并發癥,轉院后病人死亡。家屬不愿意,想找病歷、找原始資料。當事醫生很年輕怕有糾紛,一緊張就把病歷藏起來,被家屬當場抓個現行,醫患矛盾異常尖銳。對此盧醫生記憶猶新,家屬當即把醫院包圍,還在醫院打砸鬧。死者的兒子是法院的法官,女婿是檢察官……這事兒很難辦。了解這種情況后,保衛科的人都被請來幫忙,當時是副院長的盧醫生負責親自接待,盧醫生心想一定要平息,而病人家屬一看有領導參加,覺得被重視。第二天早上九點接待,盧醫生早早就開始準備,他告訴參與接待的醫生一定要有同理心,同情心。盧醫生說,這種問題沒有辦法解決,只有通過他們的同情心、同理心,站在患者家屬的角度上,讓他感覺到你是在真心實意地替他著想。第二天的接待非常成功,因為頭一天鬧得特別厲害,公安局、防暴,都來了,家屬來了十多個人,但是聲音卻越來越小。平息的結果是轉到醫調委走上了正常的軌道。盧醫生說,他都沒有想到,通過這種安撫、同情就能夠真的化險為夷。為了這一次接待,接待組事先是通過一些準備和排練的,“接待人員在和家屬溝通時都是與家屬保持近距離,盡管他們隨時有暴力傾向。我們與患者家屬始終保持近距離,坐在椅子的前三分之一,不會向后靠著,你越激烈,越痛哭流涕,越激動,我們就離得越近。隨時遞水遞紙巾,同情和理解。這件事情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說你早期的同情,有效的溝通,讓他感覺到信任。如果我們以同理心通過溝通展示出我們的仁心仁術,那么醫患沖突就會少得多,激烈程度也會輕得多,在此后的醫療實踐中我們越發體會到這一點”。盧醫生感慨到,“這么多的殺醫傷醫案,是這么多年來缺乏醫學人文素養培育的結果,忽視對方心理狀態的結果。當然確實存在極個別的病人精神病發作造成殺醫、傷醫案的情況,但這畢竟是極少數。大部分是因為缺乏醫學人文素養,缺乏人文關懷,缺乏溝通。說到底缺的不是技術,是醫學人文,是同理心、關懷。”
醫學是一門藝術
在被問及醫學人文執業技能的時候,盧醫生說,這么多年來他越來越不同意技能這個說法,技能就是皮笑肉不笑,而醫學是一門藝術,應該叫醫學人文藝術。2006年剛開始啟動醫學人文執業技能培訓系統的時候,醫學界普遍看法是醫學缺的不是技術,缺的不是善良,缺的是溝通技巧。盧醫生現在并不這樣認為,他說,醫學人文是藝術,是透過善良的心來行醫,你有了善心,才會有善念,有了善念你才有善為,我們要的不是皮笑肉不笑、笑里藏刀,我們要的是刀子嘴豆腐心。“所以我覺得透過善良所呈現出來的是藝術,透出智慧產生出來的是技術,我們不單單是學溝通技能,如露八個齒,怎么站,手放在哪里,這些東西會遠離病人的。”盧醫生意味深長地說。“我們現在應該從教育抓起,從人們的思想認識開始,從根上開始。而且我覺得應該從生活中切入,我們可以不去醫院,我們可以沒有疾病,我們可以和醫療無關,但是我們得做人吧,做人就應該講人文、講道德、講倫理。從這里抓起,醫學人文的基礎就是文化,一個沒有文化的社會氛圍和家庭里面別談人文。”盧醫生說這種文化給他印象最深的是梁曉聲說的那句話,是一種“無需提醒的自覺,以約束為前提的自由,替他人著想的善良”,應該成為我們醫務人員的人文準則。
像牧師一樣
在談到當今醫學生的擇業傾向時,盧醫生說,過去整個社會都認為學醫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兒,特別是文革時紀念白求恩,大家覺得醫生這個職業很高尚,但是后來市場化以后就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問題,比方說,念不完的書,考不完的試,打不完的架,生不完的氣,著不完的急,然后人們就覺得迷茫了。同樣的一個畢業生,不學醫的如果本身比學醫的能力水平差一些,但是他幾年就能成才了,就變成老總了,但這個醫學生還在規培里,還在研究生,五年大學,三年研究生,兩年博士生,最后和病人一沖突,這輩子就完了。“一個醫生的培養道路太漫長”,盧醫生語重心長,“但是如果能認識到這個職業的光輝,這個職業對人性的撫慰,如果人們認識到這個價值,我覺得人們還是會回歸醫學。就如我家夫人,她不學醫,但是她就意識到醫學是人最離不開的,是最人性的,是最科學的藝術,最藝術的科學。中國人講的生老病死,這四個字沒有一樣能離得開醫生,離得開醫院的。從這么高尚的一種精神境界上去看待這件事情,你就會覺得它有很重大的意義……特別高尚,跟神學一樣高尚。神學引領人類靈魂,醫學不僅引領人的靈魂還撫慰人的軀體,醫生就是一個有醫學專業的牧師。”
醫學人文是醫學上“道”的唯一出路,你可以不成為好專家,你也可以不成為好醫生,但是你一定要成為一個好人。好醫生做不動了,你就不是醫生了,好院長你到年齡退休了你就不是院長了,但是你是個人,至少可以是一個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