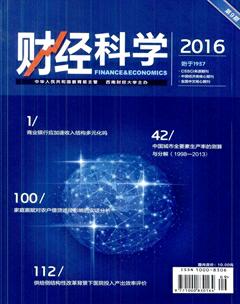中國城市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測算與分解(1998—2013)
王德祥 薛桂芝



[內(nèi)容摘要]本文采用1998-2013年全國223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數(shù)據(jù),運用參數(shù)型生產(chǎn)前沿法測算并分解了城市全要素生產(chǎn)率,分析了其時序增長和空間分布特征,得出研究結(jié)論如下:(1)1998—2013年期間,城市全要素生產(chǎn)率呈緩慢下降趨勢,樣本期間累計下降12.16%;(2)通過對隨機前沿生產(chǎn)模型進行似然比檢驗發(fā)現(xiàn)樣本期間技術(shù)進步不顯著,印證了克魯格曼“東亞元奇跡”的觀點,并對技術(shù)進步不顯著的原因進行了猜測;(3)生產(chǎn)效率總體呈改進狀態(tài),樣本期間累計上升了17.08%,且生產(chǎn)效率改進呈現(xiàn)出比較明顯的層次性。東部地區(qū)改進程度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qū),副省級及以上城市改進程度明顯高于地級城市,中國城市生產(chǎn)效率呈現(xiàn)出強者愈強的“馬太效應(yīng)”;(4)規(guī)模效應(yīng)呈逐年下降的趨勢,樣本期間累計下降29.23%,規(guī)模效應(yīng)變化是抑制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升的主要因素,規(guī)模效應(yīng)變化也呈現(xiàn)出微弱的層次性。
[關(guān)鍵詞]全要素生產(chǎn)率;生產(chǎn)前沿法;分解;規(guī)模效應(yīng)
一、引言
新古典經(jīng)濟學把經(jīng)濟增長的直接原因歸結(jié)為生產(chǎn)要素投入量的增長和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提高。資源的稀缺性意味著單純依靠要素投入的經(jīng)濟增長是難以持續(xù)的,只有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提高才是經(jīng)濟持續(xù)增長的源泉。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投資率從1981年的19.62%飛速上升到2014年的80.56%,同時“人口紅利”爆發(fā),勞動力占比不斷上升,可以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jīng)濟增長主要是靠要素投入驅(qū)動的。然而,自2011年逐年下滑的經(jīng)濟走勢印證了新古典經(jīng)濟學投入驅(qū)動增長模式無法實現(xiàn)經(jīng)濟持續(xù)增長的觀點。一方面,投資率和人口紅利終將面臨拐點,不可能持續(xù)走高;另一方面,要素投入達到一定規(guī)模一定會遇到報酬遞減的問題。當經(jīng)濟增長達到一定的階段,終將迎來經(jīng)濟增長的“陣痛”調(diào)整期。很多學者提出當前供給側(cè)改革的核心任務(wù)就是提升全要素生產(chǎn)率,將投入驅(qū)動的經(jīng)濟增長模式轉(zhuǎn)變?yōu)槿厣a(chǎn)率驅(qū)動。那么如何衡量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變化?全要素生產(chǎn)率變化的原因是什么?
索洛余值法認為,產(chǎn)出增長扣除投入增長之后剩余的就是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增長。但是,該方法對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組成部分沒有加以嚴格區(qū)分,假定所有生產(chǎn)者都能實現(xiàn)最優(yōu)的生產(chǎn)效率,認為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增長都是由技術(shù)進步帶來的,忽略了效率變化對生產(chǎn)率變化的影響。Diewet(1992)運用指數(shù)方法(Index Number Technique)構(gòu)造了Fisher生產(chǎn)率指數(shù)和Tomqvist生產(chǎn)率指數(shù)來計算生產(chǎn)率的變化,但是,這兩個指數(shù)都需要數(shù)量和價格數(shù)據(jù),如果無法提供價格數(shù)據(jù),則無法采用這種方法來計算生產(chǎn)率變化,另外指數(shù)法也無法分解全要素生產(chǎn)率,解釋全要素生產(chǎn)率變化的原因。
當前測算并分解全要素生產(chǎn)率變化常用的方法主要有非參數(shù)分析法(nonparametric teeh.niques)和參數(shù)分析法(parametric techniques)。非參數(shù)分析法將測算生產(chǎn)效率的DEA分析法和測算全要素生產(chǎn)率變化的Malmquist生產(chǎn)率指數(shù)結(jié)合起來,估算全要素生產(chǎn)率并將其分解為技術(shù)變化、規(guī)模效應(yīng)變化和技術(shù)效率變化。參數(shù)分析法運用隨機前沿分析法來計算生產(chǎn)效率,再采用生產(chǎn)前沿法估算并分解全要素生產(chǎn)率變化,將其分解為技術(shù)變化、規(guī)模效應(yīng)變化、配置效率變化和技術(shù)效率變化四部分。當前國內(nèi)采用非參數(shù)分析法測算并分解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文獻較多,而采用參數(shù)分析法分解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文獻較少。盡管非參數(shù)分析法和參數(shù)分析法都可以估算并分解全要素生產(chǎn)率,但是在隨機環(huán)境下,只有參數(shù)分析法可行。
2015年中國城鎮(zhèn)化率達到56.1%,學者們預(yù)測城鎮(zhèn)化的過程可以延續(xù)到2030年,從而進入城鎮(zhèn)化發(fā)展的成熟階段,屆時城鎮(zhèn)化水平可以達到70%。所以,城市經(jīng)濟發(fā)展的質(zhì)量直接關(guān)系到未來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的質(zhì)量。不同于以往從省級層面來測算全要素生產(chǎn)率,本文擬運用基于中國223個地級及以上城市1998-2013年的面板數(shù)據(jù),采用參數(shù)分析法測算城市生產(chǎn)效率,測算并分解城市全要素生產(chǎn)率,并對全要素生產(chǎn)率變化的組成部分進行細致地分析。相對于以往研究,本文的創(chuàng)新點在于不僅分解了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變化,而且對規(guī)模效應(yīng)的變化做出初步分解,得出資本要素對規(guī)模效應(yīng)變化的貢獻最大的結(jié)論。
二、基于SFA的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估計與分解框架
隨機前沿理論最初由Meeusen&Broeek(1977)、Aigner,Lovell&Sehmidt(1977)與Battese&Corra(1977)提出,并很快成為計量經(jīng)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當前,適用于面板數(shù)據(jù)隨機前沿模型主要有Battese&Coelli(1992)提出的時變隨機前沿生產(chǎn)函數(shù)模型和Battese&Coelli(1995)加入環(huán)境變量的時變隨機前沿生產(chǎn)函數(shù)模。Battese&Coelll(1992)其模型具體形式為:
二、計量模型的構(gòu)建與檢驗
(一)指標選取
我們參考Kams(2010)構(gòu)建一個擴展的索洛模型,Y=AF(L,K,R),R表示土地資源,所以模型的產(chǎn)出指標為Y,投入指標為L,K和R。總產(chǎn)出Y用市轄區(qū)GDP來表示,以1998年為基期,采用GDP平減價格指數(shù)進行平減。勞動力L用期末市轄區(qū)單位從業(yè)人員和城鎮(zhèn)私營和個體從業(yè)人員來表示。資本存量K采用歷年固定資產(chǎn)投資額,經(jīng)永續(xù)盤存法測算而得,資本存量的測算方法主要借鑒張軍等(2004)的做法進行測算而得。土地資源R用各地區(qū)的建成區(qū)面積表示。
我們選取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城市規(guī)模、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市場化程度、人力資本積累程度、政府規(guī)模、FDI以及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作為影響生產(chǎn)效率的環(huán)境變量。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用人均GDP來衡量;用城市年末總?cè)丝诖沓鞘幸?guī)模;用第二產(chǎn)業(yè)占比為衡量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指標;用樊綱(2011)測算的分省市場化推進指數(shù)表示市場化程度;參考戴維·韋爾(2007),用勞均人力資本表示人力資本的積累程度,勞均人力資本=(平均工資一最低工資標準)/最低工資標準;用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來表示政府規(guī)模;用FDI占GDP的比重來衡量外商直接投資水平;用人均道路鋪設(shè)面積作為其代理指標,衡量基礎(chǔ)設(shè)施的建設(shè)情況,人均GDP、財政支出和FDI均已進行平減處理。
以上變量的數(shù)據(jù)基本上來自歷年《中國城市統(tǒng)計年鑒》,其中最低工資標準手工搜集整理。由于城市的經(jīng)濟活動主要集中在市轄區(qū),為了減少由于其下轄地區(qū)導(dǎo)致的效率偏估,本文的研究對象只限定于市轄區(qū)。
(二)計量模型構(gòu)建與檢驗
隨機前沿分析方法受到的最大的詬病是效率值的計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生產(chǎn)前沿生產(chǎn)函數(shù)的形式,所以隨機前沿生產(chǎn)函數(shù)的設(shè)定至關(guān)重要。隨機前沿生產(chǎn)函數(shù)形式包括cobb-Dou-das生產(chǎn)函數(shù)和超越(Translog)對數(shù)生產(chǎn)函數(shù)。有些學者認為超越對數(shù)生產(chǎn)函數(shù)參數(shù)設(shè)置太多、二次項的經(jīng)濟意義缺乏合理解釋,而c-D生產(chǎn)函數(shù)每個參數(shù)都有很好的經(jīng)濟含義。然而,從計量方法本身來看,Cobb-Douglas生產(chǎn)函數(shù)是超越對數(shù)生產(chǎn)函數(shù)的特例,超越對數(shù)生產(chǎn)函數(shù)更具一般性。我們首先構(gòu)建超越對數(shù)生產(chǎn)函數(shù)模型,再對模型進行檢驗,以確定模型的最終形式。
對于1個決策單元在T時間內(nèi)組成的面板數(shù)據(jù),時變的隨機前沿生產(chǎn)函數(shù)用超越對數(shù)形式表示為:
檢驗通過似然比(LR)統(tǒng)計量檢驗來完成的,似然比檢驗統(tǒng)計量為LR=-2[L(Ho)-L(H)1],這里,L(Ho)和L(H1)分別為在零假設(shè)和備擇假設(shè)下的對數(shù)似然函數(shù)值。如果零假設(shè)成立,那么檢驗統(tǒng)計量LR服從漸近X2分布,即LR-X2(j),自由度j為受約束變量的數(shù)量。如果LR>Xa2(k),則拒絕零假設(shè);否則,接受零假設(shè)。
首先,我們對隨機前沿生產(chǎn)模型的適用性及隨機前沿生產(chǎn)函數(shù)的形式進行檢驗,此時備擇假設(shè)的模型形式為(9)式,零假設(shè)分別為7=u=η=0和口。βnk=βtn=βu=0。從隨機前沿生產(chǎn)模型適用性的檢驗結(jié)果看出,似然比檢驗統(tǒng)計量LR遠遠大于臨界值,所以拒絕零假設(shè),隨機前沿生產(chǎn)模型具有適用性。從隨機前沿生產(chǎn)函數(shù)形式的檢驗結(jié)果看出,LR遠小于臨界值,所以接受零假設(shè),隨機前沿生產(chǎn)函數(shù)的形式應(yīng)為c—D函數(shù)形式。
因為模型不存在技術(shù)變化,所以無需再進行檢驗,可以直接進行檢驗,此時備擇假設(shè)Hl對應(yīng)式(11),零假設(shè)為η=0,檢驗結(jié)果顯示LR值也遠高于臨界值,所以拒絕零假設(shè),技術(shù)非效率函數(shù)存在時變性。②隨機前沿模型的函數(shù)形式最終確定為式(11)。
四、城市生嚴效翠估計(1998-2013)
我們分別采用兩步法和一步法對模型進行估計,表2中模型一對應(yīng)一步法,模型二對應(yīng)兩步法。在模型一中,7為0.7348,說明生產(chǎn)者偏離前沿面主要是由生產(chǎn)中的技術(shù)非效率造成的,而模型二在用多項環(huán)境變量對技術(shù)非效率進行解釋之后,7值降為0.5128,表明本文選取的環(huán)境變量已經(jīng)解釋了非效率項的30%的內(nèi)容,這些環(huán)境變量具有一定的解釋能力。相對于模型一,模型二的σ2也明顯降低,說明加入環(huán)境變量之后生產(chǎn)過程的不確定性也明顯降低,模型二比模型一擬合得更好。對于各投入要素的參數(shù),模型二中資本要素的參數(shù)明顯高于模型一,而模型二中土地要素的參數(shù)明顯低于模型一,原因應(yīng)該在于在城市規(guī)模擴張的過程中,土地要素投入蘊含著大量的資本投入,模型二更加真實地反映了資本要素的貢獻。
從估計結(jié)果可以看出,無論在哪種模型下,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城市規(guī)模、市場化程度和人力資本積累都與生產(chǎn)效率正相關(guān)。城市生產(chǎn)效率與人均GDP成正比,說明富裕地區(qū)憑借資本優(yōu)勢、勞動力優(yōu)勢、技術(shù)優(yōu)勢和體制創(chuàng)新優(yōu)勢,擁有更高的生產(chǎn)效率。生產(chǎn)效率與城市規(guī)模呈正比,說明規(guī)模較大的城市具有明顯的要素優(yōu)勢、政策優(yōu)勢以及區(qū)位優(yōu)勢,能夠更有效地配置資源。市場化程度與生產(chǎn)效率正相關(guān),說明“看不見的手”使得市場能夠高效地配置資源,這符合經(jīng)濟發(fā)展的規(guī)律。人力資本能夠促進生產(chǎn)效率的提高是有理論依據(jù)的,但很多實證研究不能論證出人力資本對生產(chǎn)率的促進作用,主要原因在于人力資本測算方法的欠合理性,本文人力資本的積累與生產(chǎn)效率顯著正相關(guān)的結(jié)果說明我們測算人力資本的方法是合理的。投資率與城市生產(chǎn)效率呈反比,印證了Krugman(1994)隨著投資率走高會出現(xiàn)資本邊際報酬遞減以及生產(chǎn)效率下降的觀點。政府規(guī)模與生產(chǎn)效率負相關(guān)說明政府財政支出的增加對生產(chǎn)效率的改進并沒有明顯的效果,原因可能在于當前過分強調(diào)GDP的干部考核和選拔體系,導(dǎo)致地方政府行為扭曲以及財政支出結(jié)構(gòu)偏向。基礎(chǔ)設(shè)施越完善越應(yīng)有利于生產(chǎn)效率的增長,但本文論證結(jié)果顯示我國城市生產(chǎn)效率與城市人均道路面積的關(guān)系卻是負相關(guān)的,原因可能是人均道路面積只能反映道路建設(shè)的數(shù)量,不能反映道路建設(shè)的質(zhì)量,另外,以人均道路面積作為衡量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情況的指標可能不夠全面。③模型一和模型二中FDI的系數(shù)明顯不同,說明FDI與生產(chǎn)效率的關(guān)系是不明確的,這證實了張宇(2007)在短期內(nèi)FDI對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提升表現(xiàn)不明顯,更多地表現(xiàn)為一種長期的趨勢性過程的觀點。
五、城市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估計與分解結(jié)果
最終構(gòu)建的計量模型為表2的模型二,在此基礎(chǔ)上進行全要素生產(chǎn)率變化指數(shù)的分解。第三部分對隨機前沿生產(chǎn)模型進行似然比檢驗發(fā)現(xiàn)樣本期間技術(shù)進步不顯著,所以無需測算技術(shù)變化TC。另外,某些年份的城市土地成交均價無法獲取,無法測算配置效率AEc,所以只能將全要素生產(chǎn)率分解為生產(chǎn)效率和規(guī)模效應(yīng),式(7)變?yōu)椋?/p>
經(jīng)過計算,可以得到1999-2013年全國城市全要素生產(chǎn)率、生產(chǎn)效率和規(guī)模效應(yīng)的增長率及累計增長率。圖1給出了全國歷年城市全要素生產(chǎn)率、生產(chǎn)效率和規(guī)模效應(yīng)的增長率走勢,其中,規(guī)模效應(yīng)的增長率一直處于負值狀態(tài),年均為-1.95%左右,說明樣本期間的規(guī)模效應(yīng)一直呈逐年下降的趨勢。生產(chǎn)效率的增長率總體上為正值,歷年均值為1.14%,但是在1999年、2009年和2013年出現(xiàn)了劇烈的波動,尤其是2009年的增長率出現(xiàn)“斷崖式”的下降,降為一2.46%,說明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城市生產(chǎn)效率造成了顯著影響。受累于常年處于負值狀態(tài)的規(guī)模效應(yīng)增長率,大部分年份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增長率處于零值以下,說明樣本期間全要素生產(chǎn)率總體呈下降趨勢。
表3也給出了1998—2013年各地區(qū)、各城市層級城市全要素生產(chǎn)率、規(guī)模效應(yīng)和技術(shù)效率累計變化的情況。從不同區(qū)域的生產(chǎn)效率變化趨勢看,不同地區(qū)生產(chǎn)率的累計變化呈現(xiàn)出比較明顯的層次性,東部地區(qū)的生產(chǎn)效率提升最高,達26.07%,其次是西部地區(qū)13.16%,中部地區(qū)最低8.48%。從不同城市層級的生產(chǎn)效率變化來看,副省級及以上城市的生產(chǎn)效率累計提升22.74%,地級城市的生產(chǎn)效率累計提升16.55%,也呈現(xiàn)出層次性。可見,我國城市生產(chǎn)效率改進呈現(xiàn)出“馬太效應(yīng)”,擁有要素優(yōu)勢、政策優(yōu)勢以及區(qū)位優(yōu)勢的東部城市和大城市往往更有能力提升生產(chǎn)效率。
從規(guī)模效應(yīng)變化的區(qū)域趨勢看,各地區(qū)、各城市層級的規(guī)模效應(yīng)都呈逐年下降趨勢,累計下降程度均在30%左右。規(guī)模效應(yīng)變化也呈現(xiàn)出微弱的層次性,相反地,東部地區(qū)城市和副省級城市的規(guī)模效應(yīng)降低幅度較大,原因在于在規(guī)模報酬指數(shù)小于1的情況下,這些城市吸引和聚集了更多的投入要素,相比于其他地區(qū)投入要素的增長幅度更大,所以規(guī)模效應(yīng)下降更快。
從表4可以看出,樣本期間,資本要素對規(guī)模效應(yīng)的貢獻最大,占規(guī)模效應(yīng)的86.20%,土地要素占7.08%,勞動力要素占6.71%。可以看出,規(guī)模效應(yīng)的下降主要源于資本要素的貢獻。究其原因,資本要素產(chǎn)出彈性高達0.51,且樣本期間資本要素投入呈高速增長態(tài)勢,1998—2013年間,資本要素的年均增長率達到17.68%,在規(guī)模報酬指數(shù)小于1的情況下,要素投入增加使得規(guī)模效應(yīng)不斷下降。要提升全要素生產(chǎn)率,在要素投入方面要進一步縮減資本要素的投入量,調(diào)整投資結(jié)構(gòu),減少無效投資。
六、結(jié)論與建議
本文采用SFA的參數(shù)分析法來測算了1998-2013年全國223個地級城市的生產(chǎn)效率及全要素生產(chǎn)率,并對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變化進行了分解,在價格未知的情況下,將其分解為技術(shù)變化、規(guī)模效應(yīng)變化和技術(shù)效率變化。得到的結(jié)論有:
(一)1998-2013年期間,我國223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全要素生產(chǎn)率小幅下降,累計降低12.16%。究其原因,一是城市經(jīng)濟增長過程中的技術(shù)變化不顯著,這印證了克魯格曼“東亞經(jīng)濟增長完全可以用要素投入的增加來解釋”、“東亞經(jīng)濟的增長中沒有技術(shù)進步的成分”、“東亞無奇跡”的觀點。二是當前城市經(jīng)濟增長處于規(guī)模報酬遞減階段,要素投入逐年增加使得規(guī)模效應(yīng)逐年下滑,雖然生產(chǎn)效率總體呈改進狀態(tài),但是被逐年下降的規(guī)模效應(yīng)“抵消”了。
(二)雖然2008年之后技術(shù)效率有所下降,但是總體上技術(shù)效率呈改進的狀態(tài),樣本期間技術(shù)效率累計增長了17.08%,這主要歸因于我國的市場化改革、城市化進程和人力資本的積累。
(三)隨機前沿生產(chǎn)模型沒有通過技術(shù)變化的檢驗,說明在城市經(jīng)濟增長的過程中技術(shù)進步不顯著。本文認為全要素生產(chǎn)率所體現(xiàn)的技術(shù)進步是沒有蘊含資本投入的技術(shù)進步。如果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增長較低,只說明沒有蘊含資本投入的技術(shù)進步較低,蘊含在資本投入中的技術(shù)進步仍然是存在的(孔琳琳,任若恩,2005),而中國的技術(shù)進步可能被蘊含在資本投入的增長中。
(四)規(guī)模效應(yīng)是抑制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升的關(guān)鍵因素。規(guī)模效應(yīng)呈逐年下降的趨勢,樣本期間累計下降29.23%,規(guī)模效應(yīng)變化也呈現(xiàn)出微弱的層次性,東部地區(qū)和副省級城市由于吸引了更多的要素投入,規(guī)模效應(yīng)下降更多。將規(guī)模效應(yīng)分解為資本、勞動力和土地三部分,發(fā)現(xiàn)資本要素對規(guī)模效應(yīng)變化的貢獻最大,占到86.20%,原因在于當前城市經(jīng)濟增長中資本要素產(chǎn)出彈性高達0.51,且樣本期間資本要素投入呈高速增長態(tài)勢,在規(guī)模報酬遞減的背景下。過高的要素投入增長率使得規(guī)模效應(yīng)不斷下降。所以,開展供給側(cè)改革、調(diào)整投資結(jié)構(gòu),削減無效投資能有效地抑制規(guī)模效應(yīng)的下降,提升全要素生產(chǎn)率,至于減少哪些領(lǐng)域的資本投入,需要做進一步的研究。
中國城市經(jīng)濟增長進入規(guī)模報酬遞減階段之后,其增長也陷入了一個“怪圈”。投入驅(qū)動增長模式下不斷增加的要素投入使得規(guī)模效應(yīng)不斷下降,規(guī)模效應(yīng)的下降抑制了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提升,作為經(jīng)濟增長重要源泉之一的全要素生產(chǎn)率無法提升,則經(jīng)濟增長只能寄希望于要素投入,要素投入增加進一步降低了規(guī)模效應(yīng)和全要素生產(chǎn)率,經(jīng)濟增長方式轉(zhuǎn)變愈加無望。未來中國城市經(jīng)濟增長要實現(xiàn)良性循環(huán),開展供給側(cè)改革、調(diào)整要素投入結(jié)構(gòu),適當削減要素投入量,尤其是資本要素和土地要素的投入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