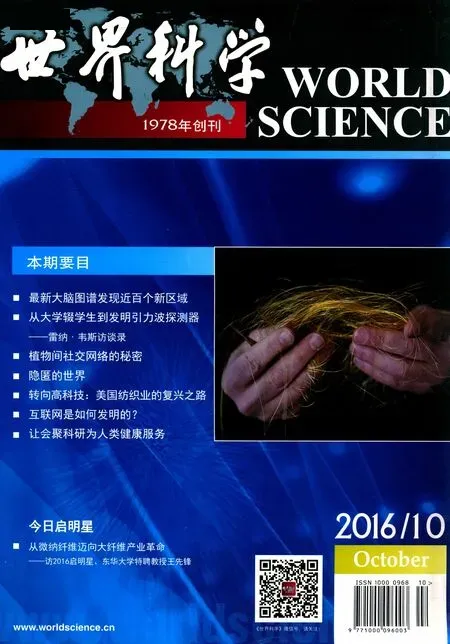植物間社交網絡的秘密
曹兵/編譯
植物間社交網絡的秘密
曹兵/編譯

最近的科學發現使人們對于植物之間的物質交換、分享甚至友誼的認識和理解提升到一個新高度
●在倫敦的艾坪森林,一位名叫梅林的科學家正在偷聽地底下樹木之間的竊竊私語。
艾坪森林是一處受到嚴格管制的地域。這片區域最初于12世紀由亨利二世發布敕令,成為皇家狩獵場。如果發現平民在這里偷獵,則會受到嚴重的刑罰。從1878年起,這個地方則轉為由倫敦市社團管理,它根據48條社團法規規范這片森林內的行為舉止。今天,這片森林的范圍則被完全限定在M25號公路內。M25號公路是環繞大倫敦區域的環形公路。森林內有小型道路穿過,整個區域的寬度很少超過4千米。森林內有一百多個湖泊和池塘,其中有幾個是1944年倫敦遭到V1炸彈轟炸時留下的爆炸坑。然而,艾坪森林的神奇故事依舊在上演。艾坪森林目前占據著將近6 000英畝的面積,區域內有各種樹木、荒地、草地和溪流,當地平民的牲畜可以在這里自由享用草地上的牧草,而蝰蛇則在林中空地享受著日光浴。盡管在各種用途間不斷切換——從高爾夫球場到山地自行車道——艾坪森林依然維持著其魔幻氛圍。
今年初夏,我在那里度過了兩天,徜徉于森林之中,和一位年輕的植物學家梅林·夏爾德雷克(Merlin Sheldrake)進行了暢談。夏爾德雷克是一位研究菌根真菌的專家。他的研究成果將改變我們對森林的認知。幾個世紀以來,人們一直認為真菌對植物有害,它們寄居在植物體內,引發疾病和功能障礙。然而最近的研究使我們認識到某些種類的普通真菌和植物存在著微妙的共生關系,不會帶來疾病的傳染,而會帶來各種奇妙的關聯。這些真菌會產生像蜘蛛絲一樣粗細的真菌管,稱之為菌絲,這些菌絲可以在土壤中穿梭,在分子級別和植物根部尖端相互交聯。植物的根和真菌相互結合,形成了所謂的菌根(mycorrhiza):這是一個復合詞,由意為真菌的mykós和意為根部的riza的兩個希臘詞根組成。由此,植物個體在地下經菌絲網絡相互連接在一起,這是一系列紛繁復雜的協作結構,我們稱之為樹林萬維網。
這些菌根真菌和植物相互聯接的關系,已經存在了很久(大約4億5千萬年)是一種共生關系——兩者都能從這種互聯中獲取利益。從菌根真菌來說,它可以從樹木汲取營養,獲得樹木在光合作用中制造的復合碳元素的糖類;而從植物來說,通過自身不能合成的酶,可以得到真菌從土壤中獲取的諸如磷和氮的營養元素。
但是,樹林萬維網的意義遠遠超過了基本的物質交換。真菌網絡也可以讓植物在不同個體之間分配資源——糖、氮、磷。一株死亡的樹木可以將自己的資源輸送給整個社區,或者處于大樹樹蔭下的小樹苗可以由此從其強壯的鄰居那里獲得額外的資源。更令人驚訝的是,網絡可以讓植物向彼此發送警告信息。一株受到蚜蟲攻擊的植物可以在蚜蟲到達周圍植株前提示其加強防衛。之前,科學家們已經了解到植物可以在地上通過空氣傳播的激素進行信息交換。但是,從來源和接受者來看,地下的這種菌根網絡要更加精確。
發現樹林萬維網的存在,并不斷揭示它所起到的作用,可以使我們了解物種的起源和消亡,把森林作為單一的超級生物體來看待,而不僅僅是一組獨立的個體群落,使我們更深入地認知植物之間的物質交換、分享甚至是它們的友誼。“如果我想簡單明了地向別人解釋我正在從事的研究工作,我只需告訴別人我正在研究植物的社交網絡就行了。”夏爾德雷克告訴我。
夏爾德雷克今年28歲,個子高挑、滿頭卷發。我們見面的時候,他圍著一條藍色渦紋花呢制成的圍巾,穿著無領羊毛夾克,背著卡其色帆布背包,背包上面釘著亮光黃銅扣。他看起來像是一位維多利亞時代走來的植物獵人,隨時準備好了進入叢林中探險。除了進行科學專業研究,夏爾德雷克還在一個名叫“溫柔秘密”的樂隊中演奏手風琴,樂隊的其中一首單曲名字為《蘑菇30 000》,屬于迷幻史詩風格,而樂隊的整體風格則匯合了各種音樂元素——東歐猶太民樂、嘻哈、電音以及滑稽模仿。一聽迷離,再聽癡迷。
作為本科生在劍橋大學學習自然科學時,夏爾德雷克讀到了一篇植物學家E·I·紐曼撰寫的論文《植物之間的菌根聯系:它們的功用及其生態意義》。在這篇論文里,紐曼大膽地提出了聯系植物的菌絲網絡的存在。“如果這種現象廣泛存在,”紐曼寫道,“那么,它將對生態系統的運行發揮著深遠的影響。”
這些新奇的論點深深地吸引著夏爾德雷克。他一直對真菌充滿了好奇心。在他看來,它們擁有超能力。他知道這些物種可以把巖石變為碎石,在地上和地下快速穿梭,在水平方向進行繁殖,通過向體外排泄酶消化食物。他已經知道它們的毒素可以殺死人類,它們可以合成精神致幻類的化學物質,使人進入迷幻狀態。在閱讀了紐曼的論文以后,他認識到真菌還可以讓植物在彼此之間進行溝通交流。
“所有這些樹木在其根部都生長著菌根真菌,”夏爾德雷克說,一邊指了指我們身邊屹立著的山毛櫸和鵝耳櫪,“你可以想象真菌本身在地下形成巨大的網絡,微小的管路在各個維向伸展,形成樹木的假體——繼續延展的根部體系,向外延展滲透入更深的土壤層中,獲取營養物質,然后輸送回至樹木體內;而植物的綠葉則固定碳元素,合成碳水化合物,輸送至根部,然后進入真菌體內。所有這一切正在我們腳下悄然發生。”
接著我們來到一片開闊地中央,數百株亮綠色的山毛櫸樹苗正在茁壯成長,每棵植株大概有幾厘米高,充分享受著陽光的沐浴。夏爾德雷克跪下來,清理掉落葉,露出一片盤子大的地方。他捏起一把碎土,用手指搓了搓:富饒的黑色腐殖質。“很難用實驗的方法來分析土壤,菌絲太微小無法用肉眼辨別,”他說,“你可以把根視系統埋入地下,觀察其根部的生長,但是你卻無法觀測到真菌的生長。當然你可以對地面以下進行激光掃描,但是這對真菌網絡來說還是太粗淺了。”
閃閃發光的棕黃色蜘蛛和黃銅甲蟲正在葉子上爭斗。菌絲將會在腐爛的葉子、原木和樹枝上分解物質以獲取食物,逐漸成長,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菌根真菌形成群落,夏爾德雷克說,一邊指著林中空地。除了滲透進入樹木根部,菌絲同時還互相滲透——菌根真菌無法從細胞層次互相分離。這種互相滲透可以允許基因物質在水平方向傳播,真菌通過無性繁殖就可以傳宗接代。夏爾布雷克解釋道。我試著想象土壤為透明的,這樣我的腦海中就浮現出真菌所組成的地下立體交通網絡,這些真菌像線一樣懸垂在樹根上,就像我們這個城市地下的網絡和光纖一樣。我曾經聽到過作家琪娜·米爾維爾(China Mieville)使用一個特別的習語來描述真菌世界:灰色王國。這個詞體現了真菌世界的另一面:它對我們平時所認識的時間、空間、維度和物種概念提出了新的挑戰。“你看著這些網絡,”夏爾布雷克說,“然后它也在回頭看著你。”
在漫步了2小時后,我們到了森林的邊緣,穿過M25號公路,翻過鐵絲護欄,到了一處看起來像是私人領地的空地上休息。我們倒不是迷路了,但是我們確實需要知道這片森林的范圍到底有多大。我在手機上查看了艾坪森林的混合地圖。一個藍點在我們所處的位置閃動。綠色向東南方向繼續蔓延,那里就是我們前進的方向,穿過繁忙的公路,進入森林深處,直至幾乎聽不到車輛的轟鳴聲。
當夏爾德雷克于2011年開始進行博士研究時,劍橋大學沒有一位導師涉足生物共生或者菌根真菌領域,所以他聯系了其他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他們來自瑞典、德國、巴拿馬和英格蘭。夏爾德雷克和這些專家建立起了一個研究菌根真菌的專家網絡。在博士研究的第二年,夏爾德雷克來到中美洲進行實地考察。他進入巴羅科羅拉多島,這個島嶼位于巴拿馬運河流域的加屯人工湖中。在那里,他加入到一位名叫小埃格伯特·基爾斯·李(Egbert Giles Lee,Jr)的美國進化生物學家所帶領的科學家團隊。

菌根真菌和植物互相聯結的關系自遠古時代就存在了,大約已經有4億5千萬年了
從方法學上來說,在島上所進行的某些科學研究充滿了危險。例如,夏爾德雷克把一位美國年輕科學家所進行的研究稱為“醉酒猴子假說”,這項研究嘗試收集猴子大量食用經過發酵的果實后排泄的尿液,以便評估這些尿液的毒素水平。夏爾德雷克在研究過程也面臨著自己的困擾和沮喪。他早期的工作就是把孢子樣品帶回實驗室進行篩選分析。每天面對的都是腐爛、蒸煮、固化和防腐,這樣的工作日積月累,不免逐漸開始讓人心灰意冷。他一直期望著能夠和所研究的真菌可以有更加直接的接觸。一天下午,他正在顯微鏡下觀察菌根真菌的孢子,他突然意識到它們看起來非常像魚籽醬。在經過幾個小時的清洗和篩分后,他已經有一堆“魚籽醬”了,他用鑷子把它們放在一小片餅干上,然后吃掉了這塊餅干。“孢子對人體真的很好,它們含有大量脂質。”他說。有時候他也會把這些孢子切成細絲,然后用鼻子吸入。
在島上進行研究的第二季,夏爾德雷克開始對那些依靠真菌獲得營養的植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它們通常被簡稱為真菌寄生植物。真菌寄生植物是一類缺少葉綠素的物種,無法進行光合作用,因此完全依賴于真菌網絡為其提供碳元素。這些非綠色植物潛入真菌網絡,從中汲取各種養分,卻不用付出任何回報,至少目前看起來是這樣的。夏爾德雷克說:“它們不遵守通常的共生原則,但是我們也無法證明它們就是寄生生物。”夏爾德雷克特別關注真菌寄生種群中一種名叫瓦龍膽(voyria)的植物,它們的花朵像淺紫色的星星一樣開滿了巴羅科羅拉多島的叢林。
人們對樹林萬維網的核心爭論在于該如何描述各種物種之間進行的交易。大家提出了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共享森林——樹木充當護理者,互相照顧,富裕的物種支持有需要的弱者;競爭森林——在一個充滿競爭的系統中,所有主體以自己的利益出發作出決定。夏爾德雷克喜歡瓦龍膽的原因之一是(他解釋道)因為它們還無法被人類充分認識,仍然處于十分神秘的狀態:“它們就是樹林萬維網的黑客。”
作為最好的植物學家,島上的當地居民作為助手和夏爾德雷克一起進行考察活動,對當地的土壤進行詳盡的統計,對數百種從綠色植物及瓦龍膽獲取的根部樣品進行DNA測序。這樣就可以使我們了解與植物相連接的真菌是什么種類,從而史無前例地繪制出叢林中最清晰的社交網絡地圖。夏爾德雷克掏出他的手機,在屏幕上向我展示了所繪制的地圖圖像。圖像中所展示的各種物種之間的微妙關系讓我想起了曾經試圖描繪全球因特網的努力:縱橫交錯的各色線條,如同煙花一般錯綜復雜。
我們停下來休息,來到一片古老松樹包圍起來的高地上,找到一塊干燥的地方,開始享用隨身攜帶的食物。夏爾德雷克帶了兩個芒果和一個菠菜餡餅。他喝著啤酒,而我帶了飲用水。在我們腳下,松樹根蜿蜒曲折,在我們四周爬行。他向我講述他在自家廚房臺面上建造的家庭實驗室,在自家花園架子上運行的小型釀酒廠。他使用蜂蜜釀造蜂蜜酒,使用三一學院內牛頓的蘋果樹上的果實釀造蘋果酒,命名為重力;使用唐恩宅里達爾文花園中的蘋果釀造蘋果酒,命名為進化。
當天晚些時候,我們來到湖邊,已經結塊發硬的爛泥凝固在淺水岸邊。鯉魚冒出水面呼吸新鮮空氣。水雞在水邊踱步,不時發出幾聲鳴叫。湖面偶爾出現幾個巨大的氣泡。夏爾德雷克和我坐在湖邊,凝視著遠方的落日。他告訴我,在發表了幾篇關于菌根真菌的專業論文之外,他還計劃出版準備這些論文背后所發生的各種千奇百怪的故事——現場考察時出現的幸運事件,使人靈光閃現的機緣巧合以及長期在外的困惑無聊和偶然相遇。兩位經過的遛狗游客打斷了我們的對話。一位滿懷期待的問我們:“你們知道游客中心在哪里嗎?”另一位說道:“我們迷路了。”“抱歉,我們也迷路了。”我開心的告訴他們。四個人做著最有把握的猜測,結果發現我們手頭的信息十分有限。他們失望地離開了。
[資料來源:The New Yorker][責任編輯:遙醒]
本文作者羅伯特·麥克法蘭(Robert Macfarlane),英國劍橋大學伊曼紐爾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