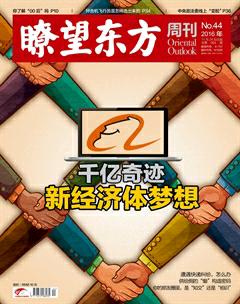蘇州河慢行空間的暢想
駱曉昀
一種新穎的解決方案被提出,即沿河打造棧道,繞過現(xiàn)有小區(qū)用地。
牡丹和馬達的愛情,始于牡丹跳河前那一句“我要化作美人魚”,最終,兩人酒后開著摩托車墜入上海的蘇州河。這是電影《蘇州河》里的故事。
大約二十年前,在這條河的兩岸,棚戶區(qū)叢生,林立了一個多世紀的廠房,早已失去了生氣,它們留給城市的是黑且濃稠、飄著生活垃圾的河水,還有空氣中飄散不去的腥臭。
那時跳入蘇州河,需要的可不僅僅是放棄生命的勇氣;而影片《蘇州河》里的美人魚,其映射的,不過是導演頭腦中的黑色幽默。
十多年過去了,如今的蘇州河呈現(xiàn)的是另一種模樣。經(jīng)過常年治理,以及公共開放空間的打造,這里或許已能吸引美人魚來居住。
華麗袍子上的虱子
吳淞江在上海的河段被稱為蘇州河,市區(qū)里的這段河流起于北新涇終于黃浦江,全長23.8公里。
相較于被稱為上海母親河的黃浦江的燦爛榮耀,過去的蘇州河更像是華麗袍子上的虱子:它穿越了整個城市,早期工業(yè)、商業(yè)以及民居生活皆是依河而生。這個城市不愿彰顯于人前的齷蹉、卑微與血汗,全都流淌在這條河中。
1844年傳教士羅當在書信中寫道:秋風一起,叢葦蕭疏,日落時洪瀾回紫。他描述的是當時蘇州河與黃浦江交匯之處的情境。當時,周圍星星點點的村落,散布于一片廣無邊際的稻田平原中。
彼時,上海開埠不過數(shù)十年。
挪威人漢驥于1912年在蘇州河畔開辦了一家名為斯堪的納維亞的啤酒廠,是上海第一家啤酒廠,釀造啤酒的用水便取自河中,可見當時的水流何其清澈。
后來,紡織、面粉、糧油加工、機械工業(yè)隨之而來,大批的工業(yè)企業(yè)在蘇州河沿岸聚集,眾多產(chǎn)業(yè)工人沿河而居,這里的人口開始高度集中。沿岸工廠視河道為露天垃圾廠,日日大量排放廢水、廢物、廢氣;居民更是習慣于將生活垃圾隨手棄于水中。
到1978年,蘇州河市區(qū)河段變得終年黑臭,河水呈現(xiàn)瀝青色,成了一條“死”河。
旅游開發(fā)的空間約束
1998年開始,上海市將蘇州河環(huán)境綜合整治作為一項實事工程、民心工程來抓,直至2005年,蘇州河才結(jié)束了27年魚蝦絕跡的歷史。
“上海市對蘇州河整體公共空間的打造計劃始于2004年,”上海市規(guī)劃設(shè)計院前總工程師蘇功洲告訴《瞭望東方周刊》,“不過,十年前的規(guī)劃未必能完全滿足現(xiàn)在的需求了。”
蘇州河市區(qū)段流經(jīng)長寧、普陀、靜安、虹口、黃浦等區(qū),黃浦、徐匯、長寧主體在南岸,楊浦、虹口、普陀主體在北岸,還有原閘北、靜安兩區(qū)“撤二建一”后新靜安區(qū)縱跨蘇州河。
經(jīng)濟基礎(chǔ)不同、人文環(huán)境差異以及交通瓶頸凸顯等歷史遺留問題,使得上海中心城區(qū)蘇州河南岸的經(jīng)濟規(guī)模、發(fā)展財力、社會事業(yè)普遍領(lǐng)先于蘇州河北岸,呈現(xiàn)“南強北弱”的局面。
2016年上海地方兩會上,就有與會代表認為,蘇州河沿岸的公共空間分割破碎,旅游開發(fā)面臨著空間上的約束。
一份提案說:蘇州河岸線沒有貫通,缺少足夠的濱河公共空間滿足旅游功能的開發(fā)。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蘇州河兩岸的住宅阻隔了蘇州河與城市腹地的聯(lián)系。住宅小區(qū)緊貼蘇州河河岸而建,散步的市民沒走幾步就會遭遇“死路”。
沿河而行,行不行?
修水是一個出生于1987年的IT開發(fā)工程師,從2012年到上海工作開始,他已經(jīng)帶領(lǐng)團隊徒步走過6次蘇州河市內(nèi)河段沿岸。
他向本刊記者介紹說,他大學畢業(yè)后在南京工作,2010年開始在豆瓣上接觸到南京“暴走團”,兩年后工作換到上海。
“當時上海沒有‘暴走團這樣的組織和活動,我與幾個相熟的朋友就在上海籌劃建立。來上海后的兩個月我們就開展了第一次活動。”修水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上海“暴走團”的受歡迎程度讓修水和他的伙伴有些吃驚,第一次徒步西藏南路沿線就有80人參與,而每次走蘇州河沿岸都有將近兩三百人報名參加。
“第一次走這條線路,是在人民廣場集合,先往外灘前行,再回頭走至華東師范大學結(jié)束。2016年‘五一前是最近的一次,我們從北新涇一直走到了外灘,走走停停加上拍照游覽,整段路程需要五六個小時。”修水介紹。

航拍的上海新靜安蘇河灣兩岸的城市景觀
“蘇州河其實是能全程走通的。”在修水看來,河上有那么多座橋,南岸遇見死路便跨橋而過走北岸,走不通了再過座橋走南岸。雖然有些路段沒有親水平臺,甚至望不到河,但河邊的老里弄和新興的藝術(shù)區(qū)都很有味道。“你可能離河有幾十米遠,但也算沿河而行吧,”修水說。
參加上海暴走團活動的成員大多為25歲至35歲這個年齡段,對他們來說,20公里左右的城市道路徒步不需要特別的訓練。
吳超站在長風國家大廈22樓的窗邊,他指著樓下那段蘇州河對《瞭望東方周刊》說:“我們也想打造沿河步道和健康跑道,雖然眼前這一段有親水平臺,但整個普陀段內(nèi)并未連成一線。”
吳超是長風生態(tài)商務區(qū)管委會辦公室副主任,他的工作地點和家都在普陀區(qū)的蘇州河沿岸,每天他都可以看見很多沿河而行的人,這讓他感受到了大眾的需求。
“附近很多居民,尤其是老人,都會沿著河邊散步鍛煉,他們在蘇州河北岸走兩三公里過橋至南岸,走一段再過橋回來,這個圈子大概有五六公里的距離。”吳超說。
在他看來,如果親水平臺能夠打造得更長一些,連貫性更好一些,將給附近居民提供更好的生活環(huán)境,而且普陀區(qū)境內(nèi)這一段蘇州河兩岸有著很多舊工業(yè)遺址,整體環(huán)境的提升,有利于這些遺址的旅游開發(fā)。
看得見歷史的河岸
過去,黃浦江帶給上海的是榮耀和財富,被迫開埠后,列強在黃浦江沿岸建起了具有各國特色的高樓大廈,使之成為當時最繁華之地;而蘇州河帶來的卻是沉重和辛酸,這里成為了列強建立的工業(yè)基地,運送資本和廉價勞動力的黃金水道。
現(xiàn)在,黃浦江留下的是萬國建筑群,蘇州河留下的是工業(yè)記憶。榮耀和辛酸,經(jīng)過歷史的沉淀,都是屬于這座城市的白描。
蘇州河工業(yè)文明展示館館長鐘經(jīng)緯向《瞭望東方周刊》介紹說,蘇州河市內(nèi)河段,各個地區(qū)的建筑有所不同。
比如,上游的普陀區(qū)和長寧區(qū)基本都是工廠;經(jīng)過華東政法大學和華東師范大學后來到了老靜安區(qū),這里的建筑是工廠與倉庫結(jié)合;再到老的閘北區(qū),其境內(nèi)基本是倉庫建筑;往下至虹口和黃浦區(qū),建筑則包括公用設(shè)施、民用住宅以及商業(yè)大樓。
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的上海史專家鄭祖安按照功能把蘇州河分為三段:東段集中著大量的公共建筑,包括當年各國的領(lǐng)事館、銀行、飯店、大戲院等,該范圍內(nèi)的老建筑大都比較高檔,很多依然保留著;河南路橋到恒豐路橋是中段,這里倉庫密集,有特色的西洋建筑也很多;恒豐路往西最早是外鄉(xiāng)人聚集的棚戶區(qū),后來是工業(yè)區(qū)。
國有企業(yè)改革后,廠區(qū)大多從河岸邊遷離。大多數(shù)的廠房倉庫被拆毀改建成商品房或綠化帶,但留下的建筑卻成為了蘇州河沿岸的地標。
上海西藏南路曾名虞洽卿路,虞洽卿是寧波商人,從歷史上看他是第一個有了“一河兩岸”概念的人。他曾獨自出資兩萬銀元,在蘇州河上造了浙江路橋,連接兩岸發(fā)展,開發(fā)了海寧路那一大片房地產(chǎn),并從中牟利。2015年,浙江路橋重修后再次開放。
在淞滬抗戰(zhàn)中聞名全國的四行倉庫位于蘇州河原閘北區(qū)境內(nèi),現(xiàn)已成為創(chuàng)意園區(qū)。四行倉庫創(chuàng)建于1931年,由“北方四銀行”即金城、中南、大陸、鹽業(yè)銀行共同出資建設(shè),這也就是“四行”兩字的由來。“八·一三”淞滬會戰(zhàn)中,“八百壯士”的“四行倉庫保衛(wèi)戰(zhàn)”使這里一戰(zhàn)揚名。
沿北蘇州河路向西步行即到四川路橋頭的郵政大樓,現(xiàn)在仍是上海郵政局的所在地,也是上海郵政博物館。這里原名上海郵政總局,1922年由協(xié)澄洋行設(shè)計,辛豐記營造廠施工,曾列為當時上海十大建筑之一,也是中國近代郵政的發(fā)祥地之一。
“從外灘源到河濱大樓,從M50創(chuàng)意園區(qū)到夢清園生態(tài)公園,從上海鑄幣廠到原圣約翰大學和原大夏大學,從上海化工研究院到上海火柴廠。蘇州河沿岸這20公里,優(yōu)秀歷史建筑和景點眾多。”鐘經(jīng)緯說。
一種新穎的解決方案
蘇功洲最近完成的規(guī)劃是關(guān)于新靜安區(qū)蘇州河兩岸的公共開放區(qū)的打造與貫通的,他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十三五期間,蘇河灣地區(qū)主要奮斗目標是,通過全力打造蘇州河兩岸人文休閑創(chuàng)業(yè)集聚帶,建成發(fā)展能級更高、綜合實力更強、空間形態(tài)更優(yōu)、城區(qū)環(huán)境更美的智慧、人文、低碳、卓越的‘都市之心,并成為推動靜安南北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引擎、蘇州河兩岸融合發(fā)展的新標桿。”
這份規(guī)劃提到:加強“一河兩岸”聯(lián)動發(fā)展加強公共空間網(wǎng)絡(luò)打造,增加濱河道路的慢行空間,形成沿蘇州河及昌平路、曲阜路軸線的慢跑道,打造綠地成系統(tǒng)、慢行成網(wǎng)絡(luò)、樓宇成組群、地下空間互聯(lián)互通的公共空間網(wǎng)絡(luò)。
而慢行網(wǎng)絡(luò)、親水平臺的打造,首先要面對的問題便是緊緊臨河而建的住宅小區(qū)。部分沿河路段沿岸遍布住宅小區(qū),如何從中建立面向社會大眾的慢行步道成為難題。
“蘇州河上游,北岸是普陀區(qū),南岸是長寧區(qū)。長寧沿河兩岸基本都已是住宅小區(qū),其保留的歷史建筑較少。即使在普陀區(qū),也有像中遠兩灣城這樣的大型小區(qū)沿河而建,而使用小區(qū)現(xiàn)有用地來打造大眾慢行步道和親水平臺,則相當困難。”鐘經(jīng)緯說。
上海市規(guī)土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相關(guān)人員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在已經(jīng)出臺的黃浦江兩岸貫通方案中,也遇到了同樣的難題,后來一種新穎的解決方案被提出,即沿河打造棧道,繞過現(xiàn)有小區(qū)用地。“這個提議為很多被相同問題困擾的區(qū)段所追捧。”這或許也是解決蘇州河兩岸貫通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