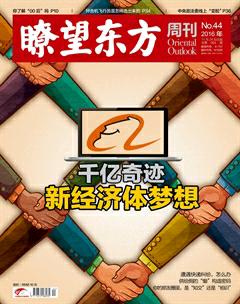地鐵丟書遭遇“水土不服”
鄭帥
這些書本就像在大學教室占座的標志物,“神圣而不可侵犯”。
2016年11月15日早8點,演員黃曉明在北京14號地鐵里丟下了他選擇的 16 本書,并在每本書里夾了一張留言條。
這是由新媒體公司新世相發起的“丟書大作戰”活動,吸引了多位明星參與。在北京、上海等地的地鐵、航班、順風車上,10000本書被隨機放置,等待后續乘客的翻閱、借讀。讀完的書籍會被乘客送回地鐵空座,再次等待下一個乘客的接力。
與此伴隨的是“新世相”轉發的一篇名為《女神赫敏在地鐵里丟了本書,結果整個倫敦讀瘋了》的文章。沒錯,這次丟書行動原產自英國倫敦——電影《哈利·波特》中赫敏有一個在火車站丟書的橋段,這啟發了英國人,后又因為明星的加入,助推了丟書活動的普及。
“新世相”通過與英國主辦方協調溝通,順利獲得了地鐵丟書活動的中國“版權”,于是才有了我們眼前看到的一切。
其實,“地鐵丟書”最早可追溯到2009年的倫敦——兩個英國青年以地鐵為據點,發起了“選擇你的讀物”的活動,實現了大量書籍在地鐵乘客中的流通。
這類活動旨在分享閱讀體驗、傳遞知識、鼓勵人們利用通勤時間讀書,往往在發起之初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但當“地鐵丟書”引入國內,卻遭遇了“水土不服”。中國先行者張旭明,曾經作為國內最早的地鐵丟書人在廣州市地鐵里試驗,卻以失敗告終。9本精心挑選的讀物幾乎無人問津,這些書本就像在大學教室占座的標志物,“神圣而不可侵犯”。
而“新世相”發起的丟書行動,在國內同樣遭到“冷遇”:無人領取的圖書被堆放在地鐵站地面一角,因違反了禁止在地鐵堆放“雜物”的相關規定,被保潔阿姨清收丟棄。
其實,從參與者的角度來看,活動本身很有價值,不再是簡單照抄國外流行時尚。“地鐵丟書”不僅僅是將“圖書漂流”移植進了地鐵,更大程度上,它滿足了一部分理性人群的知識分享心理,也迎合了一部分人的全民娛樂精神。這種有一定神秘感卻又默契配合的地鐵丟書活動,傳遞的是一種人文關懷。渴望交流的都市一族,在冷漠、快節奏的城市生活中,尋覓到了來自社會角落的溫暖。
但是,讓地鐵丟書持續下去的先決條件,不是活動主辦方或參與其中的地鐵乘客,而是社會長期積累形成的良好群體性閱讀習慣,以及這種習慣衍生出的對書本的珍視與愛惜。
面對窘境,我們似乎也有“難言之隱”。中國城市異常擁擠的地鐵空間,似乎讓地鐵里的實體書閱讀成了“多余”之舉。選擇手機碎片化閱讀或沉默放空,或許成了多數人打發漫長旅途的方式。
目前,也有一種新型的地鐵文化創意模式,被認為在中國更為可行:單向空間與京港地鐵合作,將精心挑選的文學大師的句子,印刷成精美的海報,張貼在北京地鐵4號線、14號線的車廂內部。乘客們在車廂內片刻的停留注目,即可轉化成有力的思考。喜歡某個書目,還可以通過掃描二維碼,獲取書籍信息。
這樣精簡的知識分享方式,更像是一種微縮版的“圖書漂流”,讓乘客們在旅途中各取所需。
地鐵文化,已在現今城市文明的發展浪潮中逐漸豐富起來。傳統車站意義上的公共空間,顯然已經無法滿足我們對地鐵的定義。地鐵文化,既代表著城市的過去,也代表著城市的未來。

2016年11月15日早8點,演員黃曉明參加了“丟書大作戰”活動
在全球140余種地鐵系統之中,堪稱文化與造型設計典范的地鐵站比比皆是。其中不乏被人稱為“地下藝術殿堂”的莫斯科地鐵、頭頂設計成星辰大海的那不勒斯地鐵,以及在基巖上有大量繪畫的斯德哥爾摩地鐵。這些地鐵從硬件架構出發,實現了地鐵文化的顯性表現。那些堪稱藝術品的雕塑繪畫,構成了另一道文化景觀。
除了“觀賞”功用很強的地鐵站,打造車廂里的文化軟實力,亦是未來地鐵文化的發展方向。譬如美國地鐵會為乘客提供當日最新的報紙和書籍。德國、瑞典的地鐵,是陌生人交朋友的場所。在許多歐洲國家,地鐵還是表演藝術者的溫床。在文化宣傳上,墨西哥地鐵還曾為對抗肥胖現象,推出了“做10個深蹲,就能免費乘坐地鐵”的活動。這些地鐵文化在“軟件”上的創新,為我們提供了現實性的參考。
近年來,國內的地鐵文化也有可圈可點的表現。西安地鐵主打古城文化,古色古香的車標、站標、文化墻,形成了獨特的西安風景線。武漢地鐵發放地鐵文化珍藏票,該票可以用于乘車,并具有藝術收藏價值。無錫地鐵則推出攝影長廊,展現無錫文化本源,同樣使地鐵在城市文化的展現上,邁出了一大步。
地鐵本身的存在,就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面對層出不窮的地鐵文化現象,如何引領乘客去接納并進一步創造,還要看一座城市的文化內核有多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