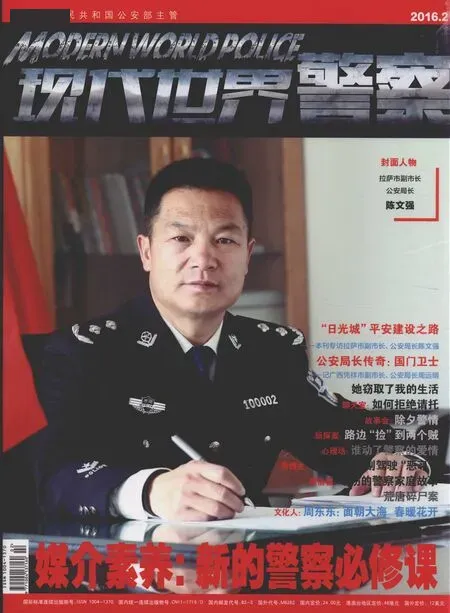憂國憂民是同心
文/陳琳
大家談
憂國憂民是同心
文/陳琳

陳琳,鳳凰衛視記者。在新聞一線工作近十年,主要從事時政報道、重大突發事件報道,重要報道經歷包括利比亞內戰、日本大地震等
警察與記者,本就是社會上最憂國憂民的職業之二,所謂“地命海心”,雖然說法極難登大雅之堂,但卻顯示了這兩個職業的從業者、尤其是基層從業者的堅守。
同是憂國憂民,有時在新聞現場,記者與警察卻免不了過招。一提“涉警新聞”,公安部門高度警惕,也是真實寫照。看報道說,幾年前,重慶曾經邀請記者與警察辯論涉警報道的底線,凡事一說到“底線”。那就大了,說明分歧不小。
警方如何應對媒體,這在警界、傳播界已有不少專論,民間輿論對此也不乏置喙。筆者在此,謹以自己供職鳳凰衛視近十年的新聞實務操作經驗,略談感受。
其實“涉警報道”尚無嚴謹的定義,從廣處說,由警方參與處置的突發公共事件也是涉警報道的一種,這也是鳳凰衛視作為市場化的專業新聞媒體涉獵最廣的一類涉警報道。大災大難之前不必多說,盡管也有救援工作不盡如人意等負面消息,但更多的還是警方與媒體精誠合作,新聞報道源源不斷。但有一些突發公共事件,尤其是“人禍”因素更多的時候,一線記者與警方的沖突屢屢爆發。不少現場執勤警察拿記者當洪水猛獸,記者則急于搬走擋在真相面前的大石頭。
警察維持現場秩序,這是天職,但造成警、記沖突,就在于一個詞——“禁止”。當警方把維持秩序等同于禁止,禁止事件主角的正當訴求,禁止記者的現場報道行為,也就成為了新聞報道的攔路虎。由于這種新聞事件現場的復雜性、利益的多頭性,有時候,警察卻成為記者在現場所能面對的相對強勢一方的“第一線”,這種位置錯置往往造成報道中出現對警方不利的內容。警方既然是秩序維持者,如果能把“禁止”化解作“有用指引”,則有利于緩和這類涉警報道的矛盾。哪些允許媒體采訪,哪些媒體不得入內,在事件當事的強勢一方缺位的時候,警方可以智慧應對。


發生在2010年北京和平里的一次火災,由于微博等即時媒體的傳播,這次著火事件迅速引起民眾關切,筆者的報道組帶著“現場直播、連線”的任務前往事發地點,而警方已經在現場拉起警戒線,所有“無關人員”不得接近,筆者也被攔在兩公里之外。其實,筆者趕到時,明火已經被撲滅,而筆者與眾同行在幾公里之外,得不到警方的權威信息,只能憑借遠遠看到的滾滾濃煙估計火勢,周圍偶有居民愿意駐足講述,也難免有夸大其詞者。老實說,這樣的報道,對于已經在即時社交媒體上引起廣泛關注的消息是有隱患的,事實上,在鳳凰衛視的報道之前,已經有一些微博評論難以克制。而在新聞傳播業發達的國家,每遇到此類事件,一定可以看到警戒線外有警方的發言人第一時間回應媒體詢問,并不斷根據現場進展更新信息,避免消息誤傳、誤報。從傳播學的角度講,對于這樣的事件,公眾有極度饑渴的知情欲望,需要更多消息構筑自己的信息安全網,判斷自己是否安全、如何應對,所以第一時間發布權威消息、防止傳播后患尤為重要。小事件如此,大事件更是這樣。而且,對視覺內容需求發達的當下,媒體不僅需要警方有發言人第一時間發聲,還需要拍得畫面。如果警方不能第一時間回應訴求,等整理好口徑、剪好素材分發給友好媒體,會發現,新聞熱點可能已經轉向,被湮沒在新聞洪流之中。這不是說,此類信息警方不回應反而“政治安全”,恰恰相反,當再有此類事件發生的時候,輿論會發現,民眾對于上一次事件的回憶被再次激發,由于之前沒能第一時間獲知消息,更加重了不信任感,會波及下一次事件以至以后的事件,這必然影響到對警方公信力的樹立。
2011年的故宮失竊案。筆者第一時間獲知犯罪嫌疑人的信息,鳳凰衛視成為最先發出相關新聞的媒體。這次報道體現警方的信息開放,在業界評論中引發積極的議論。可見此類涉警報道,于警方利多還是弊多,主動權在警方。第一時間發掘真相是記者的天職,在程序正義的前提下不阻撓新聞的傳播,是警方的社會責任。
每每有警方同仁言及警方、媒體“化敵為友”,筆者都生出“憂國憂民是同心”的呼吁。寫此文,下筆如有鬼,筆者笑言,是怕得罪親人。因從業十年,多與警方合作,雖有過齟齬但更多是精誠。家人勸筆者寫以“春秋筆法”,筆者倒覺得,既然同心,不如坦誠道吾怨、吾愿,同心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