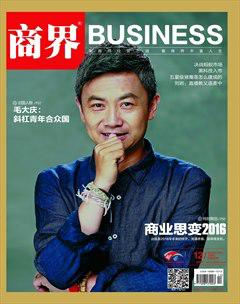萬科大事件:陽光下的金錢戰爭
江湖中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種對萬科事件的解讀。寶能、恒大收購萬科案,讓監管層看到了監管,管理層看到了公司治理,資本方看到了市場規則,投資者看到了股東權益保護……事件本身已經超越任何一方的輸、贏,而成為我們反思公司治理與資本市場法制的一個重要歷史節點。
我們仍有必要簡要回顧萬科事件:2015年7月到12月,寶能系七次舉牌萬科,以24.29%坐穩第一大股東,萬科管理層以緊急停牌、籌劃重大資產重組事項抵制寶能系;2016年6月,萬科管理層試圖引入重組方深圳地鐵,被寶能系及華潤反對;從2016年8月起,恒大連續買入萬科,成為新的角逐勢力。
尤其是2016年發生在萬科董事會里的博弈對抗,已將尚可想象的“野蠻人入侵”演變為事關中國資本市場游戲規則發展走向的一場維度戰爭。

正義讓位法制
萬科事件萬眾矚目,并不單純因其體量龐大,事關中國第一大房地產企業的權力爭奪,而在于它的任何一種角度都能牽動大眾的神經:王石及管理團隊有反收購的權利,寶能系與恒大有收購并重組董事會的權利,華潤也有反對董事會作出稀釋大股東權益的權利。企業家情懷、資本利益、股東權益相互交織在一起,形成了目前多方勢力難以共贏的僵持局面。
慶幸的是,面對各種爭議,各方總體尚能在依法合規的框架內行事,政府及監管部門也保持了基本的冷靜與克制。這要比過往許多不透明、不合規的上市公司利益爭奪陽光許多,實屬市場的進步、各方參與主體的幸事。
評價萬科事件,吳敬璉教授的一席話切中要害:
正義的判斷每個人都會不一樣,而且是無解的。但規則只有一個,即《公司法》所規定的規則,證監會所規定的規則,這才是所有人都應該遵循的。
對于王石,他自然飽受委屈,郁結難抒,很能代表一批情懷企業家的價值觀。難能可貴的是,王石在事件中也秉持了萬科管理層一貫的高水準,始終維護萬科品牌價值、核心資源。但是,他張揚的個性,有意無意表現出的“傲慢”,都不利于管理層處理與原大股東、收購者之間的關系,也把自己放在了不利的位置。
以王石為首的萬科管理層的遭遇,事實上重申了公司治理兩大不可撼動的規則。第一,所有者和經營者分離;第二,專業的管理團隊要代表資本所有者利益—終于,王石因改制時不按照現代公司通用做法確保創始人控制權,而遭遇如今的大權旁落。血一般的事實敲打著所有企業家,在競爭激烈的資本市場,最終有話語權和控制權的只能是資本,而不是情懷。
對于寶能系、恒大,以及后來站到管理層對立面的國資華潤,無論他們的行為在王石的擁躉們看來是多么的粗暴、野蠻,卻也大體遵循了法規章程。尤其是寶能系,儼然一個絕世高手,比如游走于要約收購邊緣、嚴格依照保監會相關放行條款展開收購、借《公司法》第148條董事勤勉義務大做文章等行為,都屬于最大限度地發揮法規賦予其的權利。同時,寶能系的“入侵”后來被更多人認可,也是源于其發現了萬科內在價值和市場價值之間的差價,并以相當于向其他股東支付真金白銀的方式成為了第一大股東,完成了中國資本市場久違的價值發現功能。
然而,在規則許可的范疇內,寶能系提出罷免萬科董事會的議案,華潤對重組案曖昧的表態,都著實讓人為管理層感到心寒。在最緊張的時刻,竟然只有部分獨董站到了公司利益的角度,冒著涉嫌違規披露的風險,以在公開媒體上發文“心路歷程”的方式捍衛萬科管理模式,這其實就是一幕悲劇。
依法而行卻不能實現共贏,甚至出現驅逐創始人、折損公司利益的現象,恰恰反映了相關法律法規的缺陷,或可謂之“有理取鬧”。
對于那些試圖推廣混合所有制的國資管理方與民營企業家,那些試圖以知識向資本換取實際控制權的“王石們”,還有那些已經嶄露頭角的“寶能系們”,萬科事件的善后工作都亟待回答一個尖銳的問題:萬科案中包含的各種“不合理”,都只是個案而非潛規則。
審視制度性漏洞
由萬科事件的“不合理”所泛起的諸多思變,將在未來產生更深遠的影響。
1.資本善惡
周其仁、劉姝威等專家指出,英雄不問出處,英雄的錢卻要問出處。寶能系收購資金涉及萬能險及高杠桿,監管層有必要防范資金錯配和流動性風險。
更大的漏洞在于,萬能險所購股份是否具備投票權,保險公司是否可以代表萬能險賬戶行駛股票持有人權利等問題,在目前的《保險法》《證券法》《基金法》《公司法》《信托法》《合同法》中都沒有明確表示。這極易導致“監管套利現象”,促發險資運用多個金融工具實現跨界,在監管邊界大打“擦邊球”。
同時,中國資本市場對同股同權、一股一票的執著也讓“王石們”沒有閃轉騰挪的空間。與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京東的A、B股設置相比,持股極少的萬科管理層相當于資本待宰的羔羊。
如何實現投資需求、經濟民主、資本邏輯與金融寡頭防范之間的有效平衡,借由萬科事件已經成為擺在監管層、立法界面前的一道考題。
2.獨董不獨
幾位萬科獨董的選擇意外地引起軒然大波,暴露了目前獨董制度的混亂。
在中國,獨董基本由大股東提名,薪酬由上市公司支付,造成獨董不獨抑或獨得不夠硬氣。在萬科事件中,甚至還存在有違“不關聯獨董、獨董不關聯”原則的獨董,這在股權分散的上市公司中簡直是災難。
萬科事件掀起了獨董制度改革的思潮,核心議題即獨董要獨。法律界寄望于證監會出面,組織第三方成立獨立董事工作委員會,根據不同上市公司特征從“獨董庫”中選派合適的獨董;上市公司有權否決人選,但大股東不具有提名權;獨董薪酬由證監會或第三方支付,不能從上市公司獲取利益;最后,對獨董失職的追責法律條款也亟待完善。
3.王石謂誰
王石與萬科的關系判定,不但影響萬科,也能決定格力、伊利、廊坊發展、南玻A等上市企業高管的命運。
如果遵循規則,認定王石及其團隊是職業經理人,那么無疑否定了“先有王石才有萬科”的客觀歷史。如果考慮王石是一名企業家,如何制定公平合理的契約,保證有利的一方不利用法律制裁不利的一方,又成為公司治理的關鍵一環。
契約文明與企業家精神,猶如硬幣的兩面讓人難以抉擇,前者導致官僚主義,后者引發內部人控制,皆不能偏頗。
事實上,萬科事件已經掀起漣漪。伊利股份于2016年8月修改了11條公司章程,從否決權設置、賠償設置、董事提名限制等多個維度強化董事會權力。其中部分修改涉嫌與《公司法》沖突,證監會緊急問詢其合規性,又引發了市場對公司治理邊界的大討論。
萬科事件已不局限于萬科。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邊界、國資在特殊時刻的保值策略、股東與股民利益的劃分、公司治理與控股權的平衡等問題亦在不同維度展開激烈的思辨。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萬科事件之后,中國資本市場將迎來新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