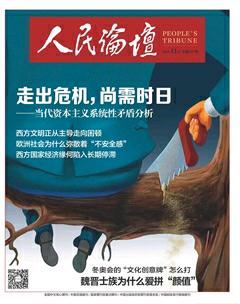英國新左派文化批評的安德森印記
賴永兵
【摘要】佩里·安德森的文化批評實踐是英國新左派文化批評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以國際化和超越資本主義為文化批評的價值取向,通過編輯《新左派評論》雜志搭建起反權力文化堡壘,在“西馬”的理論旅行中發揮著承接轉換的作用,他的文化批評實踐也為中國式文化批評提供了啟發與示范。
【關鍵詞】西方馬克思主義 文化批評 新左派評論
【中圖分類號】I06 【文獻標識碼】A
形成于20世紀50年代末的英國新左派素以文化批評見長,老一輩如霍加特、湯普森、威廉斯等,新生代如霍爾、伊格爾頓等,都是卓有建樹、舉世公認的文化批評大家。相較而言,在英國新左派群體中表現同樣耀眼的佩里·安德森開展的文化批評實踐卻并未引起足夠的關注和重視。就此,筆者試圖對英國新左派文化批評的安德森印記予以概括式“標注”。
安德森的價值取向:國際化與超越資本主義
自20世紀60年代初開展文化批評實踐以來,敢于打破偏狹保守的英國民族文化傳統,是安德森作為英國新左派成員最為鮮明的特點,他所注目的絕不限于單一的民族文化或國家,“他的思想并不對特定民族傳統效忠;其思想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中一個流動著的主體”。在其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中,安德森始終秉承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國際化路線,不僅推動英國反資本主義制度學生運動的蓬勃發展,而且促進社會主義運動在全世界的興起。安德森在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批判中就曾鮮明地強調了“國際主義”的重要性:歐洲各國的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彼此間缺乏溝通,就在于它們最為突出和最自相矛盾的特點之一——缺乏國際主義,這種缺乏是對經典馬克思主義原則的重大背離。
更進一步來看,在這種國際化的文化批評道路上,“安德森鏡像中呈現出的任何角色的身份都揭示了一個貫穿生命始終的忠誠信念:國際社會主義文化與政治事業”。立志成為資本強權終身“反對派”的安德森曾在一次與中國學者的對談中對這種忠誠信念做過明確的宣示:一是“鋤強扶弱”,聲援廣大第三世界的去殖民化斗爭;二是“絕仁棄義”,揭露西方國家的偽善民主與武力法則;三是“超越資本主義”,期待一個超越資產階級、超越資本的世界。顯然,安德森的上述價值立場是西方新左派學術語境下一種典型的文化政治話語,本質上是通過文化意義上的聲援、揭露及期待等理論立場和批評方法,展現出對權力、對資本意識形態的抵抗路徑與僭越策略。
搭建反權力文化堡壘:安德森的編輯事業之功
作為英國新左派的機關刊物,誕生于1960年的《新左派評論》在文化批評實踐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從1962年開始的幾十年間,安德森都是這份刊物的掌舵人,他通過大膽革新《新左派評論》,為英國乃至西方的思想左派搭建起持久性的反權力文化堡壘。在西方左派文化思潮處于高潮階段的20世紀60年代,作為英國新左派后起之秀的青年安德森面對保守的英國左派堅定地發出“我們不相信馬克思主義僅是一國的事情”的聲音,一改《新左派評論》運營初期僅僅專注于英國國內左派文化研究和政治運動的局限,將文化政治眼界擴展到歐陸及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從歐陸國家批判性引入葛蘭西、薩特、阿爾都塞等學者建構的更具理論色彩的馬克思主義文化觀念,以巨大的熱情關注和評論發生在古巴、阿爾及利亞、越南等第三世界國家的反殖反霸斗爭,同時對“五月風暴”等出現在歐美國家內部的青年學生運動給予支持和同情。
為有效策應上述革新舉措和理念,他還從學理層面總結和反思了英國傳統社會文化的歷史、現狀及其背后的權力關系,寫就堪為一對“姊妹”的兩篇文化批評論文——《當前危機的起源》和《民族文化的構成》。安德森此類策應式文化批評實踐一直延續到70年代中期,其標志性成果是問世于1976年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進入20世紀90年代,冷戰格局的終結令西方思想左派遭遇來自新自由主義文化思潮的強勁挑戰,《新左派評論》這一西方世界反權力文化堡壘的運營亦面臨困境。在此背景下,讓出主編職位已有多年的安德森再次走上編務前臺,以“更新”(Renewals)的名義醞釀并實施了從新千年第1期開始的改革舉措:中斷自創刊以來的連續期號,從2000年1月開始雜志2.0版的第1期;改變雜志封面裝幀格調;建立雜志網站等。當然,更關鍵的“更新”在于提出新的編輯理念——“不妥協的現實主義”,即在堅持反資本權力價值立場的基礎上,采取務實的精神看待和分析新自由主義占據主導地位的西方乃至全球文化意識形態現狀,并加大對中國等全球化新興市場國家和中東等熱點地區的考察評論,展現出更加成熟穩健的批評風格。
“西馬”的理論旅行:安德森的承接轉換之功
依托于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以及不斷精進的理論涵養,安德森的文化批評實踐立足英國社會文化現實,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先后致力于英國本土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化和整個歷史唯物主義文化傳統的開掘拓展,為進一步發展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事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承接轉換作用。這種承轉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理論的榮景之所以能夠從意大利、法國、德國等歐陸國家接力轉移至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英語國家,與安德森主持《新左派評論》編務工作打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英語傳播通道有著直接的事實關聯;其二,安德森在具體的文化批評實踐中有效整合經典馬克思主義、英國馬克思主義和歐陸馬克思主義三大歷史唯物主義文化傳統,并以此為依據從西方社會歷史和現實中透析了文化與權力的互動結構及其意識形態功能指向,進一步豐富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內涵。
安德森善于將基本理論問題與具體經驗問題結合起來,一改西方馬克思主義流行的文化-意識形態批判路徑,恢復經典馬克思主義傳統,以歷史唯物主義為基本理論立場和核心批評尺度,從政治-經濟批判立場出發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與現實進行闡釋,并在此基礎上探尋相應思想文化的特征及功能演變。無論是在討論包括葛蘭西文化霸權學說在內的整個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利弊得失,還是在解讀新自由主義、后現代主義等當代資本主義文化政治思潮的政經本質,他都靈活踐行著這種歷史唯物主義的批評方法與路徑。
文化批評中國化:安德森的啟發示范之功
對于當代中國及中國式文化批評來講,安德森的文化批評實踐不無啟發和示范價值。在當代中國文化語境中,安德森是一位令人肅然起敬的西方學者,自稱“葛蘭西信徒”的他始終致力于成為一名捍衛馬克思主義、超越資本主義的有機知識分子,不僅要深入地解釋世界,還要真正地改變世界。事實上,中國光譜也從未離開過安德森的文化批評視線:20世紀60年代對中國時政信息的傳播,20世紀70、80年代將中國作為審視歐洲社會歷史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參照,90年代直接以中國的歷史與現狀為批評對象,2000年之后則開始更多地實地觀察中國、思考中國,進而在中國出席論壇、發表文章、接受訪談等。其文化批評實踐中的這些中國印記本身,無疑為清晰把握當代中國社會文化發展狀況及前景提供了一種難得的參照視野和鏡鑒。
特別值得重視的是,當前的中國社會正在經歷著工業化、市場化和城市化改革帶來的巨大變遷,市民社會日趨成熟,以往盛行于西方的后現代主義、新自由主義等文化思潮及其具體生活表征在中國已非鮮見,對于如何抵御和化解由此造成的諸多風險,安德森站在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上靈活應用歷史唯物主義思維方法,深度解析西方文化思潮及其在當代中國的“落地”狀況的文化批評實踐,無疑是極具現實針對性的善謀良方之一,亦可為中國文化研究培育自己的思想文化“能量”,發揮不可多得的實踐價值與啟示。
(作者為重慶三峽學院副教授)
【注:本文系重慶市社科規劃項目“佩里·安德森與英國文化研究的范式轉換研究”(項目編號:2015BS083)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Edward Skidelsky. “ The NS profile: Perry Anderson”, New Statesman,Mar 19,1999.p.18.
②佩里·安德森著、高铦等譯:《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③甘琦:《向右的時代向左的人——記佩里·安德森》,《讀書》,2005年第6期。
責編/高驪 溫祖俊(見習) 美編/宋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