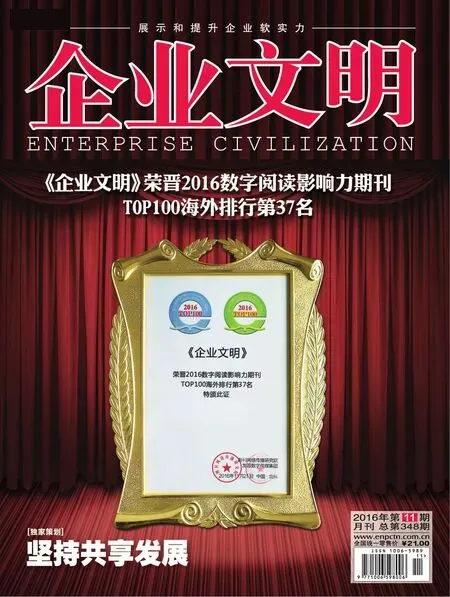共享發展理念的微觀釋義
文/徐艷梅 楊 雯
共享發展理念的微觀釋義
文/徐艷梅 楊 雯

徐艷梅個人簡介
中國科學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管理科學專業教學及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戰略管理、技術創新、組織生態。現任中國技術經濟學會理事,日本東京理科大學客座教授。
主持國家、省部及企業課題30余項,出版學術專著7部,在國內外核心期刊發表論文百余篇。向多家大中型企業提供管理咨詢。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以平均9.4%的速度增長,綜合國力大幅提升,發展成就舉世矚目,被世人稱為“中國奇跡”。但是,與此同時,一系列與發展相伴而生的矛盾和問題也越來越凸顯:激烈競爭形成的貧富分化和發展不平衡,人生、人性的貨幣化和對金錢的崇拜,企業的外部性造成的環境污染和破壞等。
市場經濟廣泛建立并快速發展的同時,其內生本質必然在社會生活中被普遍外生化,從而誘發消費主義、物質主義、拜金主義和極端利己主義等。基于對市場經濟上述本質的深刻認識,市場經濟理論的鼻祖亞當·斯密在完成《國富論》的寫作之后,又有《道德情操論》一書出版。足見正義理念在市場經濟建設中的不可或缺。
在深刻總結國內外發展經驗教訓及發展趨勢的基礎上,針對我國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并強調“共享發展”是社會發展的歸宿與目標。
共享本質上是對迄今為止人類所創造的一切物質與精神財富的平等擁有權利的要求,是對特權與私人獨占的一種否定意識,是一種倡導人與人之間應該相互關愛、共享美好生活的公共情懷。共享意識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淵源深厚,如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天下大同、家國一體的思想觀。儒家強調“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儒家對“仁”的本質闡釋是“天地、萬物、人倫之和諧”。此外,還有道家的物無貴賤,佛家的眾生平等,墨家兼相愛、交相利思想等等。
綜上,無論歷史流源中的各派先賢,還是當下的最高決策層,都將共享發展視為歸宿及目標,強調其不可動搖、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但這里所指的共享發展均為宏觀層面的內容,重審的是戰略層面社會發展的綜合平衡、總體均等,這也是中國文化敘事宏大、目標高遠的特有體現。但宏觀層面共享發展目標的實現,必是以中觀、微觀層面上的實現為前提的。現實中,微觀層面共享發展理念其實也具有重要的辯證內涵和實踐空間。共享發展不僅包括組織單元之間的共享,也包括組織單元內部的共享。這類似于生態系統的和諧原理:“群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鑒于目前較多的文獻均從宏觀視角對共享發展理念及實現路徑進行闡述,本文擬以經濟發展的基本單元——企業為分析對象,結合組織生態學相關概念,梳理企業管理實踐中與共享發展問題相關的幾點內容,以饗讀者。

共享夙愿是人類特有的生命追求
近期網上有一個名為青山周平的日本建筑設計師很火,他在北京的四合院生活了7年,不久前因為幫助胡同里的百姓成功改造居住空間而名聲大振。在“一席”講壇上,他以《我們為什么要花那么多錢去買兩屋一廳?》為題發表了一個精彩的演講,很有啟發。他從建筑師的角度觀察胡同里百姓的日常生活,并理解諸如為什么成年男子夏天在胡同里光著膀子而不覺為難:“因為他們覺得這個地方不是公共的空間,他們覺得這是家的一部分,他們家的客廳,或者他們家的哪里哪里——為什么在自己的家里面要穿衣服。”人們在胡同里下棋、打牌、聊天,這里被視為他們的客廳。許多諸如桌子、凳子、晾衣架之類的物品放在院子里,成為實質上的公共用品,鄰里共享,但物品的主人并不放棄所有權,物品的“所有”和“使用”之間有很曖昧的關系。家里不需要冰箱,因為周圍的菜市場、小賣部既方便又新鮮……他說:“所以我認為家應該是開放的,家應該跟城市融合在一起。城市可以引入到家里面,家可以延伸到城市里面。家應該是跟自然有關,跟生活有關。”
這是一個日本人眼中的北京四合院。無疑,青山周平是喜歡它的,喜歡它什么呢?自然是它的生態、和諧、共生、共享。青山周平自稱,他所有有關未來家的設計理念——“共享社區”,靈感純粹來源于北京的四合院。
不分種族、膚色,無論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只要有可能,都對北京四合院情有獨鐘。這可視為人類共持的偏好嗎?如果回答:是,則可以說:四合院作為完美體現了天人合一思想理念的居住設計,滿足的是根植于所有人類生命深處的共享夙愿。因此,“共享”是生物世界、人類社會的天然存在和本質需求。
“學習型組織”為共享發展提供了適配生境
19世紀30代以前,英國一些村莊周圍生活著山雀和紅知更鳥,牛奶公司送到各家各戶門口的瓶裝牛奶是沒封口的,紅知更鳥和山雀便在顧客開門收取牛奶前,搶先一步從瓶口吸取乳汁,長此以往,它們的腸胃系統慢慢適應了牛乳。再后來,隨著工業化進程的發展及環境的惡化,牛奶公司開始使用鋁箔封住了奶瓶口,山雀與知更鳥便不再擁有這份“免費早餐”了。
令人驚奇的是,山雀慢慢學會了用尖尖的喙刺穿鋁制瓶蓋,重開“免費早餐”的大門。知更鳥卻只有極少數學會了用喙刺穿瓶蓋的本領。
同樣是鳥類,以前同樣都會喝“免費牛奶”,而在牛奶公司加裝瓶蓋之后,為什么絕大多數紅山雀會刺穿鋁制瓶蓋,而僅僅只有極少數知更鳥學會用喙刺穿瓶蓋的本領呢?
一些鳥類專家通過對這兩種鳥類的習性進行了觀察之后解釋說:“山雀是一種群居的鳥類,在一只山雀發現用尖尖的喙可以刺穿瓶蓋后,所有的紅山雀都學會了用喙刺穿瓶蓋;而紅知更鳥是排他性較強的鳥類,喜歡獨來獨往,如果其他鳥來到它的地盤上的話,它還會大叫著把對方趕走,同類之間也基本上是以敵對的方式溝通。當一只知更鳥發現用喙刺穿瓶蓋的本領時,難以把這一發現與別的同類共享,天長日久,由于食物來源匱乏,紅知更鳥的數量日漸稀少。”
山雀與知更鳥的故事,講的是共享或獨行對生物生存的影響。美國著名管理學者彼得·圣吉曾通過此案例引申出“學習型組織”這一重要概念,用以說明企業內部、企業與企業之間學習交流的重要性。
網絡經濟、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取代資本、勞動、土地等成為主要的生產要素,這使共享而非獨占的正外部性尤為明顯,因為,知識生產要素相對于傳統生產要素而言,最大特點是共享程度越高,越能更多地展現網絡效應,這是由知識生產要素邊際收益遞增的特點所決定的。因此,共享發展理念與現有的企業生態環境存在相當程度的適宜性、匹配性,也可概括為:知識經濟的時代背景為共享發展提供了適宜生境。
共享發展首先應體現于“生物人”而非“社會人”
社會意義上的共享發展通常指的是以類型劃分的人群,即結構化了人(社會人),如城鄉之間、沿海與內陸之間、發達地區與貧困地區之間如何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等等。相對于“社會人”,共享發展對個體的“生物人”意味著什么?都說發展最終是為人服務的,那么這個“人”是指“生物人”還是“社會人”?中國傳統文化的“以人為本”是典型的“社會人本”而非“生物人本”。因此,提及共享發展,遵循以人為本的真義,首先應該落實“生物人”的共享發展問題,即人自身的共享發展。而所謂人自身的共享發展是指人兼具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需要實現肉體與靈魂的內在統一。人作為文化動物,在物質供給豐沛的同時,仍不能短缺精神追求及心靈寄托。因此,人自身的共享發展是指個體的全面發展、平衡發展、身心發展、靈肉發展。沒有這一點,共享發展理念無從談起。
從組織生態變遷的角度看,工業文明以來的企業管理發展史及企業管理思想發展史,也是對組織成員(被管理者)屬性認知進化的發展史。19世紀末20世紀初,工業技術快速發展、專業化分工日益深入、廣泛,促使企業規模迅速擴大化,企業管理日趨復雜,管理復雜度提升與管理理論及管理技術匱乏的矛盾凸顯,以美國為代表的現代管理學在此背景下進入初創時期。
科學管理之父泰羅(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立足于解決管理現場的時間浪費及效率提升問題,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通過時間研究、動作研究、標準化、職能制等建立起了一整套相較于經驗管理至為嚴謹、科學、程序、規范的管理方法,并通過可培訓、可復制的方式迅速在生產現場推廣開來。于是,組織中的普通人(工人),只要按照程序,接受命令,完成規定的程序化動作即可。自此,與機械緊密結合起來的工人開始了由“自然人”向逐步遠離原始生態的“經濟人”的轉變。有意思的是,這一轉變當時以“進步”的姿態向世人宣告科學管理時代的到來:物質生產力得到極大提高、財富快速積累,人的需要、情感、選擇、自由等價值被置于資本邏輯的演繹之中。在這一組織生態下,個人與組織的關系,是“機械人”與機械組織的關系。擁有理性或說能夠把知、情、意融為于一體的人無從體現。其后,人際關系學派的代表梅奧(George Elton Mayo,1880—1949)從科學的工業心理視角重新審視、闡釋了人是“社會人”的觀點,否定了“經濟人”假設的基本認知。20世紀50年代,赫伯特·西蒙(Herbert A.Simon,1916—2001)提出決策理論,“決策人”一詞的出現,意味著人不僅是有情感、自尊、社會歸屬感等單向要求的“社會人”,更是有自我決策、自我主張、不受外力左右、能夠獨立思考并行動的“決策人”。20世紀80年代,企業文化理論誕生,標志著管理學對人(被管理者)理解與認知的日益豐富、完善、提升,有人據此提出了“文化人”假設。
西方近百年的企業管理發展史,經歷了對組織內部“人”的發展的數次研究,相關的理論分別從身心視角、多元化利益視角等誘發人的全面發展和積極生存狀態。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借用技術支撐和利益誘發等手段曾取得了一系列效果,但相應的,其局限性也漸趨清晰,近年來,結合組織文化、組織生態、組織正義等命題學界及實踐部門正在探尋新的誘發。
目前,中國的組織發展,特別是在對人的激勵層面,整體上仍處于以技術支撐和利益誘發為主要工具和手段的時期,“富士康事件”等現象就是這一組織生態的具體反映。當組織生態無形中引導了人向物質、金錢、名譽、地位、自我等單向度發展時,必是忽略了人的本質需求:精神、心靈、道德情操。馬克斯·舍勒(Max Scheler,1874—1928)把這種有用價值凌駕于生命價值、工具價值之上并取代內在價值的狀況稱為“價值的顛倒”。因此,目前迫切需要在現有組織生態場域呼喚人的價值回歸,也就是微觀層面的人的共享發展:全面發展、和諧發展。
共享發展理念與企業有效性評價
20世紀90年代,較有影響力的利益相關者理論在管理學領域誕生并迅速得到理論與實際部門的認可。到目前為止,一般的觀點認為:發軔于20世紀60年代的這一理論,產生的最主要原因是對美、英等國奉行“股東至上”公司治理實踐的質疑。即“股東至上”的治理模式強調股東利益最大化,犧牲公司雇員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加之20世紀80年代,美英等國敵意收購事件頻發,通過收縮規模,裁減員工降低成本,在股價上揚中損害企業經理、一般員工、供應商、社區等各方利益而單獨維護股東利益。20世紀90年代以后,西方學者認為:公司治理的作用不僅包括調節股東與經理層的關系、大股東與中小股東的關系,還應該包括調節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關系,如債權人利益的保護,社區利益的保護等。公司治理的主旨應是在保護各利益相關者利益的前提下,實現公司價值最大化。
深入分析組織生態環境的變遷會發現,對“股東至上”公司治理實踐的質疑只是利益相關者理論形成的誘因之一,而非全部,真實的原因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整個企業生態環境變遷導致外部力量取代股東成為影響企業成敗的關鍵。即技術創新迫使企業與外部的聯系日益廣泛、復雜、深刻,從供應鏈合作戰略聯盟,從業務外包到業務歸核,從一體化到模塊化,企業日益成為整個生態系統中的業務單元,企業的生存、發展越來越受制并依賴于外部環境而非企業自身,環境對企業成敗的影響日益增強。企業與外部合作者的關系由線狀向網狀發展,繼而,影響企業的外部力量呈多元、分散、力量均等特點。而且,這些多元的影響力量構成系統,互相作用。單一或少數的利益相關者獨統、獨占、獨享企業管理權或利益的局面逐步讓位于諸利益相關者共同體。企業與外部的聯系成為常態,交往的頻次由單而復,單次博弈式的一錘子買賣被多次博弈的誠信機制所不容,企業必須向共享、互利、互惠的境界成長與邁進,否則,將不被生態環境所接納。相較于反映了共享理念,體現了共享精神,達到了共享目標的企業利益相關者評價方法,傳統企業有效性評價方法(系統資源法、內部過程法、目標法)的局限性日益明顯:“股東利益至上”、注重縱向權力評價,顯然不是一種兼顧生態各方利益的共享機制,有悖于組織生態環境的變化,因此必然受到環境的嚴峻挑戰。
反觀國內的管理現實,目標評價法仍然是目前組織有效性評價的主要思路,如GDP導向、市場占有率導向、利益導向、稅收導向等。這種評價及其由此帶來的方向驅動,構成了企業短期行為、透支未來行為、重數量輕質量等行為的生態背景,是一系列問題產生、形成的誘因。如果說共享發展在個體層面要求的是全面、和諧發展的話,在企業層面則必須要求長遠發展而非短期發展、質量發展而非數量發展、可持續發展而非透支式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共享發展確是企業必須努力踐行的一項重要管理活動。
(作者單位:中國科學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責任編輯:羅志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