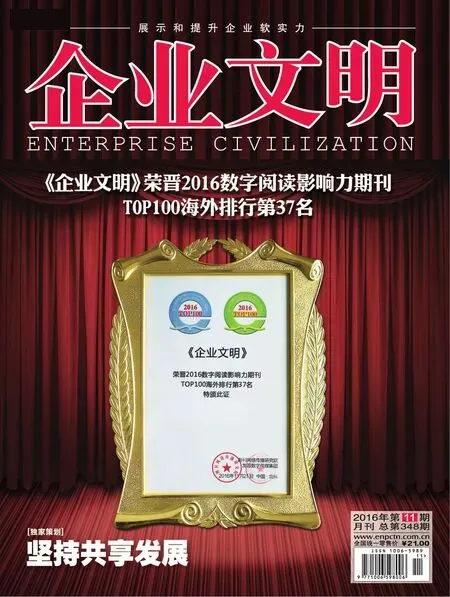建筑藝術與工匠精神
文/付晉德
建筑藝術與工匠精神
文/付晉德
建筑,是一個時代人類創造力與價值觀的直觀體現,是實用與審美的價值統一、技術與藝術的相契相融、信仰與自然的和諧共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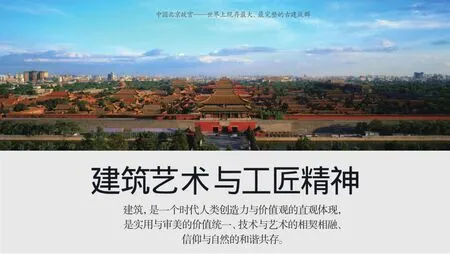
中國北京故宮——世界上現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
一個時代,不能沒有建筑藝術的“大師”和“大家”,同樣也不能沒有精勤于業的“能工”“巧匠”,一件件傳之于世的建筑精品,無不閃耀著建筑藝術與工匠精神的光芒。
建筑藝術與工匠精神來源于信仰的力量
從埃及的金字塔,到中國的天壇、希臘的神廟、印度的阿旃陀石窟,東西方文明對神靈的崇拜、對宗教的敬畏都深深影響了建筑藝術,建筑成為彰顯這種信仰力量的載體。以古埃及的金字塔為例,古代埃及人對神的虔誠信仰,使其很早就形成了一個根深蒂固的“來世觀念”,他們甚至認為“人生只不過是一個短暫的居留,而死后才是永久的享受”。在《金字塔銘文》中有這樣的一句話:“天空把自己的光芒伸向你,以便你可以去到天上,猶如拉的眼睛一樣。”“拉”是古埃及的太陽神,是古埃及神話中最重要的神,角錐體形式的金字塔表示對太陽神的崇拜,也是為法老死后搭建上天的天梯。建筑是藝術與技術融合的共同體,無論多么令人慨嘆的藝術構思,最終也離不開鍥而不舍的“工匠精神”。建于公元前2670年的胡夫金字塔,原高146.59米,因頂端剝落,現高136.5米,邊長約230多米,占地面積5.29萬平方米,塔身由分別重達1.5噸至160噸的230萬塊巨石組成,以51度的傾角向上修筑而成,其底部四邊幾乎是正北、正南、正東和正西,誤差小于1度。這種建筑的奇跡誕生于距今四千多年前,很難想象在一個還是“刀耕火種”的年代,在命如螻蟻的數十萬奴隸肩抬背扛中,歷經數千年的風吹雨打,它仍然如同豐碑一樣矗立在我們的眼前。這是一座文明的豐碑,建筑藝術與工匠技藝的完美融合,穿越塵封已久的歷史,訴說著曾經的信仰與尊嚴。它也是一座野蠻的豐碑,熄滅了多少生命的燈火才點亮這部幾千年的傳奇,在時光的流轉中回響著多少工匠沉默的吶喊,“工匠精神”與信仰同樣不朽!
建筑藝術與工匠精神根植于文化的傳承
法國作家雨果在著名的《巴黎圣母院》中說過:“人類沒有任何一種重要的思想不被建筑藝術寫在石頭上。”建筑藝術是文化最鮮明、最深刻、最長久、最直觀的體現。北宋張載的一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直言不諱地道出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核心價值觀。從歷朝歷代“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皇家建筑,到官商世家“深邃富麗、層樓疊榭”的深宅大院,再到“古樸質雅、青磚灰瓦”的普通民居,都彰顯著傳統文化的內涵,與自然環境默契相合,于咫尺之內再造乾坤,這既是對自然美學理想的追求,更是對“天人合一”哲學的實踐。建筑藝術是通過建筑的多種外在形態和形式綜合顯現出來的,獨具匠心的格局來自于“工匠精神”的精雕細刻,這種“工匠精神”來自于文化的傳承。從我國目前所見年代最早的手工業技術文獻《考工記》來看,早在先秦時期手工業的專業細密化、技術規范化、工藝科學化程度就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考工記》不僅提出了當時建筑業中慣用的長度單位:幾、筵、尋、步、軌,而且也在字里行間對“工匠精神”進行了闡述,“知得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特別是“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為良”的論斷,飽含著早期辯證唯物主義的萌芽,是對“工匠精神”的深刻思考。建筑藝術與工匠精神都根植于傳統文化的深厚土壤,一脈相承,厚積薄發,在文化的傳承中沉淀與結晶,拂去塵埃都能找到其來時的路徑。

意大利米蘭大教堂——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建筑
建筑藝術與工匠精神詮釋著價值的尺度
古羅馬建筑師維特魯威在《建筑十書》一書中提出了建筑三要素:適用、堅固、美觀。這部世界上流傳至今的第一部完整的建筑學著作清晰地提出了建筑的價值尺度。建筑是實用價值、審美價值的完美結合,一個稱得上建筑藝術精品的建筑物,其實用價值是第一位的,要能夠滿足人們對社會生產生活的需要;同時建筑通過其空間延續性和環境特定性、正面抽象性與象征表現性的結合,在幾何形的線、面、體組成和空間、色彩、質感、體形、尺度、比例等渲染中,將科學與美學、技術與藝術、物質生產與藝術創造融為一體。建筑是“凝固的音符、空間的藝術”,也是一份“鮮活的記憶、無聲的傳遞”,一件件傳世的建筑精品都是一本本“不會說話的工藝教材”。建于公元1056年的應縣木塔,是中國現存最高最古的一座木構塔式建筑,全塔整體架構所用全為木材,沒用一根鐵釘,全塔共應用54種斗拱,卯榫結合、剛柔相濟,結構科學合理,這種剛柔結合的特點有著巨大的耗能減震作用,甚至超過現代建筑學的科技水平,被稱為“中國古建筑斗拱博物館”。但是,這座與意大利比薩斜塔、巴黎埃菲爾鐵塔齊名的“世界奇塔”,修建者與眾多工匠的名字均無處查考,只留下了這份讓無數后人敬仰的匠心與技藝,在寂靜的佇立中彰顯著工匠精神的價值尺度。
建筑藝術與工匠精神體現著責任的堅守
“建筑是石頭的史書”,必須經得起時間的淘漉才能洋溢出建筑藝術和工匠精神之美。一座座“曇花一現”的短命建筑,一個個“橋塌塌”“樓垮垮”“路脆脆”的“豆腐渣”工程,與“建筑藝術”與“工匠精神”背道而馳,更多地應該探究的是“行業良知”和“職業道德”。質量是建筑的生命,沒有質量的建筑就是沒有生命的藝術。當每一個雨季“下水道都在拷問著城市良心”的時候,我們都不應該忘記建于公元595年的趙州橋,這座當今世界上現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單孔敞肩石拱橋,在漫長的歲月中歷經無數次洪水沖擊、風吹雨打、冰雪侵蝕和地震戰亂的考驗而安然無恙。這1 400多年的巍然挺立,挺立的是建造者的良心,挺立的是一部“石頭的史書”。工匠精神來自責任的堅守,這種堅守僅僅有良知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得有嚴密的制度。公元前620年前后編成的重要典籍《禮記》中記載:“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物勒工名”這種早在春秋時期就開始出現的制度,以實名制的方式推行了質量責任管理,300多年后的秦國將“物勒工名”制度廣泛運用于生產活動中,此后的歷朝歷代都沿用不輟。在明代幾乎發展到了極致,以明南京城墻的城磚為例,每一塊磚均銘記了出產該磚的府、州、縣、總甲、甲首、小甲、制磚人夫、窯匠等各級責任人的名字,經歷層層的嚴格驗收,即使能蒙混過關,但砌入墻體若干年后發生質量問題,仍要受到嚴格處罰。這種苛酷的制度,一定意義上是“工匠精神”的強制性播種。
建筑藝術與工匠精神折射著社會的溫度
建筑藝術是社會主流思想的體現,“窺一斑而知全豹”,在冰冷的木石磚瓦中能感受到當時社會的溫度。從中西方傳統建筑風格的對比來看,中國文化注重道德和藝術,體現著儒家文化和人倫秩序,講究“五行八卦”和“中正仁和”,文化的包容性使每一種外來文化最終被同化和吸收,只是在局部融匯了本民族的特色,建筑風格基本趨于統一。西方文化重視科學與宗教,具有強烈的時代特征與地域性民族特色,每一個發展階段的特征差別非常顯著,沒有一種風格能夠具有絕對的統治地位,顯示出對自然的征服和神權的敬畏。這種建筑風格上的差別,反映了物質和自然環境的差別,同時也反映了主流價值觀念與社會結構形態的差別。社會主流思想的差別直接導致了在對待工匠態度上的天壤之別。西方的工匠有著比較高的社會地位,他們擁有自己獨立、自由的權利,敢于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和看法,敢于在實踐和理論的探索中去思考,敢于在爭執中堅持自己的專業水準和職業尊嚴。但是,中國的工匠可沒有西方工匠幸運,漫長的封建社會史就是工匠群體的血淚苦難史,不僅要成年累月地從事繁重勞動,在皮鞭、枷鎖下貢獻著自己的聰慧卓識,還要編入“匠籍”、身份世襲、不得脫籍改業,被迫買斷自己與子孫后代的人生命運。從冰冷刺骨的社會溫度,到燦如星辰的建筑瑰寶,中國的“工匠精神”在苦痛中生、在苦難中長,在苦厄中手手相傳、生生不息,也正是如此,“工匠精神”始終帶著那么一股苦澀的味道,在食苦如飴的堅韌、苦盡甘來的期盼中歷久彌新。
建筑藝術與工匠精神綻放著時代的光芒
俄國作家果戈里說過:“建筑是歷史的年鑒。”建筑藝術記錄著時代的發展變遷,現代社會的思想解放和生產發展,特別是新材料、新技術、新工藝的廣泛運用和生態、節能、環保、智能等設計理念的深入人心,建筑風格呈現出多樣化、個性化、抽象化的發展趨勢,一個個新穎獨特、獨樹一幟甚至夸張寫意的建筑造型,都顯現出這個時代所擁有的思想自由、經濟繁榮、民生獨立、文明發展的耀眼光芒。但是,建筑藝術也進入了令人迷茫的階段,風格趨同的建筑、“千城一面”的城市,一定意義上成為“時代的傷疤”,這些丟失的不僅僅是建筑的精神與文化,更是城市的情懷與記憶,也正是如此,建筑用無聲的語言真實地記錄了這個腳步匆匆的時代。同樣的迷茫,也來自“惟精惟一”的工匠精神遭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窘境,“工匠精神”缺失的身后是“工匠人才”的缺口,是“工匠戰略”的缺位。推動和實施“大國工匠戰略”,最核心的在于解決“工匠式”精致生產力的供給,最關鍵的在于國家的推動、社會的認同和全民的參與,最優先的是喚醒全社會創新創業的潛能,最困難的是解決工業化、城鎮化所帶來的農民工的身份轉換和權益維護,最根本的是支撐整個經濟和社會的轉型升級。只有通過大格局統籌、一攬子推進、全縱深發力、兜底式保障,危微岌岌的“工匠精神”才能在“工匠戰略”落地中生根,才能經得起歲月流轉的歷練,才能煥發出時代氣質的光芒,才能照耀文明前行的足跡。
(責任編輯:李萬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