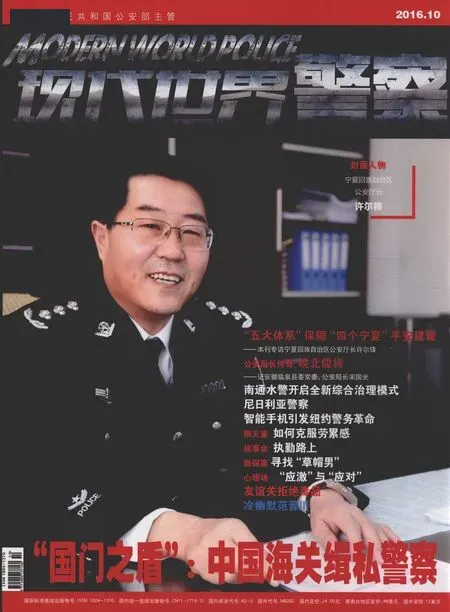“程序正義”能否解決所有問題
文/房廈 王欣
“程序正義”能否解決所有問題
文/房廈 王欣

警察執法公信力總會受到各種事件的挑戰
著名學者赫爾曼·戈爾茨坦曾經指出,就其本質而言,警察是自由社會的“異端”。所有的社會都需要在自由和秩序之間取得平衡,盡管在不同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背景之下,這個平衡各不相同。警察作為國家法律系統的前沿、法律直接執行者和秩序的首要維護者,不可避免地每天都要在大量的執法活動中與民眾互動,這其中既有互幫互助的良性互動,也必然有因執法而起的沖突。在所有國家,在執法過程中發生沖突都不可避免,甚至某些個案也會使得警民之間的信任遭到嚴重破壞,這也是學者們經常關注的話題。
2015年,美國因弗格森等案件引發了大量的關于警民關系的討論。對此,總統奧巴馬成立了21世紀警務特別工作小組,提出21世紀警務專題報告,其中就提出了通過加強程序正義、執法透明度和問責、正視過去與現在的困難來加強警民互信。美國學者湯姆·泰勒曾經基于大量的實證研究提出了執法程序正義理論:如果警察在執法過程中以公正和尊重(respect)的態度與民眾交流互動,他們就可以贏得公信力(legitimacy)。蘭德公司也撰文提出在這個信息透明的時代,警察的執法時刻都在公眾的審視之下,警民之間的信任面臨著更多的挑戰,而公信力與尊重是一條雙向道,警察給予民眾尊重,民眾給予警察公信力,如此才能加強警民之間的互信。2015年,澳大利亞格里菲斯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和澳大利亞警方也發起了一系列的道路盤查執法實驗(昆士蘭社區實驗),驗證泰勒的“程序正義”理論。隨后,蘇格蘭學者在蘇格蘭復制了這一實驗。然而,蘇格蘭警方和學者的“程序正義”與警察執法公信力的實驗卻顯示,“程序正義”干預措施并未提高民眾對警察的信任度和滿意度。相比對照組,實行“程序正義”組的滿意度不升反降,對泰勒的“程序正義”理論提出了挑戰。
泰勒的“程序正義”原則是否真的有效?警察以尊重和公正的態度對待民眾,其執法就會得到民眾的支持與理解、其執法過程就具備權威性嗎?
本文介紹的是英國著名警務專家P.A.J沃丁頓等進行的警民信任與“程序正義”的研究,以耶魯大學法學及心理學教授湯姆·泰勒的“程序正義”(procedural justice)執法理念為基礎,用研究實例指出了“程序正義”理念的片面性。“程序正義”理念認為執法過程中執法主體表現出充分的公正性及尊重,就會贏得公眾對執法者的信任進而提升執法公信力。研究表明,警方與公眾的互動過程不僅涉及警察的行為方式是否公正,更受到公眾如何認知并詮釋警察行為的影響。

對警察的負面印象一旦形成,就難以動搖
研究人員在英國黑鄉地區選擇了34組有著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公眾組成討論組。參與者觀看同一部攝像頭真實記錄的警察與一位盜車嫌疑人的交涉過程(該視頻曾在BBC一個系列節目中播出),并在觀看后進行小組討論。研究發現,參與者對視頻中警察與嫌疑人交涉的幾個關鍵階段的評價有著嚴重的分歧以及截然不同的理解。這說明執法者的行為與公眾認知之間的復雜關系,也為警察在贏得公眾信任方面提出了一個實際問題——取得公信力沒有任何簡單的訣竅。
研究指出,對于執法人員而言,理解并領會公眾對相同執法行為的不同評價非常必要,單一的或完全一致的公眾滿意度標準是不存在的。即使警察的行為符合“程序正義”,公眾的評價仍然受固有的對警察看法的影響。這些固有看法可能來自過去直接與警察接觸的經驗,或者通過間接聽說而形成的印象。
泰勒在2011年的學術文章中提出了“基于動機的信任”,認為如果公眾在與執法者互動過程中得到了公正的對待和應有的尊重,他們就會傾向于認為執法者值得信賴,他們的執法動機是為了大眾利益而非出于私利。這樣的認知一經形成,便會提高執法者的權威性,即便在未來交往中警方的行為出現紕漏,對執法者建立了信任的公眾仍很難對其產生負面看法。
研究發現,與警方交涉中產生的負面印象要比正面經歷的影響嚴重得多,甚至嚴重影響接下來的公眾與警方間的互動。負面印象一旦形成,人們對警察持有的懷疑態度強烈到難以動搖,即便警察嚴格按照“程序正義”理論執行公務,也難以讓公眾的態度有所轉變。
經過精心篩選,研究者從292個BBC紀錄片的真實案例中挑出五個案件視頻播放給34組參與者,并對他們的反應與討論進行詳細記錄,對其中存在分歧最大的一個案件進行了深入探討。
案件概述:兩名男性高速公路巡警在黑鄉地區高速公路上巡視時,被指揮中心告知一輛在當地加油站加油后沒付款的汽車正朝著他們所在的方向駛去。警方對涉事車輛追堵過程中又得到消息,該車的號牌是假的,官方數據無法檢索到。這個信息促使兩名巡警懷疑涉事車輛可能是被偷盜的。接著,警方逼停了涉事車輛,副駕駛位置的巡警跳下車,跑向涉事車輛。當鏡頭再次錄到這名警察時,他正與年輕的男司機扭打在一起,并對這個年輕人說:“下車!要不然我把你拖出來。”兩人繼續扭打了一會兒,年輕司機舉手投降并跟著警察走向警車后座,警察向年輕人解釋了他被捕的原因。接著,警方得到進一步消息,發現這個年輕人并不是偷車人,而是這輛車的合法車主,但是這輛車仍存在車牌號與注冊號碼不符的問題。警方繼續追問,車主一開始說是賣車的人搞錯了車牌號,后來承認是一周前另一名巡警給他發了“車輛缺陷整改通知”。這時,駕車的警察有些惱怒地問這位年輕人為什么帶著假牌照開車,年輕人辯解說通知讓他14天之內整改,不用馬上去。警察繼續提醒他,任何好公民都會在第一時間去整改,而不是繼續帶著非法車牌駕駛。年輕人開始在與警察對話中使用臟話,并露出輕蔑的態度。警方最終開出了80英鎊罰單。其間,雙方的交流越來越多地夾雜著憤怒情緒。總的來說,這個案件是個很典型的“輕視警察”的案件,一個叛逆的、善于辯解的中產階級富裕年輕人不斷地挑戰警察的權威,最后遭到警察開出的高價罰單。
參與者的討論在三個方面存在最嚴重的分歧。
一是關于警察根據推測執行公務。警察經常需要在僅僅知道有限信息的情況下行動。參與者一致認為警察推斷車輛有可能是被偷的想法是合理的,但是分歧在于當這個年輕司機還沒有被認定為偷竊的情況下,警方是否應對其動用武力或身體接觸的方式。一些參與者認為警察應首先在車外向車主解釋清楚逼停他的原因,然后再讓他去警車那邊接受詢問。
二是關于是否應接受車主關于“車輛缺陷整改通知”有14天期限的解釋。車主說他只被告知有14天期限,但并沒有告訴他在此期間不能再次駕駛這輛車。參與者在是否應該相信車主方面有很大分歧。
三是更廣泛層面上的責任歸屬問題。車主在知道車牌信息錯誤的情況下駕駛車輛的行為是否應該承擔責任?警察像對待偷車嫌疑人那樣對待他是否有誤,是否應該實施罰款(因為車主之前已經被開過罰單了)?
值得注意的是,參與者發表的觀點不僅僅出于他們看到了什么,很大程度上還依賴他們的想象,比如對視頻中沒記錄的一些情節的猜想。另外,參與者對視頻中兩名執法警察的看法很大程度上由參與者本身站在誰的立場說話而決定,站在警察的立場和站在車主的立場,所形成的看法完全不一致。

警察獲得公信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公眾對警察的評價不僅僅根據所看到的,還會通過聯想過去可能發生的相關事件、現在及未來的更多可能性來得出結論。盡管泰勒的“基于動機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研究者也確實觀察到,之前對警察已經形成良好印象的參與者更傾向于正面解釋警察的行為,而一旦沒有形成一定的信任,公眾更傾向于往壞處推測警察的動機。部分參與者表示,穿制服的人都會有一種優越感,居高臨下地對待公眾。無論警察行為正確與否,這種刻板印象都很難改變。研究者認為,對警察持有高度期待的人面對現實常常會失望,進而形成對警察的不信任。這為警察執法公信力的改善提出了很現實的問題。
有的參與者一開始認為警察強迫司機趕快下車是合理的,因為依據警察的合理推斷,車輛有可能是被偷的、涉事司機有可能持槍,因此出于安全的考慮,警察的行為可以理解,是必要的權宜之計。但這樣的觀點往往在發現車主不是盜車賊的時候發生改變,認為警察不應該那么強制執法,應該更尊重車主。這些很現實的問題在對警察隊伍的培訓中很少提及,常常被忽視。研究者建議,要保證警察得到足夠的專業化訓練,很重要的一點是要保證他們既能面對工作環境中的不確定性,又能應對他們工作中不可避免的爭議。
通過對簡單個案的剖析我們看到,警察獲得執法公信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是復雜的,警察在執法過程中與民眾的互動千姿百態,單純的“程序正義”原則并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但是我們仍然不能忽視“程序正義”所帶來的長久效應。那些執意對警察行為給予負面評價者,多數有過與警察互動的不良體驗,或者從影視作品、媒體報道中形成了對警察的負面印象,長期堅持“程序正義”則有可能改變這一情況。
警察不可能讓所有人滿意。作為秩序的守護者,當一些人為了自身的方便與“自由”而侵犯公共秩序之時,警察必然會與之發生沖突。在第三方看來,這種沖突中警察是完全正當的,而在當事人看來則不同。某些當事人就會從中形成對警察的負面體驗,尤其是當警察的武力升級或者懲罰升級時,如本文中最后警察開出80英鎊的罰單。
民眾的判斷還常常從結果出發,而并非從程序出發。本文中,當參與者不知道車輛是否為偷盜而來之時,普遍認為警察逼迫司機下車的行為是合理的;而當參與者得知車輛并非偷來的,一部分人的觀點則發生了改變,認為警方執法過于粗暴。這種判斷是非的方法是非理性的,對警察也是不公正的。在執法的動態過程中、信息不完全的情況下,警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做出正確判斷。
如何加強警民互信是一個深遠的話題,也是一項復雜的工程。本文所說的“程序正義”,在我國更多的是以執法規范化這個內涵更廣泛的術語所表達。與執法規范化強調法律程序不同的是,“程序正義”更多強調的是警察與民眾互動時的態度、情緒,執法過程是一個“人”與“人”互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往往情緒會壓倒理性。我們在培訓警察執法時,尤其應當重視警察的情緒管理和控制。無論在哪一個國家,警察執法公信力都會受到各種事件的挑戰,媒體尤其能夠在短時間內無限放大某個不良個案對警察整體公信力的影響。如果不能很好地處置,這種不良影響將造成更多的執法沖突和抵抗。尤其在自媒體時代,斷章取義的視頻、一面之詞的敘述往往在警察尚未來得及反應之時就已經占據了網絡媒體,而警察滯后的反應往往不足以改變已經受損的公信力。正如本文介紹的這場英國執法沖突,當事件過程已經非常明了之時,一些民眾仍然不愿意改變已有的看法,其觀點深深地受到已經形成的刻板印象的影響。因此,警察形象的長期經營對每一起案件中警察的執法公信力都會產生影響,執法公信力與警察形象的長期經營與維護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