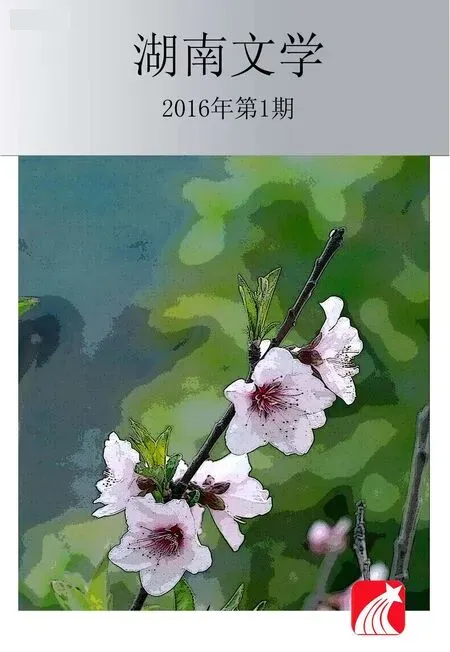風雅人物
→聶鑫森
?
風雅人物
→聶鑫森
畫韻琴音
三十五歲的何地與迫近而立之年的于今,因遲遲未婚,在湘楚大學成了令人矚目的大男剩女。
湘楚大學是一所綜合性的大學,文、理、藝、體諸系齊備。何地在美術系任教,課堂上教的是素描、速寫、水彩、油畫,業余則主攻油畫肖像。于今供職于音樂系執教古琴演奏,因父親是個有名的古琴家,自小對她耳提面命,因此她的琴藝亦很出色。他們因專業有別,又不在一個系,加之曲高和寡不喜交結朋友,所以他們雖認識,也不過是偶爾碰見點點頭而已。
何地曾留洋法國研習西畫,回國后先在一所中學教圖畫課,因創作的肖像油畫選入巴黎沙龍美展并獲金獎,被湘楚大學的校長嚴冰看中,熱情地把他聘了過來。何地個子魁梧,濃眉、亮眼、隆準高峻,說話不多,但一開口便語驚四座。他的父親是洋行的買辦,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西裝革履,很洋氣。但何地力避這種張揚的風度,上課喜著長衫或中山裝,作畫時穿的是藍布長褂,上面沾滿斑斑點點的油彩,即便上街去辦什么事,也同樣不修邊幅,大大方方,毫無怯色。
有一個星期天的上午,何地畫完一張油畫小品,想起該理發了,也不換下臟臟的工作長褂,走出畫室去了校門外的一家很漂亮的小理發館。這個小理發館的老板兼作理發師,還有一個小徒弟負責燒水等雜務。店主見何地這副模樣,傲慢地說:“先生知道理發的價格么?”何地點點頭。這個頭理得相當粗率,推、剪、刮、洗,不到二十分鐘就完成了。
“先生,請付款!”理發師口氣急促,手伸得長長的,生怕何地賴賬一走了之。
何地知道理一次發,是二角小洋,若顧客覺得服務周到,可以連同小費付一元大洋。他從口袋里掏出一塊大洋丟到店主的手上,板著臉,一聲不吭地走了。
一個星期后,何地穿上嶄新的西裝、襯衣、皮鞋,器宇軒昂地再次走進小理發館。店主馬上認出了他,立刻滿臉諂笑,點頭哈腰,先沖好一杯咖啡送上,待何地喝了幾口后,再細心地為他理發,每個細節都無可挑剔。
出門時,何地掏出兩角小洋丟在桌上。店主十分驚詫,說:“這……這……”何地說:“朋友,你不應嫌少!兩角小洋應是上次的報酬,而上次付的一元則是這次的報酬!我告訴你,以衣貌論人是要不得的!”
于今呢,沒留過洋,本科讀的也不是音樂專業,而是中文系。但她彈古琴頗受稱贊,而且對歷代流傳的琴譜鉆研很深,可以依琴“打譜”后,再用新式樂譜標示出來。校長嚴冰效仿北京大學的蔡元培,破格聘她前來任教。
于今既有古典美人的模樣,又有不讓須眉的才情。小蠻腰,瓜子臉,秀眉細目,十指纖長。古典詩詞出口成誦,而且時有作品見于報刊雜志,如《雨湖聞老者彈琴》:“秋老斜陽指上哀,撫琴猶見舊亭臺。而今兩鬢清霜染,可憶雙雙蝶影來?”出語雋雅,又聯想豐富,有人生之慨嘆。
也許是過于自憐,于今有常人難以理解的潔癖。她決不彈別人的古琴,說那上面有塵俗之氣;她只彈父親贈給她的那架宋琴,別人當然不能染指。有校工或同事來她的宿舍,傳達校方或系里的某個通知,待人走后,她要用棉布蘸上酒精,把門把手擦拭一遍,再用濕拖把拖地。她最忌諱男人嘴里飄出的酒氣、煙氣,因此,除開會、上課之外,有男性的場合她遠遠避開。
嚴冰與于今的父親是多年的朋友,對于今的婚事也就格外留心。有一次,他找于今談話,問:“小于,這世界上的青年男子,你就沒有一個看得上眼?”
于今臉紅了,說:“當然有,只是我沒碰到,所以我在等待。”
“林黛玉說:‘質本潔來還潔去。’你要學她嗎?我若看中了一個,你不會不見吧?”
“嚴校長,我相信你的眼光不俗。”
“那就好。有什么條件,只管說。”
“說不好,見了才知道。”
“這就是條件!你一見就心動的人,我相信有!古人說:十步之內,必有芳草。”
一九四一年深秋,校園里芙蓉花放、金桂飄香。嚴冰忽然通知何地和于今,到他的辦公室去,有要事相商。
身著青灰色中山裝的何地,與穿著一襲素白隱花長袖旗袍的于今,在上午九點鐘,幾乎同時出現在校長辦公室的門口。何地對于今點頭一笑,然后輕輕敲門,里面便傳出“請進”的聲音。
何地擰動把手,輕輕推開門,再讓到一旁,很紳士地說:“于老師,您先請!”
在這一刻,于今雙頰泛紅,輕輕說道:“謝謝。”然后款款而入。
嚴冰站起來,說:“二位大駕光臨,請坐!喝茶還是喝咖啡?”
何地望望于今,請她一示。
于今說:“喝茶吧。”
嚴冰又問:“綠茶還是紅茶?”
于今說:“綠茶吧,我喜歡君山毛尖。”
何地說:“我也是。宋詩中有‘亂銀堆里看君山’一句,很美。”
嚴冰沏好茶,說:“我不抽煙,何老師也非癮君子,省事了。不然的話,于老師就沒法待了。”
“嚴校長真是體恤民情。你讓我們來,不只是品茶吧?”
“當然不是。”
嚴冰言歸正傳,談到學校想設立一個專門資助貧苦學生的基金會,經他奔走聯系,本市的商會會長、醫藥界巨頭關山越,雖已年過七旬,對此事極為熱心,愿意捐助十萬大洋。但他有個請求,指名要何地畫幅他的油畫肖像,而且要現場對著真人畫。
何地冷冷地一笑,說:“他不過是一個商人,懂油畫藝術嗎?”
嚴冰說:“你說話不怕閃了舌頭,他當然懂!他年輕時讀過英國的倫敦大學工商系,歷年經商取財有道,還鼎力資助過孫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他能用英文寫詩寫文章,也能填詞度曲,是個學貫中西的人物。何老師,他很欣賞你的肖像油畫呵。”
“畢竟我是為錢而作畫,可悲可嘆。”
“不,你是為需要幫助的貧寒學子作畫,此為大愛,何悲何嘆?”
何地立刻不作聲了。
于今嘴一噘,說:“這就好了,他只需要何老師的畫筆、油彩,我能去干什么?”
嚴冰說:“你不能不去,關老爺子專門點了你的名哩。”
“這就怪了。”于今說。
“關老爺子知道,畫家畫他的肖像,必須保持一個固定的姿勢和表情,真正畫完要十天乃至半個月,每一天,要在固定的時段坐在同一個地方,這是光影的需要。他說他年事已高且有病,恐怕會‘貌寢’。”
聽到“貌寢”二字,何地、于今忍不住笑了起來。因為這個古籍里的詞語很形象,但知之者甚少,表示人無精神,五官昏昏睡去。這個老爺子果然高雅!
“老人睡著了,何老師怎么畫?但他平生酷好古琴名曲,只要聽到琴聲便睡意全消。老人一有睡意,于老師你便撫琴,提起他的精神。而何老師聽了你的琴聲,也會腕底生風的。”
于今一笑,說:“何老師未必……喜歡聽。”
何地忙說:“我能一飽耳福,幸甚矣哉。”
嚴冰說:“那就說定了。從明天開始,每天上午十點到十二點,你們辛苦兩小時。關老爺子會派小車來接,九時半在校門口迎候。”
何地、于今幾乎齊聲答道:“好。”
走出辦公大樓,深秋的陽光薄如金箔,在他們眼前飄飛,很美。風聲颯颯,帶點兒清涼。
于今問:“何老師,古琴曲中,你喜歡哪幾支?”
何地說:“我喜歡《洞庭秋思》《陽關三疊》,還有《歸去來辭》。我聽人說,尊父和你精于蜀派指法,又吸取了吳派技巧,‘吟猱’最見功夫。”
“你聽過?那我就多彈這幾支曲子。”
“我家有你們灌制的唱片,是上海百代公司出品的。我畫畫時,常聽哩。”
于今有些吃驚,隨即又平靜了下來,說:“我家的墻上,掛著何先生的油畫,不是肖像畫,是風景畫《雨湖春曉》,柳堤邊的漁舟,湖波上的輕霧,短橋上的人影,可以讀出一個‘靜’字來。”
“哦?”
“你別奇怪,是你的一個好友轉贈給我的,我非常喜歡。”
“你喜歡肖像畫嗎?”
“當然。你畫得很有激情,不是用筆在畫,是用心在畫。”
“于老師什么時候有閑了,我給你畫一張肖像畫,好嗎?”
“謝謝。上午有時間嗎?”
“我上午沒有課。”
“到我宿舍去吧。明日該為關老爺子彈琴了,先練練,你也給我提提意見,怎么樣?”
“好。只聞說你的宋琴,極古雅,正想開開眼。”
……
半個月過去了,關老爺子的肖像畫,在于今的琴聲中,何地順利地畫好了。
半年過去了,春暖花開時,嚴冰(當然還有其他的同事)忽收到何地、于今送來的大紅請柬,恭請參加婚宴。嚴冰忍不住哈哈大笑,有情人終成眷屬,他自謂功不可沒!更喜關老爺子配合得嚴絲合縫,把這出牽線搭橋的大戲演得圓圓滿滿。
在舉行結婚儀式的喜堂里,正面墻上,掛著何地畫的大幅油畫:他和于今手牽手走在林間小道上,腳邊開著紅色、白色的杜鵑花。畫兩邊是嚴冰用隸書寫的紅紙賀聯:“何地繩纏鴛鴦鎖,于今花綴連理枝。”
性博士
湘楚大學社會學系的幸怡齋,四十多歲了,依舊是個獨身。論家世,他出自城中大戶人家,經濟豐裕;論學識,留洋修過博士,著述亦多;論人才,無殘無疾,中等個子,只是年漸長,顯得干瘦而有些老氣。他不是不能成家,是不想成家,喜歡一個人獨來獨往,自由自在,“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年青時,幸怡齋的碩士生導師池上波,字尺水,曾含蓄地問過他:“你可否是天閹?”他也回答得意味深長:“天閹倒不是,是心閹。”古人把男子原本就沒有性能力,稱之為“天閹”。而“心閹”是什么?幸怡齋說:“是從心里不斷閹割這種想法,我只在這個方面治學。”
池上波年長他十余歲,主業是研究中國農耕社會的鄉村經濟,但多才多藝,能書畫能刻印,他為幸怡齋畫了一張宋代號稱“梅妻鶴子”的林和靖賞梅圖,一尊孤石伴一樹怒放的白梅,賞梅的林和靖身邊,閑立兩只小鶴。然后題了一首詩:“幸郎第二林和靖,不隱孤山隱校園,勤治婚戀性學史,書窗相對不愁鰥。”又為學生刻了一方印:“白梅花下影不孤。”
幸怡齋的重要著作有《中國婚姻史》《中國性文化概說》等。他字破卷,典出“讀書破萬卷”的古語。他確實讀書廣博且精細,而且記憶力驚人,有綜合能力,有思想,是塊做學問的好材料。在《中國婚姻史》一書中,論述到早期婚姻的“搶婚”,舉《易經·屯卦》為例:“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池上波極為贊賞,大聲說:“好!”
但《中國性文化概說》一書,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中期面世后,卻掀起軒然大波。書中談到一夫多妻、同性戀、戀童癖、自戀、鞋戀、物戀、春宮圖、相思卦諸多情狀,令本地“孔德會”的頭面人物和許多學生家長極為憤怒,認為這是誨淫誨盜、敗壞世風,報紙上罵幸怡齋為“性博士”。輿論洶洶,一致要求學校開除幸怡齋。
校方當然是頂著壓力,置之不理。幸怡齋也毫無怯意:能開除他的教職,能將性學開除出學問之外嗎?
只有池上波按捺不住,奮筆疾書一篇篇文章,登載在本地的幾家重要報刊上,為學生據理力爭。從英國人靄理士的名著《性心理學》,談到“花間派”詞人的艷詞、《金瓶梅》及《紅樓夢》中的性文化,概言“食色性也”,色是從生物基礎里生長出來的一種男女之間感情上的吸引力,是“人之大欲”。而他的學生幸怡齋,是個恂恂君子,治學于“性”何罪之有!在他的引導下,該校許多名教授,亦披掛上陣,口誅筆伐,令一些假道學及無知者落荒而逃。
幸怡齋特地去了池府,站在老師面前,深鞠一躬,說:“尺水先生,耽誤你多少寶貴時間,學生勞你操心了,謝謝!”
“不必謝。老師是為捍衛學術的純潔與尊嚴,不吐不快!快坐下,我們好好聊聊。”
“我最近在寫一本談《紅樓夢》性愛的書,先生的大文給了我許多啟發。”
“我不過粗粗一說,不足為據。你定有新的發現,說來聽聽。”
“不敢。比如:賈母的老年性心理探微,賈寶玉的性夢,相思局的性游戲意味,鳳姐為何親近秦可卿,焦大的口唇快感,斗草的潛本文剖析……等等。”
“好,角度小,取材新。斗草又名斗百草,為少男少女春令的游戲,你有什么見解?”
“《紅樓夢》第六十二回所描寫的斗草,參加的都是女性,所斗花草與對答之詞,都體現了男與女、陽與陰的對應關系,如‘觀音柳’與‘羅漢松’,‘君子竹’與‘美人蕉’,‘星星草’與‘月月紅’,‘牡丹花’與‘枇杷果’,‘姐妹花’與‘夫妻蕙’,潛意識表現出她們對男性及美好婚姻的渴望。”
“此書寫完,我來寫一評文,如何?”
“先生就太抬愛我了!”
……
本地廣播電臺有一檔節目“子夜談婚論愛”,配樂朗誦名女人評說戀愛與家庭的散文,很受人歡迎。節目開始時,所播的歌曲為《叫我如何不想他》,由幸怡齋應邀作詞,一共三段,每段四句,每句七個字。作曲的是省城長沙的一位名作曲家,采用了花鼓小調的音樂元素,活潑、輕快、舒展,很好聽。凡有收音機的家庭,都愛聽這檔節目,年青的女子更是如醉如癡。因作詞的幸怡齋是本土人物,于是有了人數眾多的追星族。
幸怡齋有一個收藏室,里面陳列著豐富的性文化器物及圖文資料:銀元寶、玉如意、金蓮鞋、鴛鴦鎖、竹夫人、湯婆子、春宮圖、《金瓶梅》與《紅樓夢》的繡像畫……門楣上懸一橫匾,上寫四個篆字:“風月無邊”。門兩邊的對聯為:“十八之下莫探眼,八十以上應當心。”什么意思呢?未成年者嚴禁參觀,氣虛力衰的老人要當心在看過后心臟加速、血壓增高。他經常利用休息日,接待前來參觀的人,并進行講解。他講解時,神態平靜,語速不急不慢,如老僧說法。
他的性文化研究與獨身主義,多年來,既讓人津津樂道,又讓人困惑不解。
池上波常暗示他:“人總要老的,老了總得有個伴,趁著現在還是中年,亡羊補牢未晚。”
幸怡齋說:“先生,世俗認為這門學問不干凈,我自身得一塵不染,讓這門學問變得干凈,讓有邪念的人不能興風作浪。”
“蠢話!”池上波啼笑皆非。
幸怡齋忽然收到一位陌生女子的情書,隔三差五就有一封,說喜歡他的歌詞《叫我如何不想他》,說喜歡他的風流倜儻,夢中常見到他的英俊與儒雅……每信落尾的一句話,必是“教我如何不想他”。幸怡齋哈哈一笑,給那女子復了一信,稱下個星期天上午,他將在雨湖公園的聽雨軒開講座,屆時可一睹他的風采。
星期天上午九時,當可容百來人的聽雨軒座無虛席時,幸怡齋緩緩走進門,再走到講臺邊坐下。第一句話是:“有人沒見過我吧,我就這副模樣,又老又丑!”
滿堂笑語飛揚。
坐在最前排的一個青年女子,忽然站了起來。她長發披肩,身著紫色碎花旗袍,把手中的小提包甩了甩,一噘嘴,說:“原來是這樣一個糟老頭子!”然后,高跟鞋嗑嗑嗑地響出了會場。
幸怡齋仰天大笑后,念道:“叫我如何不想他,花前月下共飲茶。原來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大家又是哄堂大笑。
“諸君,我現在正式開講,題目是《五代“花間詞”中的性意識解秘》……”
唐琴
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古城湘潭有一個為數不小的琴人群體。何謂琴人呢?即是家有古琴且能彈奏古琴的人。
而古琴,最少要是清代以前的玩意,因上有七條弦,又叫“七弦琴”。琴身為狹長形的音箱,長約三尺有余,琴頭略寬于琴尾;面板為桐木、杉木,底板為梓木,當然也有使用楠木、紫檀之類名貴材質的;外側有用金屬、瓷、貝殼制成的圓星點十三個,名曰“琴徽”,也叫“徽位”;底板開出大小不同的出音孔,謂之“龍池”“鳳沼”。上年歲的古琴,當然價值不菲;能操琴的人也多是有身份、有財力和有學養的人。
年過花甲的秋一江,就是古城聞名遐邇的琴人。他蓄著一把黑得放亮的長胡子,寬臉、高鼻、濃眉,體量高大,人譽之為“美髯公”。他是個大畫家,人物、山水、花鳥俱能,畫價每方尺達銀元十塊,誰若還價,他一口粗氣把胡子吹得飛揚起來,噴出兩個梆硬的字:“送客!”
他喜歡彈古琴,也喜歡收藏古琴,林林總總,好幾十張。最珍貴的,是唐代雷威所制的“天籟”琴,除了他和家人,別人沒這個眼福一觀。他常用這張琴,彈奏古曲《高山流水》。可他就沒有像高山流水結知音那樣的機緣。他認為這世上,可堪入目的人少之又少。
城里有一家老字號“醫琴坊”,老板年過五十,叫班師捷,矮而胖,臉肥、嘴闊。班家相傳的手藝是修古琴,給琴看病、治病,不就是“醫琴”么。能命出這種店名的人,不俗,也讀過些書,這是無疑的。班思捷看過、摸過、修過不少古琴,但家里卻無經濟實力去收藏古琴;也懂琴理、樂理,卻沒有閑功夫去操琴,因此,他不是琴人,只能稱為“修琴匠”。
班思捷早聽說了唐琴“天籟”,在名人手上歷代傳承,現在藏在了秋府。他真想看一看、摸一摸。可“天籟”似乎從不出毛病,沒送來修過。其實,就算“天籟”要修,秋一江也會送到省城長沙去,他認為本地的修琴匠,沒這個能耐!
終于班師捷忍耐不住了,小小心心去叩訪秋府,虔誠地說明來意。
秋一江既不讓客人落座,也不泡茶、遞煙,仰天哈哈大笑后,問:“你是開‘醫琴坊’的?”
“是。”
“好高雅的名字!可我這里無琴可醫。”
“我只想看看‘天籟’。”
“唐琴如稀世美人,能讓你這個俗人看嗎?送客!”
班思捷一張臉都氣白了,這真是奇恥大辱,掉頭便匆匆而去。
客人走了,秋一江在客廳里笑了好一陣,覺得心里很痛快。然后,走進了他命名和題匾的“琴巢”,這是他儲琴和彈琴的房間,很寬大,很明亮。墻上掛著一排排古琴,房中央擺著黃花梨木的清代琴案和圈椅,琴案一端擱著一只明代的銅香爐。
他點燃一支檀香,插在香爐里,再從一個大書柜里取出一個楠木琴匣。他打開琴匣,小心地搬出“天籟”琴,放到琴案上。然后坐下來,彈《高山流水》一曲。
琴聲一響,所有房間里的聲音都靜寂了。他的夫人正在佛堂,剛才還在輕敲木魚細聲念經,忙停住木棰閉住嘴。廚房里的傭人,洗菜不敢弄響水盆,切菜不敢驚動刀、砧。
這是秋府的規矩。
彈完了《高山流水》,秋一江走出“琴巢”,興致勃勃地進了畫室。
宣紙早鋪好了,墨、色早備下了。他拎起一支大筆,略一思索,便急速地畫起來。勾完了線,再敷色,畫的是他自已,坐在庭院中的花樹間,彈著“天籟”琴。畫題是《斯人獨寂寥》。
夫人不知什么時候進了畫室,站在畫案邊,忍不住輕輕地說:“可憐、可惜、可嘆。”
秋一江擱下筆,板著臉問:“你說什么?”
夫人微微一笑,說:“可憐你知音難覓,可惜你明理太少,可嘆你矜狂忤人。”
“我做錯了什么?你這樣憤憤不平!”
“一江,剛才班思捷想看看‘天籟’琴,何必粗言粗語以拒?有必要得罪人家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活世上,圖的是一個‘和’字。”
秋一江猛地拿起大筆,蘸飽了黑水,在剛畫好的《斯人獨寂寥》上,狠狠地胡涂亂抹,還要這畫做什么,毀了!
夫人默默地走出了畫室。
古城的一份小報上,忽然刊出署名“鑒偽”的文章,題目為:《秋一江的“天籟”琴應為贗品》。浩浩蕩蕩四千來字的文章說得有根有葉:唐代雷威所制的琴,底板多用楸梓,而楸梓之色是微紫黑,鋸開可見。而這張“天籟”琴,底板顯然是用的黃心梓,其木中心之色應該偏黃,這就不是唐人所講究的格局……
秋一江很快就讀到了這篇文章,氣得在家里咆哮如雷,這不是羞辱他嗎?
“我的祖上瞎眼了?買回了不是唐琴的唐琴!這個借名‘鑒偽’的人,真是混帳透頂!這口氣,我怎么咽得下去!”
秋一江第一次屈尊給琴人們發了請帖,約定日期,在雨湖公園的“云霞閣”聚會,他要當眾出示“天籟”古琴,并當場驗證真偽,以正視聽。
那是個初夏的上午,不少人——琴人和非琴人,都來到了古香古色的“云霞閣”。這是古城的盛事,誰不想一睹為快。
當聘請的一個木匠,當眾把“天籟”琴剖開,然后撬開琴的底板,再橫里鋸開。的的確確,真真切切,楸梓的木色發黑泛紫,誰說它不是唐琴!
秋一江臉色一下子開朗了,捋了捋胡子,放聲大笑。笑到高潮處,忽然戛然而止,脊背上立即沁出了冷汗。這唐琴就這么毀了?為了一篇胡猜亂說的文章,為了他家和自已高貴的面子,居然愚蠢到當眾鋸琴以作求證!
秋一江再看了看在場的人,獨不見“醫琴坊”的老板班思捷。這個人不是要看“天籟”琴嗎?他應該是早知信息的,怎么沒來?在這一剎那間,秋一江似乎明白了什么。
過了幾天,秋一江攜破琴去了長沙,找了好幾家修琴店,口徑何其一致,都說“無力回天”!
回到家里,秋一江惆悵了多日,埋怨了多日,憤怒了多日。
夫人說:“不是有家‘醫琴坊’嗎?也許這個班思捷有絕招可醫。”
“找他,呸!”秋一江沖口而出,然后又放緩聲調,“我……去……試試看。”
秋一江輕裝簡從,攜琴去了“醫琴坊”。
當時的情景怎樣?彼此間說了些什么?沒有人看見和聽見。
但兩個月后,唐琴“天籟”傷好復原,安安然然回到了秋府。而且,秋一江和班思捷,此后成了來往頻繁的朋友。
班師捷常在一天的勞作之余,趁夜色去訪秋府。
“師捷老弟,請到‘琴巢’品茶。”
“謝謝,一江兄。”
“品茶后,我給你彈《高山流水》,如何?”
“我就愛聽這支曲子。”
責任編輯:趙燕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