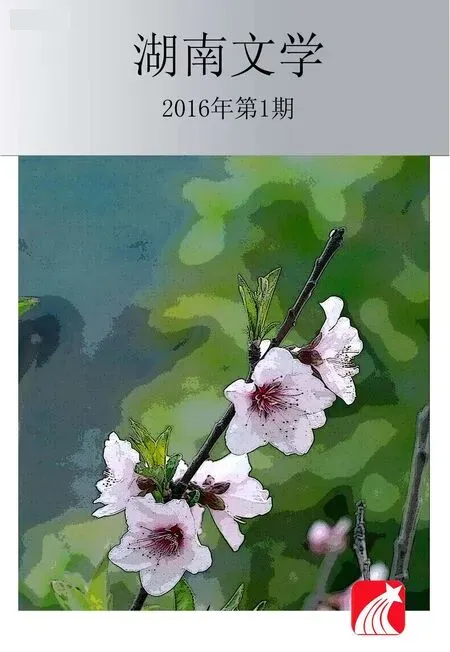《楚門的世界》:群居生活的幾個關鍵詞
→謝宗玉
?
《楚門的世界》:群居生活的幾個關鍵詞
→謝宗玉
一
現在,我想用電影《楚門的世界》,來說說“城市與人”的關系,為此,我不得不拿自己曾為之熱淚盈眶的主人公——楚門開刀。
《楚門的世界》講的是,一個名叫基斯督的導演,為了真實而完整地表現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的全過程。在楚門還是受精卵時,就把他的撫養權買下了。然后專門為他搭建了一個大得無法想象的舞臺,舞臺虛擬了一個四周環海的城市,名為桃源島。
城市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都是道具。連空天空、太陽、月亮、大海、雷電、風雨都是布景。居在這個城市成千上萬的居民都是群眾演員。目的就是為了給主人公楚門營造一個真實可感的生活場所,讓他對自己演員的身份完全一無所知。城里安裝了五千多個攝像頭,將楚門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一天二十四小時全程拍錄下來,全球同步播放。時間已長達三十年之久。楚門的粉絲,或者說這個“真人秀”的在線看客長期高達十幾億人。窺探楚門的私生活成了全世界人們時髦的休閑方式。
孰料有一天,楚門因為亡父的離奇復活,終于發現自己身處一個巨大的騙局中。于是他想方設法,甚至不惜以死抗爭,最終擺脫了導演基斯督的控制,沖出桃源島,去了外部世界。全球粉絲都為他的壯舉歡欣鼓舞,激動得要抽瘋。
五年前,這部片子曾把我弄得號淘大哭,原因是我從主人公楚門身上看到了自己循規蹈矩、身不由己的一生。那種像被電腦程序編排好了的生活軌跡,讓我內心的抑郁和悲哀,如楚門一樣越積越重,越積越厚。然后我辭職了,人生的軌跡毫無邏輯地拐了彎,可感覺如何?是不是自由得想要飛呢?并沒有。生活依然是按部就班地過著。
正因為這樣,我開始對楚門的反叛有了懷疑。
那種被設計、被規劃的感覺,顯然是整個文明制度造成的。準確地說,是群居生活的規律和法則造成的。只要我們逃不出現有的文明制度,那么我們的遭遇就是注定了的。這一點,在楚門離開之前,基斯督已跟他剖析得相當清楚。
五年前,我以為導演彼得·威爾對楚門的行為是贊許的。等回頭再看這部片子,我發現導演在贊許的同時,還在電影中蘊藏了生存和文明的二律背反悖論,它像一個無邊無際的迷宮,帶給人的思索是無窮的。這正是我要為這片子再寫文章的原因。
很顯然,這部片子的象征意味很濃。桃源島象征著伊甸園,也可以說,象征著我們生活的這個星球。真人秀的導演基斯督象征造物主基督,桃源島的萬事萬物都是他“制造”出來的。楚門對基斯督的反抗,可看作是亞當對上帝的反叛,也可看作是人類對造物主的對抗。這些,我在別的文章中有過論述,按下不表。
這篇文章,我只想用群居生活的法則,抽絲剝繭般,把我的偶像楚門親手毀掉。我以為殘酷的真相比空中樓閣式的夢想,更讓人成熟。如果有讀者因我這篇思想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的文章感到心痛,那么請
相信,我的痛勝他十倍,我痛徹肺腑!
二
“朝九晚五”,是一種標準的都市生活。亡父的離奇出現,就像一根導火線,點燃了楚門對這種生活的反思:為什么順順當當、水到渠成的生活,好像并不是自己想要的呢?為什么從記事開始,命運就像一根被洪流裹挾、載沉載浮的木頭,從來都不由我們控制?為什么所謂的幸福滋味總這么被動,而且可有可無?我們小時候的理想都遁逃到哪里去了呢?原以為我們都是自己的國王,長大后才發現,我們其實是萬千瑣事的奴仆。對電影里的楚門而言,哪怕是一次小小的斐濟之行,都無法達成。
我們很容易把種種不遂人愿的現實歸罪于上司或同事,單位或家庭,卻不知那只是表象,真正的罪魁禍首卻是我們曾為之無比自豪的人類文明。
如果說,上帝以無為而治的方式,給這個萬物搭建了一個散漫而自然的舞臺,那么,文明則是以大包大攬的方式,給人類搭建了一個“斗榫合縫”的舞臺,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城市。它跟基斯督給楚門搭建的桃源島如出一轍。
如果我們把大自然看作是原生態,那么桃源島和其他千千萬萬個城市都是“人造空間”。如果人類不存在,這些空間就不會在地球呈現。當然,我們也可以說,如果螞蟻不存在,蟻窩也不會自然生成;如果鳥兒不存在,鳥巢也不會自然生成。問題是,鳥巢和蟻窩的建造,憑的全是一種懵懂的生物屬性,它可以看作是上帝的假手之作,而人類文明所建造的一切,除小部分受其生物性影響外,更多依靠了人類的社會屬性。
換句話說,城市從來就不是上帝給人類的應許之地。上帝許給人類的,只是像猴子那樣,在山林跳來縱去,即使允許擁有巢穴,也應該是非常簡陋粗糙的。上帝根本沒想到,人類會憑借日益清醒的智慧,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把一個叫文明的東西伺養得這么妖嬈,簡直比神話中的碩大無比的怪獸更可怕。它隨便就可以在地球上劃一塊地盤,建一座城市,而且完全不按上帝的布景邏輯,恣肆妄為地規劃著里面的一切事物。
是的,文明當初是由人類一點一滴創造的。但現在,很顯然,文明已主宰了我們的生活。文明不是某個人創造的,文明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所以文明努力的方向,注定是朝著集體利益最大化的方向。至于個體的“苗頭”,只要是為了集體利益最大化,該砍就砍,該削就削,活不成的,那就去死!正如城市里那些被修剪得整整齊齊的花草不再是它自然的模樣,被文明制度規范得服服帖帖的人們也不再是山林里猿猴的模樣。
恩格斯說,“勞動創造人本身”,這話很對。人類不再是自然生長的山野精靈,而是文明大工廠流水線上的產品。寫到這里,我想起在學校的監控下我刻苦攻讀的兒子,他正在被文明的大錘,敲擊成社會需要的模樣。很痛。但有什么辦法?
就這樣,我們不再是自己了,一個個成了這個星球原本沒有的怪物,或者說變種。相對其他物種而言,我們都是文明的“虛擬產品”。
既然這樣,作為文明產品的楚門,又何來那么多感慨?基斯督不是胸有成竹、信心滿滿嗎?他自以為可以操控楚門的一切,自以為可以順理成章地演繹楚門的“完美人生”。可結果呢?他失敗了。
基斯督其實未必就一定象征上帝,他也可看作是人類文明的象征。所以基斯督的失敗,看作是人類文明的失敗,更意味深長。上帝或許是一個凡事了然于胸的先知,由人類集體智慧虛擬出來的文明則絕對不是,它看起來更像一個自高自大、自吹自擂的“酒鬼”。所以“人類一思考,上帝就會發笑”。
在上帝心中,萬事萬物,條分縷析,所以億萬年來,宇宙永遠是那么風清月明,即使偶爾有失足的流星,也是無傷大雅的美麗風景。而人類何去何從,文明這個“酒鬼”根本就沒弄清楚,所以幾千年來的文明史,便是人類自相矛盾、把地球搞得烏煙瘴氣的歷史。
我們不妨以“楚門事件”來分析,看看文明是怎么自相矛盾的?為了發揮個體的最大潛能,為人類集體利益添磚加瓦,文明會不遺余力地鼓吹個體的自由和獨立意識,盡可能地發揮個體的主觀能動性。它饋贈給每個人“英雄主義”的夢想,并利用現有的一切知識,來拓寬個體的心靈格局。讓每個人內心都是一個豐饒的世界,讓每個人都是他自己世界的國王。
是的,覺醒的個體從懵懂中掙扎出來,他們看起來是從上帝的手中解放了。問題是,文明為了人類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又不得不對個體的所有言行,作了嚴格而繁瑣的規范。如有違反,必受懲罰。比如說,人類發現那個叫“電”的玩意,它的確給人類生活帶來了無法想象的便捷,但要使用它,規則就不下一百條。
現在,對比出來了,而且很明顯。如果說,上帝對它手中懵懂的萬物采取的是放養的姿態,就是說,由著萬物去“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它只會從中微調一下即罷。結果萬物呈現出現在這般相生相克、互利互惠、欣欣向榮的模樣。
文明對它手中覺醒的人群采取的卻是圈養的形式。它事無巨細,大包大攬,妄圖為人類找到一條灑滿陽光的康莊大道。結果有沒有找到,姑且不論。人類靈敏的心靈顯然被它的條條框框給弄痛弄傷了,弄得忍不住要呻吟,要吶喊,要叛逃。
這就是被文明豢養的楚門,為什么還要發出一些看似“得隴望蜀”的感嘆。文明的悖謬之處就在于:一方面它打破上帝的黑屋,喚醒了懵懂的個體,另一方面卻又苛責有著豐富內心的個體成為比上帝監管時更順從的奴隸。這才是楚門要叛逃的根本原因。
更何況,上帝種植在我們身上的生物性還沒有被文明完全鏟除,日益惡化的生存環境也讓它不由自主地成了反叛者。就是說,人體內的社會屬性認可的舒適環境,恰恰是人體內的生物屬性難以忍受的。浩瀚的天空,鳥兒可以在上面飛,魚兒卻不可以。可現在人身上,既有鳥的屬性又有魚的屬性,你叫他們何以棲身?
三
可惜,除了地球,楚門哪也去不了,這種逃離看起來象征意味很濃,其實產生不了什么積極影響,他無非從一個生存圈換到另一個生存圈,一個舞臺換到另一個舞臺而已。日益深化的文明已將整個地球都異化成了一個超級舞臺,那么,作為個體小小的人兒,無論逃到天涯海角,都避免不了被操控的命運。
我們一出生,就注定了悲劇的色彩。個體除了要戴上文明制度的枷鎖外,還要與別的個體相爭。我們的口號是:“天賦人權,每個人都神圣不可侵犯,每個人都有為自己謀幸福的權力。”文明把我們的欲望之火撥得很旺,把我們的胃口吊得很高,文明還幫助人類速度繁衍,可文明卻帶不來滿足欲望的生存資源。
一個人要想生存下去,必須奮斗在人群中。而人上一百,形形色色,群居的人們只能在各種糾葛、矛盾和牽絆中度過一生。夸張一點地說,以群居為特征的城市,不管是上層還是下層,不管是領導還是平民,沒有一個人能完全操控自己的時光。那些領袖人物的日常生活,不都是按日程編排好的嗎?就說電影里的基斯督吧,他雖然可以操縱主人公楚門,但他上頭還有更大的老板決定他的命運。何況,三十年來,他也完全被這個真人秀欄目困住了。他的全部心思幾乎都在圍著楚門的喜怒哀樂打轉,他在編排楚門的同時,也被楚門塑造著。這大概就是群居生活的常態吧?
我想,就算真有上帝存在,那上帝也只能在眾神的彼此牽絆中度日。西方神話,就是這么寫的。
所以,要想把群居生活過好。生而為人,“妥協”便是生存最為關鍵的一個詞。
城市是文明的淵藪。復雜的城市要想如機器那樣運轉起來,個體的人就必須安分守己地做好機器配件的角色。工業文明最顯著的特點就是社會化大分工越來越細,人們只有把各自的工作干好,才可享受足以活命的生存資源。山林里的猴子跟城市人一樣,也是成群結隊的,但它們是單干戶,沒什么分工合作,所以構不成文明社會。它們之間是一種單純的屈從關系,即弱者屈從強者。人群則是一種互相妥協的關系。從某種意義上講,妥協既是文明的一部分,也是文明加速發展的潤滑劑。說到底,那些條條框框,都是多方利益集團各退半步的情形下制訂的。
妥協,它不是和稀泥,而是人類文明的精華。如果說屈從關系只是一種私關系的話,那么妥協關系則具有很強的統一性和普適性。它不是個體之間私人劃定的,而是由整個文明決定的。個體的人若不遵守,想肆意欺負弱者,那么就有專門的審判機構對他進行制裁,個體的人再不要憑一己之力,去報殺父或奪妻的仇恨了。
可惜情商不高的楚門不懂這些,在一場巨大的騙局中懵懵懂懂度過三十年,一旦發現自己被設計了,就造反不干了。他也不想一下,如果說他是被設計了的,那么圍繞在他身邊三十年的其他配角,就更是被設計了的。人家能安之若素,他為什么不能?作為演員,他是全球巨星,但作為桃源島的居民,他只是一名普通的保險經紀人。他必須遵循這個小城的法則,才可能在這里安居樂業,頤養天年。正是他的不妥協,打破了桃源島的平衡,把桃源島拖進了土崩瓦解、萬劫不復的境地。
四
隨著都市化進程的加速,人類進入高度聚居的社會,個體的人需要進一步約束自然天性,才能跟得上時代和文明越來越具體、越來越繁雜的要求。這時,人類每一個聚居地,都跟桃源島差不多——一個碩大無比的舞臺。
既然是舞臺,那么“表演”,就是群居生活的另一個關鍵詞。
楚門未解其味,當發現妻子、父母、朋友、同事,以及街上所有的陌生人都在他面前演戲時,他歇斯底里,簡直要瘋了。又怕又氣的妻子,不得不指責他沒有一點專業精神。他不知道,表演是群居生活一種很重要的日常事物。
在城市這個巨大的攝影棚內,我們用語言表演,用行為表演。每個人都是天生的表演家,或者說,天生的戲子。從一出生,我們要學會表演一種叫哭的表情,才會有奶吃。(其他動物,單這一項,一輩子都學不會。)我們要學會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才能左右逢源,迎來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
是的,在這個片子中,作為戲子的楚門,的確被導演控制了。但在人生的舞臺上,我們什么時候沒有被導演控制呢?最開始我們的導演是恨鐵不成鋼的父母,接著是驕橫跋扈的領導,然后是性格強悍、說一不二、自以為是的妻子(丈夫),再然后是那些自私自利、無情無義、貪婪無比的“啃老族”,最后,殯儀館的主持人給我們導演一場或冷清或喧嘩的謝幕劇。
作為導演的寵兒,在這個影片中,楚門還只是一個隱性演員,只要他不跟導演叫板,不撂挑子,那么無論他說了怎樣出格的話,做了怎樣出格的事,導演都會讓他一輩子衣食無憂。可憐的是他的好友馬龍,從幼稚園開始,就做了他的配角,在這部長達三十年的肥皂劇中,他幾乎每一句話都是臺詞,每一個動作都是表演。只有在楚門失蹤的時候,他才說了一句屬于自己話:“他不見了。”做了一個屬于自己的表情:雙肩一聳,兩手一攤。結果被導演罵得要死,就算這個肥皂劇不以楚門的叛逃結束,他的下場也很可能是被辭退。
楚門的妻子并無過錯,只因為被楚門的尋根究蒂弄得束手無策,導演就打算把她換下來,再找一個女人讓楚門煥發“第二春”。楚門的父親正因為無法勸阻楚門“揚帆遠去”的理想,所以只能以“非正常死亡”的形式丟掉這份工作。
都市的生存法則不正是要求我們把屬于自己的角色演好嗎?文明的演變也可看作是一部加長劇,它需要整個人類配合演好。哈提帕文明、奧爾梅克文明、古納巴泰文明、邁錫尼文明的神秘消失,或許就是那些民族的人沒有演好自己的角色,結果也像這場真人秀節目一樣崩盤了,整個民族被時代無情的秋風掃出了歷史舞臺。
翻開史書,這種例子不勝枚舉:戚夫人沒有演好自己的角色,被呂雉當人彘泡在缸里給腌了;宋江沒有演好自己的角色,致使一群頂天立地的好漢下場悲慘;楊廣沒有演好自己的角色,致使一個大好的朝代迅速滅亡;慈禧太后等一小撮權貴沒演好自己的角色,差一點讓一個古老王國四分五裂。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愛填詞的李煜,愛畫畫的宋徵宗,以及說話如滔滔江水般的希特勒,都同楚門一樣,隨心所欲表演了與自己身份不合的節目,結果謝幕無不慘烈。
走出桃源島的楚門,其命運將如何?真難說。
語言的產生,其實就是為了讓人類的表演更加準確精彩。語言從一開始就具有臺詞的成分。我們的祖先之所以要結結巴巴把一個個新詞從喉嚨掏出來,就是為了讓自己做一名更合格的戲子。可以說,如果沒有群居生活,沒有可供表演的舞臺,人類就不會有語言的產生。語言是群居的產品。
“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在人類文明的大舞臺上,縱使你巧舌如簧,你最好也只講屬于你這個角色的臺詞,多說少說,都是敗筆,都會影響你命運的走向。我曾經認識一個人,自認為口才了得,在任何場合下都夸夸其談,把很多屬于領導該說的話都說了,結果無論他在其他方面表演得多成功,最后只能郁郁不得志。
可惜的是,人群中的“歪嘴和尚”太多。有些人一輩子念錯臺詞,什么話不利于團結,不利于合作,不利于凝聚人心,不利于整合力量,不利于文明發展,他就說什么話。
當然,古往今來,就沒有不說錯話的人。只是,錯話說得少的人,在群居社會,他的收獲遠遠大于他的真實才能可以給他的。錯話說得多的人,縱使他才華通天,最后大概也只能向楊過哥哥學一套“黯然銷魂掌”,作為收場。
那么,如何才能念對臺詞呢?道德不是要求我們講真話嗎?如果我們一味地指鹿為馬、指桑罵槐,那么連最簡單的事物都無法命名,溝通將變得困難重重,文明又何以能夠推進下去?
所以,講真話是沒錯的。但講真話只是文明制度的“規定動作”,每個人都要講一定數量的真話。“自選動作”則是講利人利己、利家利族的臺詞。“善意的謊言”永遠是群居生活的通行證。真話是文明的骨骼,臺詞是文明的毛皮。換句話說,臺詞包括真話和謊言,就看在什么時候說真話,在什么場合說謊言。
在這個問題上,楚門簡直做得一塌糊涂,為了追求真相,他盡說不該說的話,臺詞念得一團糟。除他外,他那個一見鐘情的女友,也是一個特別不合格的演員,她亂糟糟的臺詞差一點提前就讓桃源島陷入癱瘓狀態。
五
楚門叛逃的原因,最重要的一點,是他發現自己一直生活在欺騙之中。可是,在妥協中求和諧的群居社會,誰沒有騙過人?誰又沒被人騙過呢?我們之所以要說“臺詞”,是因為群居社會并不苛求于語言的真假,只要求語言的效果,群居生活的本質就是在掩飾和欺騙中求和諧。
人心不足蛇吞象。這句諺語對人類欲望作了生動的注釋。可我們這種駭人的欲望能一覽無遺地公之于眾嗎?事實上,我們變幻莫測的內心有太多事情和念頭需要掩飾,欺騙是我們的生存手段之一,就算是最親密的人也不例外,只是程度不同罷了。你不會告訴你的情人,你早晨把尿撒褲子了,而且在撒尿時,你還意淫了某個影星。在電影中,楚門偷偷摸摸用撕扯下來的畫報去拼圖的行為,不就想瞞過桃源島所有人嗎?楚門只發現自己生活在一個騙局當中,卻不知人人都生活在騙局當中。
人類強大的掩飾能力也是文明的表征之一。群居社會就是由一個又一個或大或小的騙局組成。若是沒有這些騙局,世界看起來就不會那么美好。你的原始目的無非就是為了性交,但你把前奏做得了那么花團錦簇,美不勝收。你向眾人表現出你的善良、勇敢、慷慨和堅毅,你繞了那么大的一個圈贏得了世界,最終,才抱得美人歸。獸類是不需要這種掩飾的。它要性交,前爪朝著母獸的后腰搭過去便是,若有其他公獸阻攔,那么便以鋼牙利爪尖角說話。“將欲取之,必先予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不是一種狡詐的謀略,而是人類文明得以盛行的妥協行為。
事物的兩面性,決定了人文社會沒有絕對的真相和真理。看過電影《羅生門》的人都知道,相同的一件事,通過不同人的敘述,居然大相徑庭。吊詭的是,他們似乎都在說真話。為什么會這樣?這是因為他們只陳述了事物中對自己有利的部分。好比一顆多棱面寶石,每個人只描述了它的某個面。
求知欲是文明發展的動力,但那是指人類對自然事物的探求。若是對探討群居關系的社會事物過于好奇,那總有一天會“害死貓”的。就比如楚門。當發現所有人都向他掩飾真相時,他沒有退回去反思其原因,而是一味地窮追猛打,結果他探求真相的目的是達到了,卻毀了成千上萬人的工作,毀了全球幾十億人早已成習慣的娛樂方式。
所以真正的智者只喜歡對自然科學窮追不懈,找到了分子找原子,找到核子找中子。衛星上了月球,還要去火星。總之是鍥而不舍。而對人際關系采取的則是“難得糊涂”的態度,所謂“不癡不聾,不做家翁”,“凡事以和為貴”。
顯然,我們都是戴著面具生活在人群之中,文明給我們打造了很多副面具,與不同的人打交道戴不同的面具,你若問我哪一副面具才是真的。那么我告訴你,文明的面具只有實用的,沒有真實的。人類真實的面具早已同我們的祖先類人猿一起,消失在山林之中了。
不妨設想一下,假如楚門更老練一點,發現了真相,卻佯裝不知,那他不但可以把導演基斯督玩于股掌之上,還可以將桃源島和全球人們玩于股掌之上。懷揣真相而不說出來,他就掌握了與命運之神討價還價的法寶。他簡直有一萬種方法,把自己弄成桃源島說一不二的掌權人。群居社會的秘密好比俄羅斯套娃,誰也不知誰掌握了哪一層秘密。發現了真相而不說出來的楚門,就相當于從基斯督的包圍圈中跳了出來,去反包圍基斯督。群居生活這種“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關系學運用,大概正是人類樂此不疲的游戲之一吧?
六
被窺視,也是楚門無法在桃源島再待下去的一個重要原因。有一天,汽車電臺的調頻出了錯,楚門發現自己的一舉一動都被暗中監控,這讓他疑神疑鬼,寢食難安。可楚門不知道,偷窺其實也是群居社會的常態。我們生活在一幢幢樓房之中,恰如動物園的一座座籠子。城市就是一座巨大的人類動物園。這時你偷看我,我偷看你,便成了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隨著科技的進步,我們利用各種文明產品,把偷窺的目光投到了全球任何一個地方。人類因足不出戶所造成的心靈危機,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很多人會認為,山林里自由無拘的生活,還沒有關在城市牢籠的生活來得更豐富多彩。
偷窺也是人類文明的原動力之一。有偷窺就有互相比較,彼此模仿;有偷窺就有技壓群芳的欲望產生,有精益求精的自我要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文明便是從這種精益求精中豐滿起來的。當然,有偷窺就有嫉妒、痛苦、暴力和毀滅。據說北宋時期,金人之所以決定大舉南侵,就想偷窺一下江南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結果弄得富饒寧靜的江南“自胡馬窺江去后,廢池喬木,猶厭言兵。”顯然,偷窺是人類全部情感的誘因。我們所有情感的產生,都是建立在與他人的牽連上。從某個角度來說,人類的文明史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因“偷窺”而產生的暴力史。
偷窺也讓我們漫長而蒼白的人生擁用了彌足珍貴的幸福感。對人類來說,幸福是由什么決定的?幸福是由頭腦中的信息量決定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一直是人類向文明進軍的口號,而讀書行路的本質是什么?就是“窺探”。
越是成功的人,被偷窺的概率就越高,狗仔隊追逐的,從來都是那些明星大腕。平凡的大多數人,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鄉鄰,才會對他們的家長里短點評一句兩句。很多時候,被偷窺的概率正是一個人成功與否的測量器。楚門如果知道他不是一個普通人,而是全球當紅巨星,那么偷窺對他來說算什么?電影最后,當他要跨出大門,轉身瀟灑一鞠躬時,他其實已經知道全球觀眾都在看他,這時他已全無怯意,完全是一副超級巨星的范兒。可惜的是,走出那扇大門,他就失去了被全球觀眾窺視的機會,跟著失去了,還有因這種窺視帶來的無數美好日子。
我們已迎來了一個“娛樂至死”的時代,電影《楚門的世界》便是這個時代最精彩的注腳。農耕時代,我們的家人親族都在身邊,我們靠血濃于水的親情維持生命的正能量。但后現代城市把祖輩的人際關系全都打亂了,我們的親人一個個孤零零地散落在四方,圍繞在我們周圍的,都是陌生人,或者說是不同利益的訴求體。
“你是瘋兒我是傻”,在城市冰冷的水泥森林里,陌生人只有既當觀眾又當演員,你娛樂了我,我又娛樂了你,才會讓漫長的人生顯得不那么孤寂。在城市這個大舞臺上,不同利益的訴求體恰到好處地使用“臺詞”,雖然阻止了城市成為“暴力街區”的可能,但充滿了利己主義的臺詞并不能溫暖彼此。溫暖彼此的,很多時候,是靠一種屬于后工業時代的娛樂精神。走在午夜無人的街頭,如果你覺得孤獨得想死,不妨鉆進眾聲喧嘩的酒吧,與無數陌生人瘋狂地舞一回,這時你的熱血馬上就會沸騰,你的精神馬上就會振奮。第二天你又可以人模狗樣、意氣風發地與不同的利益訴求體周旋到底。
楚門的叛逃,也可看作是與傳媒消費時代的一種對抗。但悲哀的是,楚門的叛逃,并不是“自然之子”對文明進程的反思。楚門的一切氣質和品性,幾乎都是導演基斯督塞給他的,或者說,是人類文明塑造出來的。楚門是一個被徹底異化的文明產品。他的叛逃,只相當于一個“不肖子孫”反叛他的“專制父親”。這種反叛行為只能使一團糟的文明更加混亂。
無奈的是,“專制父親”是培養不出神清氣爽的“自然之子”的。上帝也似乎放棄了對人類的管教。既然這樣,盡管我不再認可楚門的行為,但在潛意識,我仍希望時不時有年輕人像楚門那樣站出來,去搗鼓那么幾下。或許不經意間,就點中了文明的命脈之所在呢?哪怕就像電影《雪國列車》中所描述的那樣,反叛的結果是同歸于盡,人類最后只剩下兩棵希望的“獨苗”,我也不覺得可惜。
只要人類的“種子”還在,文明被打碎重來又如何?
責任編輯:易清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