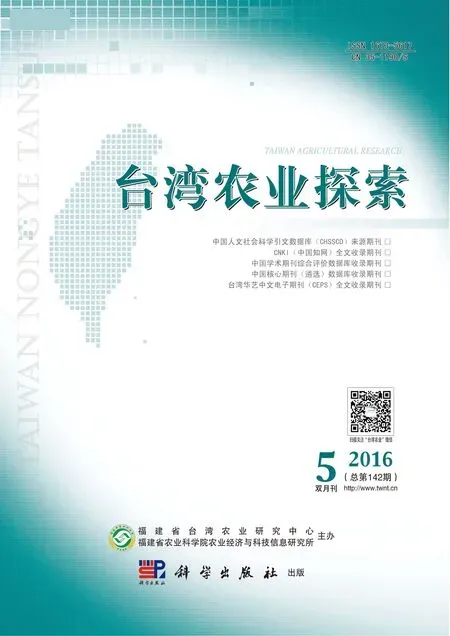價格變化、收入分配與農村益貧式增長
謝東梅
(福建農林大學經濟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2)
?
價格變化、收入分配與農村益貧式增長
謝東梅
(福建農林大學經濟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2)
基于3維Shapley貧困變動分解方法,分析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和價格變化對于農村貧困變動的影響,將價格因素引入益貧增長指數,測度農村增長的益貧性;運用增長發生曲線,結合特定百分位消費價格指數,觀測各百分位平均收入增長率的變動軌跡;在此基礎上,采用減貧等值增長率綜合評價1990—2009年中國農村增長的益貧性質。研究結果表明,農村增長弱絕對意義益貧、價格變化和收入分配影響減貧進程,通貨膨脹的異質性是益貧式增長判斷的重要影響因素。
Shapley分解;益貧式增長;通貨膨脹;收入分配
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總能減少貧困。然而,不公平的加劇,使得增長并不那么益貧[1]。長期以來,影響人們經濟思考的傳統擴散(Trickle-down)效應隱含著經濟增長會自動惠及低收入者,有效的減貧策略只要專注于經濟增長就足夠了[2]。但研究結論并不使人信服,分析結果也不穩健[3-4]。它無法解釋一些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貧困不降反升的現象,也無法回答經濟增長對于低收入者的潛在受益是否會由于不公平的上升而逐漸削弱或抵消的現實思考。貧困變動既取決于平均收入的增長,也取決于增長利益的分配。隨著20世紀90年代經濟領域中收入分配理論研究的復興,包含著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的益貧式增長(Pro-poor Growth)成為主流發展理論,其核心在于實現可持續貧困減少,強調重視增長的性質和模式。
1 文獻回顧
1.1 國際上益貧式增長判斷標準
界定和評估增長的益貧性(Pro-poorness of Growth)必須根據一般的倫理判斷提出明確的益貧標準。
第一,明確區分益貧增長和其他類型的經濟增長。它需要回答:“增長是否益貧,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益貧”這樣的問題。為理解經濟增長對貧困變動的影響,通過分別測度平均收入和收入分配的貧困變動效應,即將總貧困分解為增長效應和分配效應,觀測貧困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的動態變化[1]。KAKWANI等[3]在分解貧困增長效應和分配效應的基礎上,提出“益貧增長指數”(Pro-poor Growth Index, PPGI),測度經濟增長的益貧程度,為判斷經濟增長性質和制定益貧政策提供了有用的分析工具。
第二,評估敏感于低收入者之間的收入分配。假定Lorenz曲線保持不變,低收入者之間增長的受益分配取決于各自最初的收入水平,且高度敏感于貧困線的選擇。如果將貧困線設定在收入分布的眾數附近,可能夸大經濟增長的減貧效應,從而忽略最低收入人群。益貧判斷應該相對更加強調增長對于更低收入人群的影響,一種更為直接的研究方法是觀測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長率。DOLLAR等[2]通過Pen’s Parade計算最低收入五等份組的平均收入增長率,檢驗總增長是否有利于低收入者。RAVALLION等[5]則通過標準化Watts指數,提出“增長發生曲線”(Growth Incidence Curve, GIC)測度20%最低收入人群平均收入增長率的變化,描述收入分配中各百分位受益于經濟增長的狀況。
第三,區分絕對意義和相對意義益貧。國際上,通常采用弱絕對意義益貧、相對意義益貧和強絕對意義益貧反映增長模式。弱絕對意義益貧是指低收入者從經濟增長中獲益大于0(即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長率大于0),貧困減少[5];相對意義益貧意味著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長率高于社會平均增長率,貧困減少的同時,相對不公平下降[3];強絕對意義益貧則要求低收入者的絕對收入增加額高于平均水平,絕對不公平隨著經濟增長而下降[1],這是最為嚴格的益貧式增長定義。KAKWAN等[6]在PPGI和GIC的基礎之上,開發了一種新的增長率測度指數——“減貧等值增長率”(Poverty Equivalent Growth Rate, PEGR),將上述3種可供選擇的益貧式增長定義統一到一個概念化框架中測定增長性質。PEGR既充分考慮平均收入增長率,也考慮到增長利益在低收入者和非低收入者之間的分配,測度符合單調性公理,即貧困減少率為PEGR的單調增函數,最大化PEGR也就意味著最大化貧困減少。
第四,評估需要提供宏觀經濟運行的總體判斷。宏觀經濟穩定能夠促進益貧式增長已經得到普遍認可,通貨膨脹對于低收入者的影響也應該在益貧式增長測度中得到反映。
通貨膨脹對于低收入者的相對影響及其與貧困變動之間的關系取決于特定的歷史條件和制度環境[7]。先驗的觀點通常認為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能更有效地抵制通貨膨脹的影響。FISCHER等[7-10]詳盡地概述了通貨膨脹對經濟的潛在影響,但沒有明確假定低收入者相對受到更多的損害。之后,大量的實證研究通過跨國跨期樣本分析通貨膨脹對于不公平和貧困的影響,調查結果支持“低收入者比高收入者遭受更多通貨膨脹損失”的觀點,通貨膨脹加劇了收入分配不公平,趨向于減少最低五等份家庭的收入份額,并趨于增加貧困。在益貧式增長的理論文獻及其運用中,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得到了廣泛關注。特別是在整個收入分配過程中,相對價格變化對于益貧式增長的影響已逐漸引起一些國內外學者的高度重視,忽略通貨膨脹的不公平性會造成益貧式增長估算的嚴重偏誤[11-14]。
1.2 中國農村經濟增長的減貧效果
反貧困進步是評價發展中經濟整體表現的一個廣為接受的衡量標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成功地處理好了穩定、改革與發展之間的關系,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推動下,走出了一條獨特的反貧困道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減貧成就[15]。在30多年的時間里,中國使7億多人口擺脫了貧困,是世界上唯一提前完成聯合國將貧困人口減半千年發展目標的國家。始自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土地相對平均分配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農村益貧增長的重要開端。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產生的效應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了貧困的快速減少。按照RAVALLION的測算,農村貧困發生率從1980年的75.70%迅速下降到1985年的22.67%,貧困率下降比例約占到1980—2001年貧困率下降總比例的84%[16]。廣大農村人口在改革開放的初始階段普遍平等地受益于經濟增長。增長模式關乎不公平演化,80年代中期開始,農村改革的農業收入效應減弱,進一步的收入增長取決于非農收入的增加,非農收入的分配并不公平,不斷上升的不公平減緩了反貧困進程。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是農村貧困減少的困難時期,一些年份的貧困率有所回升,農村地區呈現貧困上升的信號。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重新恢復減貧速度,90年代后期又有所放緩,農村反貧困進步表現出階段性不均衡特點。相應地,農村貧困的空間分布也從相對集中的生態模式逐漸轉變為邊緣化、分散化的社會經濟模式[17-19]。進一步的減貧面臨著多重不利因素的影響。為確保經濟增長的益貧性,需要在宏觀上保持經濟的穩定,經濟衰退和通貨膨脹會對更低收入人口帶來更大的沖擊[20]。研究結果表明,1988—1989年的通貨膨脹對于農村貧困具有負效應[16,21]。為了充分理解農村經濟增長的益貧性,3個因素需要被檢驗: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和價格變化,它們之間如何相互作用于農村益貧式增長。本文基于Shapley貧困變動分解方法,嘗試性將價格變化因素加入到PPGI、GIC和PEGR 3種益貧式增長度量指數中,分析農村經濟增長的益貧性質。
2 分析框架
2.1 3維Shapley貧困變動分解
貧困指數一般表述為:

(1)
公式(1)表示貧困水平取決于3個因素:平均收入u,收入分配狀況L(p)和反映生計水平的貧困線z。
假定貧困線保持不變,貧困變動ΔP可分解為經濟增長效應ΔG和收入分配效應ΔI[22-24]。
貧困總變動:ΔP=P1-P0=P(u1,L1,z)- p(u0,L0,z)
(2)
經濟增長效應:ΔG=P-P0=P(u1,L0,z)- p(u0,L0,z)
(3)
收入分配效應:ΔI=p1-p=p(u1,L1,z)- P(u1,L0,z)
(4)
公式(3)表示收入分配在最初配置水平上保持不變,平均收入變化產生的邊際效應;而公式(4)則表示平均收入保持在末期水平上不變,收入分配產生的邊際效應。然而,如果其他條件不變,基期和末期互換,也能進行同樣的分解。如何配置效果更佳,缺乏支持。于是,對稱理論提出將基期和末期的分解結果進行算術平均,以避免誤設誤差[25-28]。

(5)

(6)
公式(5)和(6)可以理解為2維的Shapley分解,分別用來測度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對于貧困變動的邊際貢獻。由于該方法具有穩健性和分解完全性等優點。因此,在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收入分配—貧困變動之間的動態關系分析中廣泛地加以運用[29-35]。
上述2維的貧困變動分解,是假定貧困線z沒有發生變化。實際上,由于價格因素的變化和生活費用成本的上升,外生選擇的貧困線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這樣,需要引入第3個因素:“貧困線”因素。GüNTHE等[12]亦將此因素稱為“相對價格變化”因素。通過隱含著通貨膨脹率的貧困線解釋價格變化對貧困變動的影響。嚴格建立在合作博弈理論基礎之上的Shapley分解原理,可用于進一步構建貧困變動的分解框架。Shapley分解將每一個因素的邊際貢獻平均分配給所有可能的組合。當平均收入、收入分配和貧困線3個變量投入于Shapley貧困變動分解程序中,始自于末位的6種可能組合方式對應于6種可能向下的路徑(圖1),可得平均收入(u)、收入分配(L)和貧困線(z)對貧困變動影響的分解值。
(7)
(8)
(9)
于是,ΔP=ΔP(u)+ΔP(L)+ΔP(z)
(10)
通過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和價格變化的Shapley分解,充分描述貧困變動特征。

圖1 Shapley貧困變動分解
2.2 考慮價格因素的益貧增長指數(PPGI)
為估算經濟增長的益貧性,本文嘗試將價格因素引入KAKWANI-PERNIA的PPGI中。假定存在一個正的增長率Δg%,則總貧困彈性可以定義為:
(11)
η=ηu+ηL+ηz
(12)
公式(12)中,貧困的經濟增長彈性ηu總為負,意味著當收入分配和價格水平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增長必然減少貧困;貧困的收入分配彈性ηL可為正、負或零,當ηL為負時,收入分布朝有利于低收入者的方向變化,貧困明確減少,增長是益貧的;貧困的價格彈性ηz同樣可為正、負或零,當ηz為正時,價格變化損害低收入者利益,對于貧困減少產生負面效應,增長并不益貧。由此,可得益貧增長指數:

(13)
若ηL<0、ηz<0,φ>1,增長絕對益貧;若0<φ<1,即使ηL>0、ηz>0,增長仍然減少貧困;若φ<0,增長會極大地損害低收入者,導致貧困上升。
2.3 剔除通貨膨脹的增長發生曲線(GIC)
RAVALLION等[5]提出了增長發生曲線(GIC),通過計算收入分配中各百分位的平均收入增長率,用于判斷益貧式增長狀況。GIC定義為:
(14)
gt(p)表示從t-1到t期第p百分位平均收入y的增長率。對于所有的百分位p,如果gt(p)>0,貧困減少,增長弱絕對意義益貧;如果gt(p)>0,且gt(p)為遞減函數,則增長相對意義益貧。
公式(14)反映的是名義GIC,在實證分析中,運用的是實際的特定百分位平均收入增長率。實際GIC通常計算為:
(15)
從t-1到t期第p百分位平均收入增長率的相對價格變化通過CPI予以調整,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剔除通貨膨脹對全體社會成員實際收入水平的影響。但這種消脹方法意味著收入分配中存在著無差異通貨膨脹率,即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受到相同的通貨膨脹率影響。事實上,由于不同收入人群的消費模式和消費特征不同,物價上漲本身也具有結構性差異,采用統一的CPI進行調整,會低估通貨膨脹對于低收入者的不利影響,不能恰當評價低收入者經濟增長的受益程度。更為精確的方法是采用特定百分位消費價格指數(Percentile-specific Consumer Price Indices,PCPI)計算特定百分位平均收入增長率[12-14,36]。
(16)
其中,pcpit(p)為第p百分位的特定通貨膨脹率。在益貧式增長測度中,考慮通貨膨脹的異質性,避免益貧式增長估算的偏誤。
2.4 符合單調性公理的減貧等值增長率(PEGR)
KAKWANI等在PPGI和GIC的基礎上,提出了減貧等值增長率(PEGR),PEGR的內在邏輯是:如果經濟增長進程中,相對不公平沒有發生任何改變,那么,經濟增長將帶來同比例的貧困減少,經濟增長與貧困減少之間存在著單調關系[6]。PEGR表達為:
γ*=φγ
(17)
φ為益貧式增長指數,γ為平均收入增長率,通過平均收入增長率γ對益貧增長指數φ進行調整。提高PEGR不僅需要快速的經濟增長,還需要提高低收入者的增長受益比例。當且僅當γ*>γ,經濟增長益貧。
3 模型和數據說明
本文的貧困狀況測度基于Lorenz曲線,沿用VILLASENOR和ARNOLD的廣義二次項(General Quadratic,GQ)模型[37]。
Lorenz曲線方程:L=L(P;π),其中,P是累積人口百分比,π是待估參數向量。該曲線描述人口累積百分比P和收入累積百分比L之間的函數關系,用以反映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分配差距狀況。
GQ模型:L(1-L)=a(P2-L)+bL(P-1) +c(P-L)
(18)


(19)
其中,z為貧困線,yi為低收入個體i的收入,q為低收入人口數,n為總人口數,α為社會貧困厭惡系數。當α取值為0,1和2時,相應得到貧困率(H)、貧困距(PG)和平方貧困距(SPG)3個分解指數,α取值越大,對低收入與非低收入人群之間、及低收入人群之間的收入分配公平性越敏感,反映越清晰,對更低收入人群的關注程度也越強。標準化的FGT指數無疑更適合于益貧式增長判斷。
以收入作為福利水平的度量指標。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農村居民收入分組數據,1990年為12等份,其余年份均為20等份。通過收入分組數據,得到相應各年的Lorenz曲線點,即P和L的一組數值,根據這一組數值,用OLS法回歸估計出參數a、b和c的值,參數經過檢驗后,可計算出FGT指數值。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特定百分位消費價格指數(PCPI)的計算采用人均純收入5等份分組的生活消費支出數據,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國家統計局從2003年起公布5等份分組統計數據。由于數據的局限,GIC僅檢驗2002—2009年的變動狀況。
4 農村貧困變動的三因素分解
本文采用2條貧困線,一條是國定貧困線,1990年為300元;另一條是1天1美元國際貧困標準線,1990年折算為475元,2009年為1194元,與我國的低收入標準線極為接近。表1列出了2條貧困線的FGT指數。
1990—2009年農村貧困總體下降,不同貧困線的貧困變動不一致,貧困線越高,減貧效果越明顯。按照1天1美元貧困標準(表1),H指數從1990年的34.35%持續下降到2009年的7.31%,下降趨勢明顯;PG指數也相應地從9.59%下降到4.07%。在FGT的3個指數中,隨著α取值的增大,貧困下降速度趨緩,2000年以來,國定貧困線的PG、SPG指數反呈上升趨勢,低收入人口貧困程度加深。2009年即便采用國定貧困線,貧困指數仍在上升,低收入人口數量表現出剛性的穩定。

表1 各年份貧困狀況
對農村貧困變動進行3維的Shapley分解,解釋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和價格變化對于貧困變動的影響。表2分解結果中的增長因素總為負,表明經濟增長促進減貧。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增長的減貧效應減弱。按照國定貧困線,1990—1995年間經濟增長使得H指數下降25.14%,2005—2009年間僅能下降3.54%。當賦予低收入人口更大的權重,經濟增長的減貧作用趨弱,按照1天1美元貧困標準,2005—2009年間經濟增長使H、PG和SPG指數分別下降6.39%、2.43%和1.29%,經濟增長對最低收入人群的減貧作用有限。分配因素總為正,收入分配發生了不利于低收入人群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經濟增長的減貧效應。雖然沒有證據表明不公平的負面效應隨著時間推移而遞增,但自2000年以來最低收入人群分配效應的不利影響愈加突出。當考察價格變化對貧困變動的影響時,可以發現,價格因素總是為正,大部分時期價格效應占優于分配效應。與預期相一致:1990—1995年間價格因素的貧困變動負效應顯著,此間1994—1995年的通貨膨脹給低收入人群帶來了極為不利的影響,較大程度地抵消經濟增長的減貧效果;在物價相對較為穩定的2000—2005年間,價格因素的貧困變動效應也較小,價格變化影響減貧進程。

表2 貧困變動的增長、分配和價格因素分解
5 農村益貧式增長評估
為分析中國農村各個不同時期經濟增長的益貧程度,參照KAKWANI和PERNIA的判斷標準,對益貧增長指數(φ)設立一套評價標準。
如果φ<0,增長不利于減貧;0<φ<0.30,增長弱益貧;0.30≤φ<0.60,增長中度益貧;0.60≤φ <1,增長較高程度益貧;φ≥1,增長高度益貧。
評估1990—2009年中國農村增長的益貧程度。表3結果顯示:(1)1990—1995年2條貧困線3個貧困指數的φ值表現一致,增長弱益貧。其間,1993—1995年是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最快的一個時期,經濟增長具有積極的減貧效應,但通貨膨脹損害低收入人群,顯著抵消經濟增長的減貧效果;初始不公平也影響著低收入人群的經濟增長受益性。(2)1995—2000年2條貧困線的φ值出現差異。按照國定貧困線,H、PG指數增長弱益貧,但SPG指數沒有益貧性。然而,按照1天1美元貧困標準,H、PG指數增長表現出中度益貧。雖然,這一時期的農村貧困減少較前一個時期緩慢,但增長益貧性相對提高,這一發現具有重要意義,驗證了益貧指數φ與貧困減少之間不存在單調關系。增長益貧性提高主要歸因于價格貧困彈性較前一個時期明顯下降。(3)2000—2005年2條貧困線的φ值差異性顯著。按照國定貧困線,H指數達到中度益貧,但PG、SPG指數益貧性顯示為負值,貧困發生率仍敏感于平均收入的增長,但最低收入人群沒有從平均收入的增長中相應受益,甚至是受損的。按照1天1美元貧困標準,H、PG和SPG指數顯示出較高的益貧程度,意味著提高貧困標準有助于改善益貧程度。(4)2005—2009年2條貧困線的φ值分化明顯。按照國定貧困線,FGT指數均為負值,較低的貧困線沒有益貧意義,需要提高貧困標準,我國從2008年起正式采用低收入標準作為扶貧工作標準。按照1天1美元貧困標準,H指數的φ值上升到0.75,較高程度益貧,然而,PG、SPG指數的益貧性迅速下降,SPG指數甚至轉變為負值,這一時期快速的農村經濟增長由于新一輪物價水平的持續上漲而非常不利于最低收入人群。
為進一步分析通貨膨脹的異質性,運用增長發生曲線(GIC),結合特定百分位消費價格指數(PCPI),觀測各百分位平均收入增長率的變動軌跡,判斷增長的益貧狀況。根據五等份組農村居民消費支出構成,低收入人群和非低收入人群食品消費支出比重有所不同。以2002年為基年,將農村CPI分為“食品”和“其他”2類,食品價格上漲幅度明顯高于其他商品。將PCPI簡化計算為:

表3 貧困變動的增長、分配和價格彈性與益貧增長指數
PCPI=ω食品(p)×CPI食品(p)+ω其他(p) ×CPI其他(p)
(20)
其中,ω食品(p)、ω其他(p)分別為第p百分位的“食品”和“其他”消費支出比重。表4結果顯示,從低收入百分位到高收入百分位PCPI略有下降。
圖2中,2002—2009年對于所有的百分位p,gt(p)>0,農村貧困減少,增長弱絕對意義益貧。最低收入百分位gt(p) 在沒有考慮通貨膨脹的情況下,gt為11.08%,最低收入百分位gt(p)為8.95%;通過CPI調整后,gt下降為7.74%,最低收入百分位gt(p)為5.65%,益貧程度下降。通過PCPI調整后,GIC繼續下移,比較經過PCPI調整與CPI調整后的2條GIC,可以發現,收入百分位越低,曲線之間差距越大,表明通貨膨脹對更低收入人群往往更加不利,特別是2007年以來糧價和食品價格推動的物價上漲,由于低收入人群有著更高的恩格爾系數,實際購買力下降幅度超過高收入人群,從而使得低收入人群益貧程度更進一步下降。研究結果同時也揭示了通貨膨脹是益貧式增長測度中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通貨膨脹存在異質性,可通過PCPI對益貧判斷偏差進行修正。 從相對意義考量農村益貧式增長(表5),4個時期的實際收入增長率γ在上升,經濟實現快速增長,但增長產出并沒有相應實現貧困的快速減少。γ*<γ,增長進程中,由于價格因素的變化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上升,低收入人群沒有同比例受益于經濟增長,農村經濟增長不具有相對意義益貧。 表4 農村各收入戶PCPI 3維Shapley貧困變動分解是動態福利測度的重要工具,通過這一分析工具將通貨膨脹的異質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納入農村益貧式增長判斷中。 與預期相一致:價格變化和收入分配影響減貧進程,大部分研究時期價格效應占優于分配效應,通貨膨脹和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不利于低收入人群,較大程度地抵消了經濟增長的減貧效果。 圖2 2002—2009年農村GIC 表5 農村減貧等值增長率 考察各個不同時期農村經濟增長的益貧程度,研究結果發現,1990—1995年,經濟增長具有積極的減貧效應,但初始不公平以及此間1994—1995年的通貨膨脹影響著低收入人群的增長受益程度,這一點與RAVALLION和CHEN的研究結論相一致[16]。1995—2000年,農村貧困減少較為緩慢,但增長益貧程度相對提高,這一發現具有重要意義,驗證了益貧指數與貧困減少之間不存在單調關系。益貧程度提高主要歸因于價格貧困彈性的明顯下降。2000—2005年,較高貧困標準表現出較高的益貧程度,而低貧困標準則顯示最低收入人群沒有從平均收入的增長中相應受益,甚至是增長受損。2005—2009年,這一時期快速的農村經濟增長由于新一輪物價水平的持續上漲而不利于最低收入人群。總體而言,農村增長弱絕對意義益貧,不具有相對意義益貧。研究結果同時也揭示了通貨膨脹的異質性是益貧式增長測度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實際應用中,可通過PCPI對益貧判斷偏差進行修正。進一步的研究可根據各個不同地區價格水平和消費水平的差異驗證這一結論。 [1]KLASEN S. In Search of the Holly Grail: How to Achieve Pro-poor Growth [C]// B TUNGODDEN, N STERN. Annual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Europe.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2003. [2]DOLLAR D,KRAAY A. Growth is Good for the Poor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2(7):195-225. [3]KAKWANI E,PERNIA E M. What is Pro-poor Growth [J].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2000,18(1):1-16. [4]EASTWOOD R,LIPTON M. Pro-poor Growth and Pro-growth Poverty Reduction: Meaning,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J].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2000,18(2):22-58. [5]RAVALLION M,CHEN S. Measuring Pro-poor Growth [J]. Economics Letters,2003(78):93-99. [6]KAKWANI N,SON H H. Poverty Equivalent Growth Rate [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2008,54(4):643-655. [7]EASTERLY W, FISCHER S. Inflation and the Poor [R].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00:2335. [8]BLANK R, BLINDER A. Macroeconomics,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overty [C]// S DANZIGER,D WEINBERG, In Fighting Poverty: What works and what does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180-208. [9]DATT G, RAVALLION M. Why Have Some Indian States Done Better Than Others at Reducing Rural Poverty [R].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1996:1594. [10]LI H,ZOU H. Inflation,Growth,and Income Distribution: A Cross-country Study [J].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02(3):85-101. [11]KOLENIKOV S,SHORROCKS A. A Decomposition Analysis of Regional Poverty in Russia [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5,9(1):25-46. [12]GüNTHER I,GRIMM M. Measuring Pro-poor Growth When Relative Prices Shift[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7(82):245-256. [13]SON H H,KAKWANI N.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Price Changes on Poverty [J]. Econ Inequal,2009(7):395-410. [14]張克中,馮俊誠. 通貨膨脹、不公平與親貧困增長——來自中國的實證研究[J]. 管理世界,2010(5):27-33. [15]汪三貴. 中國特色反貧困之路與政策取向[J]. 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0(4):17-21. [16]RAVALLION M, CHEN S. China’s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7(82):1-42. [17]RISKIN C. Chinese Rural Poverty: Marginalized or Dispersed [J]. China’s Reforms: Structural and Welfare Aspects, 1994, 84(2): 281-284. [18]都陽,蔡昉. 中國農村貧困性質的變化與扶貧戰略調整[J]. 中國農村觀察,2005(5):2-9. [19]岳希明,李實,王萍萍. 透視中國農村貧困[M]. 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7. [20]SANGUI W. Overcoming Poverty through Development—A review and assessment of the experiences of large scale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J]. China Economist,2009:104-118. [21]YAO 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over 20 Years of Reform [J].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2000,48(3):447-474. [22]KAKWANI N,SUBBARAO K. Rural Poverty and its Alleviation in India [J].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1990,25(13):A2-A16. [23]JAIN L,TENDULKAR S. Role of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in the Observed Change of the Headcount Ratio Measure of Poverty for Rural and Urban Population of India 1970-71 to 1983 [J]. Journal of Indian Schoo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1):165-205. [24]DATT G,RAVALLION M. Growth and Redistribution Components of Changes in Poverty Measure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2(38):275-295. [25]SHORROCKS A F. Decomposition Procedures for Distributional Analysis: A Unified Framework Based on the Shapley Value [R]. University of Essex and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1999. [26]林伯強. 中國的經濟增長、貧困減少與政策選擇[J]. 經濟研究,2003(12):15-25. [27]萬廣華,張茵. 收入增長與不平等對我國貧困的影響[J]. 經濟研究,2006(6):112-123. [28]萬廣華,張藕香. 貧困按要素分解:方法與例證[J]. 經濟學(季刊),2008(3):997-1011. [29]KAKWANI N,PRAKASH B,SON H H. Growth, Inequality, and Poverty: An Introduction [J].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2000,18(2):1-21. [30]魏勇,俞文華. 中國轉軌時期居民收入差距、貧困與增長問題的研究[J]. 經濟科學,2004(1):5-16. [31]王雨林,黃祖輝. 影響轉型期中國農村貧困變動率指標的因素的分解研究[J]. 中國人口科學,2005(1):50-57. [32]胡兵,胡寶娣,賴景生. 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對農村貧困變動的影響[J]. 財經研究,2005(8):89-99. [33]陳立中,張建華. 經濟增長、收入分配與減貧進程間的動態聯系[J]. 中國人口科學,2007(1):53-59. [34]張全紅,張建華. 中國的經濟增長、收入不公平與貧困變動:1981—2001——基于城鄉統一框架的分析[J]. 經濟科學,2007(4):15-24. [35]羅楚亮. 經濟增長、收入差距與農村貧困[J]. 經濟研究,2012(2):15-27. [36]張全紅. 糧價上漲、通貨膨脹與城市貧困——基于兩種價格指數的對比分析[J]. 統計研究,2008(9):11-15. [37]VILLASENOR J,ARNOLD B. Elliptical Lorenz Curves [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89,40(2):327-338. [38]FOSTER J,GREER J,THORBECKE E. A Class of Decomposable Poverty Measures [J]. Econometrica,1984,52(3):761-766. Prices Change,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Rural Pro-poor Growth XIE Dong-mei (CollegeofEconomics,FujianAgricultureandForestryUniversity,Fuzhou,Fujian350002,China) Based on the three-dimensional Shapley poverty variance decomposition method, the effects of economical growth,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rice changes on rural poverty changes were analyzed. By introducing the price factors into the pro-poor growth index, the pro-poorness of rural growth was measured. And by using the growth curve, and combining with the percentile-specific consumer price indices, the changes in the average income growth rate of each percentile were observed. Then, on this basis, the poverty reduction equivalent growth rate was used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pro-poorness of China’s rural growth from 1990 to 2009.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rural growth was weekly pro-poor in absolute sense,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rices shift affected the process of poverty reduction,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inflation wa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judgment of pro-poor growth. Shapley decomposition; pro-poor growth; inflation; income distribution 2016-08-19 謝東梅(1968-),女,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農村社會保障. E-mail:xiedongmei@fafu.edu.cn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11BGL070);福建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2012Z008) 10.16006/j.cnki.twnt.2016.05.005 F124.7 A 1637-5617(2016)05-0023-09
6 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