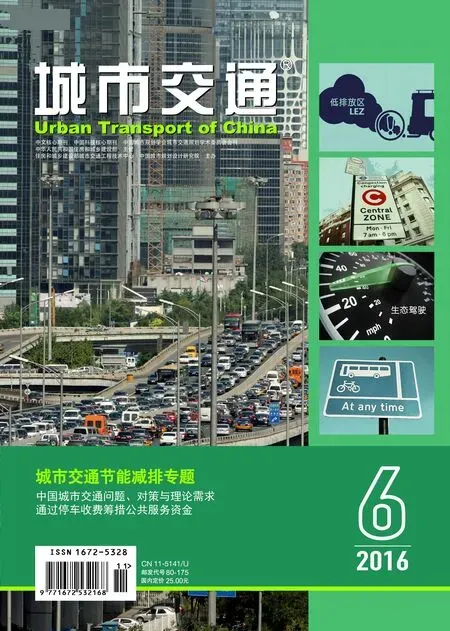適于中國城市的TOD規劃理論研究
王有為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北京100045)
適于中國城市的TOD規劃理論研究
王有為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北京100045)
TOD規劃理論在中國得到廣泛應用,有效指導了城市交通樞紐地區的開發建設,但在實際應用過程中對其理解還存在誤區。首先對TOD的概念、規劃原則、分類與典型模式進行解讀。重點分析美國TOD規劃理論產生的歷史背景,以及中美城市在發展階段、人口密度、土地所有制、公共交通投資體制、文化背景的差異性。由此得出美國的TOD規劃理論并不能完全適用于中國城市。最后,基于TOD規劃理論中的核心原則與中國城市發展現實,提出適于中國特征的TOD規劃模式。
TOD;規劃理論;典型模式;土地開發;交通樞紐
以公共交通為導向的(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TOD)規劃理論形成于1980—1990年。美國建筑師彼得·卡爾索普(Peter Calthorpe)于1993年在《下一代美國大都市地區:生態、社區和美國之夢》(The Next American Metropolis∶Ecology,Community and the American Dream)中,首次明確提出TOD的定義、類型、要素、系統和導則。隨后,TOD規劃理論傳播至世界各地,在歐洲和亞洲人口密度比較高的城市受到熱烈追捧。然而,世界各地的TOD社區規劃實踐千差萬別。近年來,中國幾乎所有城市軌道交通車站周邊地區的開發都以TOD規劃理論為指導,但沒有一個軌道交通車站周邊地區按照標準的TOD模型進行建設。原因既有具體實施層面的可行性問題,也有對TOD規劃理論存在不同認識的問題,以及標準的TOD模型是否適用于中國城市實際情況的問題。
1 TOD規劃理論的內涵
1.1 TOD的概念
TOD規劃理論是在城市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的,人們對TOD的理解和認識仍然在不斷完善。卡爾索普將TOD定義為:半徑為1/4英里(約400m),以公共交通車站和中心商業區為核心的土地混合利用社區。其設計、構造和土地的混合使用強調步行導向的環境并強化公共交通的使用。TOD將居住、零售、辦公、公共空間和公共設施等結合在適于步行的范圍內,從而使居民和雇員在不排斥使用私人小汽車的同時能夠方便地使用公共交通、自行車和步行等多種交通方式[1]。
比較典型的還有伯尼克(M ichael Bernick)和賽維羅(Robert Cervero)的定義,認為TOD是一個布局緊湊、功能混合的社區,以一個公共交通車站為社區中心,通過合理的設計鼓勵人們較少使用私人小汽車,更多乘坐公共交通。這樣的一個社區以公共交通車站為中心向外延伸約1/4英里,相當于步行至車站5min的距離。位于社區中心的是公共交通車站及環繞在其周圍的公共設施和公共空間,其中公共交通車站充當與周圍其他區域聯系的樞紐,而公共設施則成為本區域最重要的核心,公共空間則呈現為用于人們聚集、慶典以及承載特殊事件的現代版的古希臘廣場[2]。
另外,美國一些州級政府機構對其轄區內的TOD開發也有自己的定義。例如加州交通局將TOD定義為:適中或更高密度的土地利用,將居住、就業、商業混合布置在一個大型的公共交通車站周圍適于步行的范圍內,鼓勵步行交通同時不排斥私人小汽車交通。馬里蘭州交通局將TOD定義為:相對較高的發展密度,包括居住、就業、商業以及公共設施等功能混合于一個大型的公共汽車站或軌道交通車站周圍適于步行的范圍之內,偏重于步行和自行車交通的設計原則,同時允許私人小汽車交通[2]。猶他州在進行Wasatch Front地區規劃時將TOD定義為:將就業、居住和日常生活設施集中在公共交通車站周圍,在地區公共交通系統的關鍵節點創建高密度和功能混合的用地布局模式,并進行面向步行的設計。TOD使人們減少使用私人小汽車,更多選擇步行、自行車和公共交通出行,在家和公共交通車站的步行范圍之內可以方便使用各種服務設施[3]。
以上各種定義雖然表述不同,但核心的理念一致,即TOD指圍繞公共交通車站,在步行距離范圍之內進行高密度的混合用地開發,并進行面向步行和公共空間的設計,但并不排斥私人小汽車的使用。美國各州政府從實際操作角度出發的定義比專家學者的定義更加寬泛。
中國很多城市雖然在結合軌道交通車站或公共汽車站進行TOD開發建設,但各城市對于TOD的定義及核心內涵缺乏自己的見解,均在沿用美國學者和政府對TOD的定義。有學者曾經提出美國學者對TOD的定義并不適用于中國的實際情況,認為TOD在中國應該定義為:從城市規劃和城市交通規劃一體化的角度,實現交通與土地利用的高度整合。具體來說,是在骨干公共交通線路沿線和公共交通車站易于步行的范圍內進行適度的高強度土地開發,強調居住、辦公、商業、公共空間等用地的混合使用設計,使其與公共交通設施形成有效整合的一體化社區,從而引導城市空間有序增長,控制城市無序蔓延[4]。這一定義重點強調在城市宏觀層面公共交通與土地利用的結合,與美國學者提出的TOD概念有較大出入,并未被中國學術界廣泛接受。
1.2 TOD規劃原則
TOD的規劃原則與TOD的定義一樣,處于不斷發展的過程中。1993年卡爾索普提出了7項TOD規劃原則:
1)在區域規劃層面組織緊湊、有公共交通系統支撐的城鎮模式;
2)在公共交通車站周圍適于步行的范圍內布置商業、居住、就業崗位和公共設施;
3)創造適于步行的道路網絡,營造適于行人心理感受的街道空間,在各個目的地之間提供便捷、直接的聯系通道;
4)提供多種價格、密度的住宅類型;
5)保護生態敏感區、濱水區以及高質量的開敞空間;
6)使公共空間成為人們活動的中心,并且為建筑所占據而不是停車場;
7)鼓勵在已有發展區域內的公共交通線路周邊進行新建和改建[1]。
1997年,賽維羅和考克曼(Kockelman)提出了關于TOD的3D原則:
1)密度(Density),高密度開發可以縮短出行距離,更加適合步行和自行車出行,也更加適合公共交通出行。由此,公共交通客流量得到提高,人均車公里數減少。
2)多樣性(Diversity),土地利用的多樣性具有多重目的,如為居民提供便捷的日常生活服務、減少私人小汽車出行、增加地區活力等。
3)合理的設計(Design),通過合理的設計保證在相對高密度的發展條件下為不同的人群提供多層次的選擇[2]。
以上原則是美國學者基于美國城市發展的實際情況做出的結論,其中部分原則并不適用于中國城市發展的實際情況。對此,有學者提出了適于中國的TOD規劃5D原則[5]:
1)級差密度(Density Differential),用相對密度代替絕對密度,距離公共交通車站越近開發密度越高,但不同區位車站的周邊地區開發密度不同。
2)港島式區劃(Dockized District),通過步行系統與服務設施的一體化設計,將TOD的影響半徑擴展至400m之外。
3)豪華設計(Deluxe Design),重點強調TOD社區的高標準建設和人性化設計。設計不僅限于環境方面,還應包括站臺、出入口、各接駁交通方式的時刻表、車輛、車站設備等方面。
4)多樣選擇(Diverse Destination),在城市和區域層面將居住與就業進行平衡,使TOD社區的居民可以方便地到達城市的各類服務中心。
5)漲價歸公(Distributed Dividends),從財務平衡角度出發,將由于公共交通建設帶來的車站周邊土地升值部分由政府收回。
這些原則僅僅是個別學者的提法,并沒有得到學術界和各級城市政府的認可,也沒有實際案例進行驗證。這5項原則本身也有許多值得商榷之處,多樣選擇和漲價歸公的實際可操作性難度極大。
1.3 TOD分類與典型模式
卡爾索普將TOD社區分成兩類:一類是城市型TOD,位于區域性的重軌、輕軌或BRT車站,其商業強度和就業密度很高,居住密度在中等以上,多個城市型TOD串聯起來,形成城市發展軸;另一類是鄰里型TOD,以位于交通支線的公共交通車站為中心,乘公共汽車到城市軌道交通或BRT車站不超過10m in,其規模和密度比城市型TOD小,更加偏重居住功能。卡爾索普設想的理想TOD規劃模式見圖1。
這種TOD的分類方法和理想布局模式,自卡爾索普提出后得到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和城市政府廣泛認可。但這種TOD分類和布局模式明顯是根據美國實際情況提出的,并不一定適合其他國家和地區。實際上,世界各地包括美國在內也難以找到完全按照標準模式建設的TOD社區。
另外,即便是在這一理想TOD模式中,私人小汽車仍然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規劃交通性主干路從TOD社區通過,為其提供便捷的私人小汽車交通服務。同時,為了方便私人小汽車的使用,卡爾索普不得不將理想的TOD模式設計成半圓型,可見私人小汽車在美國人心中有著牢不可破的地位。
分析理想的TOD規劃模式,其內部各個地塊之間的聯系雖然很便捷,但與周邊次級區域的聯系不便,與相鄰TOD社區如何聯系不明確。其路網形態整體來看比較封閉,與周邊地區路網銜接以及與既有城市路網協調均比較困難。因此,該模式僅適用于城市外圍孤立公共交通車站周邊地區的開發,不適用于整條骨干公共交通線路沿線整體開發,也不適用于在城市建成區內進行TOD改造。

圖1 典型TOD社區規劃模式Fig.1 Typicalmodelof TOD community planning
TOD理論積極推行用地功能混合,但在其理想模式中,各類用地是相互分開的,沒有混合用地。各類用地僅僅是在TOD社區范圍內進行混合配置,沒有考慮各類功能在豎向上進行混合布置。
2 美國TOD理論產生的歷史背景
2.1 城市無序蔓延
20世紀60年代,私人小汽車已經發展成為美國居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由于老城區存在人口密集、交通擁堵、環境污染嚴重等城市病,大多數美國人向往田園式的郊區生活。私人小汽車極大地擴展了出行距離,使人們在郊區生活在市區工作的愿望成為可能。由此,人們開始逃離城市中心到郊區生活。美國大多數城市經歷了以郊區蔓延為主要模式的大規模空間擴展過程。此舉導致城市人口郊區化,土地利用密度降低,城市建設密度趨向分散化。由此帶來的城市中心地區衰落、社區紐帶斷裂以及能源和環境等方面的一系列問題日益受到關注。
20世紀90年代初,基于對郊區蔓延的深刻反思,美國逐漸興起了新的城市設計運動——新傳統主義規劃(New-Traditional Planning),后來演變為新城市主義(New Urbanism)。作為新城市主義倡導者之一的卡爾索爾普所提出的TOD策略逐漸被學術界認同,并在美國的一些城市得到推廣應用。
大多數美國人已經習慣了以私人小汽車為導向的城市蔓延發展。為了使人們能夠接受TOD社區,猶他州在為前瓦沙奇(Wasatch Front)地區編制TOD規劃導則時,首先強調以下五項原則:
1)TOD社區不排斥私人小汽車,住在TOD社區人們同樣可以駕車出行;
2)TOD社區與既有的低密度社區可以和諧相處;
3)TOD社區內同樣有大量獨立住宅供人們選擇;
4)TOD社區描述的土地混合使用只是在不同的地塊布置不同的功能;
5)TOD社區建設是一個長遠的地區發展策略,隨著地區的經濟增長逐步改變[3]。
由此可見,盡管TOD規劃理論在美國學術界得到一致認可,但讓民眾接受TOD社區還十分困難。TOD社區的目的是減少私人小汽車的使用、改變低密度蔓延的城市形態,但在美國實踐過程中不得不考慮如何與私人小汽車和諧共處,盡可能在不影響私人小汽車使用的前提下發展TOD社區,以便得到美國民眾支持。
2.2 公共交通復興
20世紀早期,美國也曾有過短暫的城市公共交通發展期。紐約、芝加哥等大城市紛紛建設地鐵、輕軌、有軌電車等公共交通設施。但隨著私人小汽車的普及和城市郊區化的發展,公共交通出行比例逐漸下降,部分公共交通線路在被石油和汽車公司收購后取消。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城市空心化非常嚴重,城市中心區衰退,城市經濟活力和競爭力下降,引起地方政府和專家學者的高度重視。
從城市和區域的總體發展考慮,美國各地政府都希望恢復城市中心的活力,1954年美國《住房法》修正案的出臺為城市中心區改造提供了資金支持。20世紀70年代后美國又掀起一波城市中心區復興運動。
城市中心區建筑密度高、人口密度大,只能依靠公共交通解決居民出行問題。于是,華盛頓、洛杉磯、波特蘭等大城市又開始大規模建設公共交通,紐約、芝加哥等城市也開始更新改造老舊的公共交通系統。美國的公共交通系統在大城市中心區開始復興并逐漸向郊區延伸。大城市公共交通的復興,特別是軌道交通系統的建設為TOD社區開發提供了必要的支撐條件。
3 中美城市差異性
3.1 城市發展階段不同
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中期是美國城鎮化快速發展時期,到20世紀60年代,美國城鎮化率已經超過70%,進入城鎮化后期。美國的城鎮化與機動化基本同時進行,到20世紀70年代,美國私人小汽車千人擁有量已經超過400輛,基本上達到每戶一輛的水平。私人小汽車的高機動性和公路系統大規模建設為城市低密度蔓延提供了必要支撐。美國TOD規劃理論的提出和實踐是在美國城鎮化和機動化基本完成后才開始。由于城市人口增長緩慢,城市空間結構已經成型,人們已經習慣以私人小汽車引導的低密度蔓延式城市形態,TOD社區在美國發展非常艱難。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資料,中國2015年城鎮化水平為56.1%,這里面還包含約2億的農民工,戶籍人口的城鎮化水平僅為40%左右[6]。中國當前正處于城鎮化快速發展的中期,未來20年內還將有四五億人口由農村進入城市。中國的機動化水平當前也處于快速發展階段,機動化水平最高的北京,私人小汽車千人擁有量也僅為250輛左右,人們對私人小汽車的依賴性并不強。中國城市還處于快速擴張階段,城市空間結構尚未定型,私人小汽車普及率還不太高,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車交通仍然是大多數城市的主要交通方式。將TOD規劃理論引入中國城市發展過程中、實現公共交通與土地利用緊密結合,對中國當前城市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3.2 城市人口密度不同
美國國土面積約930萬km2,適于居住的面積約760萬km2,而總人口僅約為3.1億人。美國是一個地廣人稀的國家,人口分布也比較分散,人口超過100萬人的城市僅有約10個,大多數美國人生活在中小城市。除了少數大城市的中心區外,美國城市人口的密度也非常低。例如,俄亥俄州最大城市克利夫蘭市,1980年人口約175萬人,而建成區面積達1 680 km2,人均建設用地面積接近1 000m2,幾乎是中國城市人均建設用地面積的10倍。
中國國土面積雖然有960萬km2,但適于居住的面積僅約為470萬km2,而總人口卻有約13.5億人。2015年,中國城市轄區人口超過1 000萬人的有12個,城市轄區人口超過100萬人的約有140個[7]。中國城市人口數量雖然大,但建成區面積并不大,例如長沙2008年城市人口約330萬人,而建成區面積僅為320 km2。
TOD規劃理論在美國主要解決城市低密度蔓延的問題。根據卡爾索普的研究,TOD社區內住宅區的凈人口密度最低為每公頃25戶,適宜的人口密度為每公頃45戶,內部要包含獨棟住宅、聯排住宅和公寓樓等多種形式[1]。美國猶他州前瓦沙奇地區、俄勒岡州波特蘭地區的實踐,僅僅是依托軌道交通車站,將一些原本閑置的土地和少量獨棟住宅新建或改造成多層建筑。
中國城市人口密度普遍較高,即便是近年新開發的城市郊區和一些小城市,也都以幾十層的高層住宅和辦公樓為主,很少有低密度的別墅區。因此,TOD社區在中國并不需要擔心城市低密度蔓延問題。近年來,中國城市擴張速度也很快,呈現高密度蔓延的態勢,特別是在一些軌道交通車站周圍,由于開發密度過高,經常造成軌道交通過于擁擠、服務水平和舒適度下降,并存在一定的安全隱患。
3.3 土地所有制不同
美國的土地以私有制為基礎,大部分適宜人類活動的土地掌握在私人手中,只有國家公園、自然山體、水體、濕地、荒漠等禁止開發或不適宜開發的土地由聯邦政府所有。對于私有土地,美國政府并不能進行太多限制,而且要保證所有的私有土地具有相同的開發權利。美國各地政府均有自己的《區劃法》,主要目的是保證某個地塊的開發不影響其周邊地塊的開發和使用。在城市郊區,建設獨棟住宅對周邊地區影響最小,同時能夠滿足當時美國人對獨棟住宅的需求,因此,美國城市的低密度蔓延得以順利推進。
中國的土地以公有制為基礎,分為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只有國家所有的土地才允許進行開發建設和交易,集體所有土地只能在村集體內部進行交易,而且不能進行大規模開發建設。由于政府對土地嚴格把控,中國的城市擴張速度、城市空間結構與建設形態完全掌控在政府手中。盡管中國很多大城市的房價非常高,但在城市的近郊區甚至建成區內還經常存在大量農業用地,這在土地私有制國家是無法想象的。正是由于政府對土地的嚴格掌控,使中國城市不可能出現低密度蔓延的現象,城市的每一步發展只能按照政府的規劃有序推進。
3.4 公共交通投資體制不同
TOD社區建設的一個重要前提是要有大運量公共交通作為支撐。公共交通設施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并且很難從后期運營中收回。因此,公共交通設施的建設多數情況下只能由政府承擔,公共交通運營可以由公司組織,但需要政府給予大量的財政補貼。大多數美國人很少乘坐公共汽車,對公共交通系統的關注比較少,大規模的公共交通設施建設很難通過市議會(City Council)的批準。另外,公共交通設施建設帶來的土地升值只能被土地所有者占有,公共交通投資方無法從中獲益。因此,在美國只有少數大城市建有比較發達的公共交通系統,多數城市難以得到公共交通設施建設和運營資金。
中國城市人口密度大,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車交通是大多數市民主要的出行方式。當前,中國正處在城鎮化和機動化的快速發展階段,城市交通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公共交通也越來越受到各地城市政府的重視,在中國大力發展公共交通很容易得到政府和民眾的支持。截至2016年2月,中國獲得國家批準建設軌道交通的城市已達到40個,未來3年至少有10個以上城市將獲得批準[8]。2016年將有15個城市新開通運營軌道交通線路,到2016年底,中國軌道交通運營線路累計將達到120條,運營總里程將達到3 600 km,運營車站將達到2 500座[9]。大規模的軌道交通建設為TOD社區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3.5 文化背景不同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自由是其立國之本,在郊區有一套獨立住宅、駕駛私人小汽車往返于各地已經成為美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人對大城市并沒有特別的情感,也不向往大城市生活。只有窮人和新移民才會選擇在市中心居住,富人和中產階層基本上都居住在城市郊區。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城市一直是國家統治的中心,大城市的各種機會遠多于小城市和農村,人們對大城市充滿向往。另外,中國的大多數公共服務設施都集中在城市中心。正是人們對城市中心的特別偏好,才使得中國城市一直保持緊湊發展,沒有出現低密度蔓延。
4 TOD規劃理論在中美城市實踐中的差異性
4.1 高密度開發
提高城市開發密度、保護郊區自然環境、阻止城市低密度蔓延,是美國發展TOD社區的主要目的。由于中美國情差異,TOD在中國的主要目的是引導城市有序發展,使公共交通設施建設與土地開發利用相協調。
中國的TOD社區不宜過分強調提高公共交通車站附近的開發密度,而應該強調土地開發密度與公共交通設施的運輸能力相協調。由于地鐵、輕軌、有軌電車等公共交通方式的運輸能力差別較大,圍繞不同類型公共交通車站的土地開發密度應該具有一定差異。各類用地的開發規模需要結合公共交通分擔比例和公共交通設施運輸能力進行測算確定。
4.2 土地利用多樣性
保持TOD社區用地的多樣性是提升社區活力、減少跨區出行、降低高峰時段雙向交通需求不均衡性的重要手段。雖然土地混合利用在中國城市比較普遍,但是在城市新發展地區缺少具有城市服務職能的公共設施,公共服務類用地以服務社區內部為主。當前,中國城市的混合土地利用模式雖然能夠減少跨區出行的交通需求,但無益于降低高峰時段交通需求的不均衡性。例如,北京市軌道交通13號線、4號線、5號線等,早高峰時段進入市中心方向客流量超過軌道交通的運輸能力,而離開市中心方向卻客流稀少,造成公共交通運輸能力極大浪費。為了減少這種浪費,均衡雙向交通,中國TOD社區進行用地多樣性布局時應該考慮在軌道交通車站附近引入具有城市服務職能的公共服務設施。
另外,不同于美國TOD社區只強調在平面上進行土地混合利用,中國TOD社區在強調平面土地混合利用的同時,還應強調垂直方向的功能混合。
4.3 良好的空間設計
面向公共空間及步行和自行車交通系統的人性化設計是提升公共設施服務水平和社區活力的重要手段。這一點中國城市的大型社區和公共交通車站設計得都不夠理想,存在步行和自行車交通系統環境差、步行設施不連續等問題。中國TOD社區規劃需要著重強調連續的步行系統設計和公共空間美化。
美國的TOD社區人口密度較低,人們的交通規則意識比較強,人與車的干擾并不嚴重。因此,美國的TOD社區并沒有強調步行系統的連續性。中國人口密度高,人與車之間的相互干擾極大地降低了步行舒適性和步行速度,并有潛在的危險。因此,中國TOD社區在規劃時應該將人與車在空間上分離,努力構建連續的步行網絡。
4.4 適宜的TOD社區規模
美國TOD社區規模以適宜的步行距離為限,一般半徑為400~800m。從以人為本的角度出發,500m左右的距離是比較合適的步行尺度,并且這一規模經過了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實踐檢驗。
當前,中國城市中自行車出行量比較大,存在大量自行車換乘大運量公共交通的需求。有學者建議以自行車10m in的出行距離來劃定中國TOD社區的范圍。根據卡爾索普的測算,半徑400m的TOD社區內只要居住密度達到8 100人·km-2,就可以維持一個大運量公共交通系統的運行[1]。中國一般城市社區的人口密度遠超過8 100人·km-2,即使以400m半徑來劃定TOD社區規模,如果不對土地開發強度進行合理調控,其產生的客流量仍然有可能超出大運量公共交通設施的運輸能力。如果以自行車10m in的出行距離作為TOD社區的范圍,社區半徑可能達到2 km以上,以當前中國大城市一般社區的開發強度,這一范圍產生的出行量將遠遠超過大運量公共交通系統的運輸能力。因此,中國TOD社區的規模不宜太大,距離大運量公共交通車站500m左右、步行10min以內是適宜的規模。
4.5 TOD社區分類
中國城市人口密度普遍比較高,沒有出現類似美國城市低密度蔓延的情況。中國當前的TOD社區建設都是圍繞地鐵、輕軌等大運量公共交通車站進行的城市型TOD開發,鄰里型TOD對中國城市建設沒有過多指導意義。因此,美國TOD社區的分類方式也不適用于中國。
近年來,中國高速鐵路和城際鐵路大力發展,圍繞高鐵車站和城際鐵路車站進行高強度開發成為中國學術界和地方政府的共識。大量的高鐵和城際鐵路車站周邊也采用TOD社區模式進行開發,但是其開發強度、用地功能和影響范圍都遠遠超出一般的城市TOD社區。這種圍繞高鐵車站和城際鐵路車站進行的TOD開發可以定義為區域型TOD社區,是中國特有的TOD社區類型。
5 基于中國特征的TOD模式構建
5.1 TOD定義
TOD是一個以大運量公共交通車站為中心,以400~800m為半徑,土地混合利用且開發強度與交通運輸能力相適應的城市混合功能區。在這樣一個城市功能區內,通過合理的設計鼓勵人們較少使用私人小汽車,更多選擇步行和公共交通。位于功能區中心的是公共交通車站及環繞在其周圍的公共設施和公共空間,公共交通車站充當與城市其他區域聯系的樞紐,而公共設施則成為本區域最重要的核心。
5.2 TOD規劃原則
1)開發密度適宜。
以公共交通設施的運輸能力為基礎,使土地開發產生的出行量與交通設施的運輸能力相協調。一方面要避免土地開發密度過低,造成土地資源和公共交通資源浪費;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土地開發密度過高,造成公共交通服務水平降低和吸引力下降。
2)土地混合使用。
TOD社區的土地使用應該包括三種主要功能:居住,為社區服務的公共設施,為城市服務的公共設施。居住是TOD社區的基本功能,宜占TOD社區總用地的30%~60%;配套建設為社區服務的公共設施可以大幅減少居民跨區出行,并提升社區的活力,這類用地宜占TOD社區總用地的20%~30%;為城市服務的公共設施可以進一步提升社區活力,并可以均衡城市交通流的潮汐現象、提高交通設施的利用效率,這類用地宜占TOD社區總用地的10%~40%。
在用地布局上,為城市服務的公共設施應盡量靠近大運量公共交通車站,為社區服務的公共設施可以與居住用地進行適度混合。
3)步行設計連續。
面向公共空間的人性化設計是TOD社區的靈魂。中國城市人口密度大,行人與機動車相互干擾問題嚴重,這極大降低了步行的吸引力,從而降低公共交通設施的吸引力,使人們更多選擇私人小汽車出行。以公共交通車站為中心,構建連續的步行系統是中國TOD社區最基本的人性化設計要求。
5.3 TOD分類與典型模式
根據所在位置不同,中國的TOD可以分為區域型TOD和城市型TOD兩類。區域型TOD是指以高速鐵路、城際鐵路車站為中心,以商業、商務功能為主導的高強度混合開發區域。這類TOD常常最終形成城市副中心或城市商務中心區。城市型TOD是指以地鐵、輕軌等大運量公共交通車站為中心,以居住、公共服務、商業功能為主導的混合開發區域。
中國城市的道路網結構以方格網為主,TOD社區作為城市的一個功能區,其道路網絡需要與城市道路有機銜接。因此,中國TOD社區的道路網絡適宜采用方格網布局,不宜采用放射狀或自由式的路網結構。
大運量公共交通引導的土地開發模式與骨干道路網絡引導的土地開發模式不同,理論上講,軌道交通應該與城市骨干道路網分離。理想的城市型TOD社區典型模式如圖2所示,以軌道交通車站為中心,采用圈層式的用地布局,利用連續的步行網絡將各個地塊與軌道交通車站聯系。道路網絡采用方格網的形式,方便與城市路網銜接。骨干道路與城市軌道交通線路分離,軌道交通線路有獨立的走廊。這種模式要求軌道交通線路建設、道路網建設和土地開發同步實施,適用于城市外圍的新開發地區。
中國城市中的大多數區域,早期都是依托骨干道路開發建設起來的,軌道交通只能以骨干道路為依托進行建設。因此,在對城市已開發區域進行TOD改造時,其理想的布局模式需要進行適當修改。適用于建成區改造的城市型TOD社區典型模式如圖3所示,軌道交通線路位于城市主干路下,城市用地以軌道交通車站為中心,采用圈層式布局,利用連續的步行網絡將各個地塊與軌道交通車站聯系。
區域型TOD社區典型模式如圖4所示,以鐵路車站為中心,半徑200m以內主要布置為鐵路旅客服務的交通和商業設施;半徑200~800m范圍布置商業、辦公、娛樂等公共服務設施;半徑800~2 000m范圍布置居住和產業用地。在大中城市,鐵路車站通常有軌道交通接駁,鐵路車站與軌道交通車站共同作用形成TOD走廊。

圖2 適于中國城市的理想城市型TOD社區模式Fig.2 Idealized TOD communitymodelsuitable for Chinese cities

圖3 適于中國城市建成區的城市型TOD社區典型模式Fig.3 Typicalmodelof TOD community suitable forurban built-up areas in China

圖4 區域型TOD社區典型模式Fig.4 Typicalmodelof regional TOD community
6 結語
中國城市與美國城市存在顯著差別,不能用美國的TOD規劃理論直接指導中國城市的實踐。學習TOD規劃理論重點在于理解其思想和理念,在實際應用中需要與城市具體情況相結合。本文通過對TOD規劃理論內涵、產生背景及中美城市差異的分析,指出當前中國在TOD規劃理論應用中存在的問題,并結合城市特點提出適用于中國城市的TOD定義、規劃原則、分類及典型模式。TOD規劃理論的核心思想在于將大運量公共交通建設與周邊土地利用緊密結合,提升交通效率與社區活力,降低居民對私人小汽車的依賴,實現綠色、可持續發展。其具體的規劃指標、規模、設計布局等需要根據交通技術發展、生活理念變化和城市具體情況調整完善。
[1]Peter Calthorpe.The NextAmerican Metropolis∶Ecology,Community and the American Dream[M].New York∶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1993.
[2]馬強.近年來北美關于“TOD”的研究進展[J].國外城市規劃,2003(5):45-50.Ma Qiang.Recent Studies on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in North America[J].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2003(5)∶45-50.
[3]Envision Utah.Wasatch Front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Guidelines[R].Utah∶Envision Utah,2002.
[4]趙晶.適合中國城市的TOD規劃方法研究[D].北京:清華大學,2008.Zhao Jing.Study on TOD Planning Methodology for Chinese Cities[D].Beijing∶Tsinghua University,2008.
[5]張明,劉菁.適合中國城市特征的TOD規劃設計原則[J].城市規劃學刊,2007(1):91-96.Zhang M ing,Liu Jing.The Chinese Edition of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J].Urban Planning Forum,2007(1)∶91-96.
[6]徐紹史,胡祖才.國家新型城鎮化報告2015[M].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2016.
[7]國家統計局城市社會經濟調查司.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15[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6.
[8]艾澤瑞.中國大陸申報軌道交通建設獲批城市一覽表[EB/OL].2016[2016-11-24].http//tieba.baidu.com/p/4342188756.
[9]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交通運輸部.交通基礎設施重大工程建設三年行動計劃(發改基礎[2016]730號)[R/OL].2016[2016-11-24].http∶//www.waizi.org.cn/law/13298.htm l.
Suitability of TOD Planning Theory for Chinese Cities
Wang Youwei
(China Center for Urban Development,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Beijing 100045,China)
∶The extensive application of the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TOD)planning theory in China haseffectively guided the developmentand construction of urban areasw ith intermodaland intramodal terminals.However,themisunderstanding of the TOD principles still exists in practice.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TOD's concept,planning principles,classification and typicalmodels.Through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background of the TOD theory in the U.S.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U.S.cities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stage,population density,land ownership system,public transportation investment system and culturalbackground,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TOD planning theory adopted in the U.S.isnotcompletely suitable for cities in China.Finally,the paper proposes a TOD planning model that tailors to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core principles of TOD planning theory and the developmentof Chinese cities.
∶TOD;planning theory;typicalmodel;land development;intermodal terminals
1672-5328(2016)06-0040-09
U491.1+2
A DOI∶10.13813/j.cn11-5141/u.2016.0607
2014-04-09
王有為(1975—),男,北京人,碩士,高級城市規劃師,主要研究方向:城市規劃與交通規劃。E-mail∶jty_wangyw@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