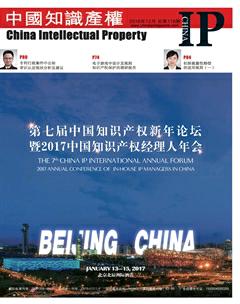專利行政案件中公知常識認定現狀分析及建議
卓銳
關鍵詞 舉證不積極 依賴技術調查官 公知常識認定規則
公知常識是專利授權確權行政案件中的一個常用概念。某項技術在其所屬領域基于申請日(或優先權日)前的該領域技術發展水平及該領域技術人員的知識水平,已經被廣泛地接受并應用,以至于該技術在該領域已經到達了“公知化”的程度,就應被認定為公知常識。但我國現行的專利法律法規中,沒有對公知常識這一概念進行明確的定義。同時,對公知常識的判斷主體,即所屬領域的技術人員這一擬制的“人”的認知水平和判斷能力,并沒有一個客觀明晰的界定。因此,在專利行政案件審判中,當事人、專利復審委員會以及法院對公知常識的問題認定時常產生分歧。為此,本文以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成立以來的專利行政案件中涉及公知常識認定的64份判決書為研究對象,力圖通過分析專利行政案件中有關公知常識認定的情況,找出各方分歧的原因,并有針對性地提出相關建議。
一、專利法律法規中有關公知常識的規定
我國《專利法》和《專利法實施細則》中均沒有公知常識的相關規定,有關公知常識的規定均體現在《專利審查指南》中。
《專利審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八章4.10.2.2規定,審查員在審查意見通知書中引用的本領域的公知常識應當是確鑿的,如果申請人對審查員引用的公知常識提出異議,審查員應當能夠說明理由或提供相應的證據予以證明。
《專利審查指南》第四部分第二章3.3規定,對駁回決定和前置審查意見中主張的公知常識補充相應的技術詞典、技術手冊、教科書等所屬技術領域中的公知常識性證據。
《專利審查指南》第四部分第二章4.1規定,在合議審查中,合議組可以引入所屬技術領域的公知常識,或者補充相應的技術詞典、技術手冊、教科書等所屬技術領域的公知常識性證據。
《專利審查指南》第四部分第二章4.3.3規定,主張某技術手段是本領域公知常識的當事人,對其主張承擔舉證責任。該當事人未能舉證證明或者未能充分說明該技術手段是本領域公知常識,并且對方當事人不予認可的,合議組對該技術手段是本領域公知常識的主張不予支持。當事人可以通過教科書或者技術詞典、技術手冊等工具書記載的技術內容來證明某項技術手段是本領域的公知常識。
二、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專利行政判決中涉及公知常識認定的情況
第一,根據認定公知常識的方式不同,通過對上述64份判決的分析,可以將其分為以下三類。
1.以審查證據的方式認定某項技術是否為公知常識的情形
在上述64份判決中,涉及證據審查的判決共有9份。這其中,有5份判決中涉及的公知常識性證據為教科書或專業辭典。另外4份涉及證據審查的判決情況如下:
(2014)京知行初字第179號判決根據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生效判決中的相關認定,確定相關技術特征為所屬領域公知常識。
(2015)京知行初字第275號判決根據當事人提交的涉案專利申請日前已經實施的自攻螺釘用螺紋的國家標準,認定涉案專利權利要求2的附加技術特征屬于機械領域的公知常識。
(2014)京知行初字第78號判決和(2015)京知行初字第3495號判決經過分析3GPP標準文檔的形成過程及其法律性質,均認定上述標準文檔不能單獨證明某一技術特征為通信領域的公知常識。
2.以說理的方式認定某項技術是否為公知常識的情形
在上述64份判決中,有36份判決對公知常識的認定進行了說理,其中大部分是相對較為簡單的說理,如(2014)京知行初字第110號判決認定:“對比文件2中公開了非金屬絕緣層可為塑料層,考慮到塑料材質可為透明或者半透明性質的材料,并可采用局部透明的方式,因此這屬于公知常識”。
在上述36份判決中,有4份判決對公知常識認定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說理,分別是涉及中醫藥領域的(2015)京知行初字第3438號判決、涉及通信電子領域的(2015)京知行初字第58號判決、(2015)京知行初字第3495號判決以及(2015)京知行初字第2227號判決。
3.一筆帶過的情形
上述64份判決中,有19份判決是以如“本專利權利要求X相對于對比文件結合本領域公知常識不具備《專利法》第二十二條第三款規定的創造性”之類的評述簡單帶過。
第二,從認定結果方面進行分類,在上述64份判決中,絕大多數判決均確認專利復審委員會對于公知常識的認定正確,僅有以下3份判決改變了專利復審委員會有關公知常識認定的結論:
(2015)京知行初字第591號判決認定在煙葉的存儲后期需要采取措施抑制醇化屬于本領域的公知常識,并撤銷了被訴決定。
(2015)京知行初字第2227號判決認定涉案專利相對于對比文件的區別技術特征2并非所屬領域公知常識,并撤銷了被訴決定。
(2015)京知行初字第3495號判決認定專利復審委員會在申請人已經提出異議的情況下,并未舉出公知常識性證據,亦未進行充分說理,在被訴決定中直接認定區別特征1、2均為本領域公知常識,屬于認定事實錯誤,并據此撤銷了被訴決定。
通過對上述64份判決的統計分析可見,在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目前的專利行政案件審理中,有關公知常識認定的問題存在以下幾個突出的特點:1.涉及公知常識性證據的判決很少,64份判決中僅有9份;2.進行詳細說理的很少,64份判決中僅有4份;3.與專利復審委員會認定不同的很少,64份判決中僅有3份。
三、審判實踐中進行公知常識認定時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通過對上述64份判決的分析,結合筆者的審判實踐,筆者認為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目前的專利行政案件審理中對公知常識進行認定時存在的問題及其產生的原因如下:
1.當事人舉證不積極
在進行公知常識認定時,當事人提交公知常識性證據以支持其主張無疑是一種理想的狀態。但目前審判實踐中這種理想狀態往往難以出現,當事人提交證據證明某項現有技術屬于公知常識的積極性很低。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有以下幾點:第一,專利行政案件中,有一些現有技術雖然沒有被收錄入教科書、技術手冊、技術詞典,但其的確已經在涉案專利申請日時被所屬領域技術人員廣泛接受和應用,已經成為公知常識,甚至有一些實際上屬于生活的常識。在此情況下,當事人提交公知常識性證據是有相當難度的。第二,某些技術領域有其獨有的特性,以通信領域為例,該領域的技術更新速度很快,許多新出現的技術迅速在行業中大量應用,很可能未等到該項技術被教科書、技術手冊、技術詞典收錄,該項現有技術已經被通信領域的技術人員廣泛接受并應用,進而成為本領域的公知常識。在此情況下,要求當事人舉出公知常識性證據顯然過于苛刻。第三,當事人往往將用以證明某項技術為所屬領域公知常識的證據局限于《專利審查指南》列舉的三種形式。但實際上,除了上述幾種公知常識性證據,當事人是可以提交其他的證據用以說明某項技術在某一時間節點上已經被所屬領域技術人員廣泛應用,已經達到“公知化”的程度。
2.法官過于依賴技術調查官
審判實踐中經常出現的情況是,審查員在被訴決定中未進行充分說理就將某一技術特征認定為所屬領域公知常識,法官對上述認定存有疑惑但無法形成內心的確信。面對這樣的困境,法官不可避免地對技術調查官的技術支持產生一定程度的依賴。
由于審理專利行政案件的法官并非所屬領域技術人員,加之在審判實踐中,判斷是否屬于公知常識的時間點往往早于案件審理之時,因此,要求法官在審理此類案件時準確地界定數年之前的所屬領域技術人員的認知水平和判斷能力具有相當的難度,而在生物、化學、醫藥、電子、通信等領域,相關技術問題造成的障礙更是法官在短時間內難以克服的。由此,法官對所涉案件技術事實的認知水平和判斷能力,尤其對某一技術特征是否已經為所屬領域技術人員公知這一問題的界定,相對于所屬領域技術人員尚存差距。
反觀專利復審委員會的審查員,其往往具有相關領域的碩士甚至博士學位,其從事的審查工作也往往與其專業背景相吻合。而且審查員在日常工作中每天會接觸大量相關領域的技術方案,這也使得審查員在技術問題的判斷上具備了豐富的經驗。因此,審查員對所涉案件技術事實的認知水平通常高于從事專利行政案件審判的法官。也正是因為法官與審查員對技術事實的認知水平存在相當差距,才會導致法官自覺不自覺地對技術調查官的技術支持產生依賴。
3.判決說理不充分
通過對上述64份判決的分析不難看出,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在專利行政案件審理過程中,對公知常識的認定存在說理不夠充分的問題。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對公知常識認定問題說理是否詳細充分與所涉的技術領域以及所涉技術本身存在一定關系,一些根據生活常識或基本科學知識即可判斷屬于公知常識的技術客觀上并不需要詳細說理。其次,審判實踐中,在當事人并未提交公知常識性證據,需要法院對某項技術是否屬于公知常識進行說理論證時,確實存在“越公知越難以說明”的情況。
四、有關公知常識認定問題的思考和建議
審判實踐中,公知常識的認定給法官帶來不小的困擾,當事人對此也爭議很大。針對審判實踐中的現狀,為有效解決前文所述的問題,筆者建議如下:
第一,在審判實踐中形成鼓勵當事人對公知常識進行舉證的導向
《專利審查指南》對公知常識性證據進行了列舉,即教科書、技術手冊、技術詞典三種形式。一般而言,如果某項技術已經被載入上述文獻,就可以認定該項技術屬于公知常識。此外,審判實踐中還有依據國家標準或者在先生效判決進行公知常識認定的先例。可見,除了上述文獻,當事人還可以提交其他形式的證據用以說明某項技術在某一時間節點上已經被所屬領域技術人員廣泛應用,達到“公知化”的程度。
證明某項技術為所屬領域的公知常識,最有力、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提供證據。一方面,證據能夠明確地顯示時間,從而有效地避免法官以案件審理時所屬領域的公知常識判斷涉案專利在其申請日時的創造性;另一方面,一方當事人提交證據,為另外一方或兩方當事人對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以及證明力等方面充分發表意見提供了機會,法院在充分聽取各方意見的基礎上作出裁判,不僅能使裁判更大程度地接近事實,更有利于增強裁判的說服力,使當事人信服。因此,鼓勵和引導當事人提交證據以證明其有關某項技術屬于公知常識的主張不失為一個有益的嘗試。而這種鼓勵和引導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判決中充分評述相關證據進而作出裁判,不僅讓當事人意識到提交證據的現實意義,也可以讓當事人對何種證明程度可以被法院采信形成合理的預期。
第二,結合涉案公知常識本身的技術特征及其所屬技術領域的特性有針對性地加強裁判文書說理
在審判實踐中,很多情況下對公知常識的認定只能通過說明理由的方式進行。但如何才算說理充分,必須結合公知常識本身的技術特征及其所屬技術領域的特性進行判斷。
1.對于諸如“相對于機動車道路,人行道路和非機動車道路均屬于慢行道路。”【參見(2015)京知行初字第61號判決】之類的“公知常識”,究其本質,其實際屬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2001年)第九條所指的當事人無需舉證證明的“眾所周知的事實”。對于此類“公知常識”,當事人無需舉證,法院也無需說理,徑行認定即可。
2.對于諸如“加強筋能夠提高構件的強度和剛度。”【參見(2014)京知行初字第46號判決】之類的“公知常識”,基于基本的科學知識即可判斷其在所屬領域已經屬于公知常識的,其也無需法官過多地說明理由。
3.對于其他當事人沒有舉證或者囿于所屬領域的特性難以舉證,且無法根據基本的科學知識直接判斷的“公知常識”,法官應當結合涉案專利申請日時所屬領域技術發展水平以及該領域技術人員對某一技術特征的接受和應用程度,在充分論理的基礎上進行認定。
第三,合理運用技術調查官制度,形成司法主導的公知常識認定規則
審查員有專業技術背景,其以中立裁判者的身份作出的審查決定理應得到法官足夠的尊重,而法官尋求技術調查官支持以厘清技術事實也是合理運用技術調查官制度的應有之義。但如果過分相信審查員的認定或過分依賴技術調查官的技術支持,在沒有形成足夠的內心確信的情況下作出判斷,不僅有損裁判的說服力,還會有讓渡司法審判權之虞。
公知常識的認定雖然必定要以技術事實的確定為基礎,但從技術事實的確定到達最終的法律認定有賴于法官運用法律知識和法律思維完成。可見,公知常識的認定歸根結底并非技術問題而是法律問題。而法官通過研習法律、審理案件所積累的法律知識、法律思維以及實務經驗使得法官在解決法律問題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這既是法官最擅長的工作,也是法官應當擔負的職責。因此,法官在公知常識認定的問題上理應更加自信,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具體而言,法官應該在尊重審查員中立專業判斷的基礎上,引導各方當事人對公知常識問題充分發表意見,合理運用技術調查官制度,讓技術調查官做好法官的“技術翻譯”。從而使法官能夠更客觀更充分地理解技術問題,厘清技術事實,夯實法律判斷的基礎,并最終作出有說服力的裁判。
此外,法官對于公知常識的認定標準應當嚴格掌握,不宜輕易認定某項技術為公知常識。筆者提出這一建議系基于以下理由:公知常識必定屬于現有技術,即便某一技術特征難以被證明是公知常識,但證明其為現有技術在很多情況下是可以通過充分的檢索實現的。法官嚴格掌握公知常識的認定標準,能有效地推動當事人或審查員更積極地進行現有技術的檢索,以多項現有技術相結合的方式評價涉案專利的創造性。這固然可能增加當事人與審查員的工作強度,但并不會對專利權人或者無效宣告請求人的權益造成任何損害,而且還能夠為涉案專利創造性的判斷提供更為客觀的依據,進而可以有效地防止“公知常識”被濫用,保障當事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