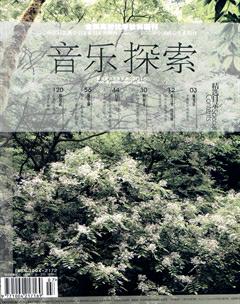三十余年來平湖派琵琶藝術研究述評
石洋
摘要:平湖派琵琶是我國著名的琵琶流派之一,為我國琵琶藝術的發(fā)展做出過重要貢獻,對近代中國琵琶藝術有著巨大影響。三十余年來,學界對平湖派的傳承與發(fā)展進行了較為深入、持續(xù)的研究,有力推動了琵琶藝術的發(fā)展。通過系統(tǒng)全面地回顧這些成果并加以綜合分析,厘清其研究脈絡,認真地反思研究中的不足與缺憾,將有助于深入探討平湖派這一傳統(tǒng)的民族音樂遺產(chǎn),促進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與發(fā)展。
關鍵詞:平湖派;琵琶;民族音樂
中圖分類號:J632.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2172(2016)03-0044-07
平湖派琵琶是我國著名的琵琶流派之一,興于浙江嘉興平湖,自李廷森起,歷經(jīng)李煌、李繩墉、李南棠代代相傳。1895年,平湖派第五代傳人李芳園輯錄出版了《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譜》,標志著平湖派琵琶藝術的形成,傳承百余年來對我國琵琶藝術產(chǎn)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起至今30余年來,對平湖派琵琶的研究開始逐漸豐富,但總體上講,個例性研究多,群體性研究偏少,且缺乏綜合分析,研究的內容、深度尚有很大的空間。
一、發(fā)展概況
本文以1982~2015年期間中國期刊網(wǎng)中關于平湖派琵琶藝術研究的學術論文和碩博論文為依據(jù),描述30年來平湖派琵琶的基本研究狀況,以期能較全面地呈現(xiàn)其研究概貌。
對平湖派琵琶藝術的研究大體分兩個階段。1982年,廣州音樂學院殷惠麟教授與平湖派琵琶演奏家楊毓蓀先生合撰并發(fā)表了第一篇平湖派琵琶專題研究文論——《淺談平湖李芳園傳派琵琶藝術特點》,開啟了平湖派琵琶研究新的歷史篇章。但此后,1982~2000年的近20年間,以平湖派琵琶為專題的研究論文相當稀少。著作方面,1990年,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了任鴻翔整理的《平湖派琵琶曲13首》樂譜,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出版了楊毓蓀整理、編著的《平湖遺韻》。這是第一階段,即“興起一緩慢發(fā)展”階段。2000年之后,隨著我國文化事業(yè)的逐步繁榮,傳統(tǒng)文化受到重視,社會和學界對平湖派琵琶這一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上影響最大的五大琵琶流派之一的關注也逐步增強。2007年7月,平湖派琵琶成為浙江省第二批非遺項目。同年,首個平湖派琵琶傳承基地在平湖市百花小學成立。2008年6月,平湖派琵琶被收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保護名錄》。2013年11月,平湖市舉行首屆中國平湖派琵琶文化論壇,來自全國十幾位琵琶演奏家、理論專家聚首平湖,共商平湖派琵琶保護和傳承大計,同時還舉辦了建國以來第一場高水平、高層次的平湖派琵琶演奏會。2014年11月,平湖市和西安音樂學院共同舉辦了“平湖派第七代傳人楊少彝教授研討會”,緬懷楊先生并研討平湖派琵琶在西北大地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與之相適應的是,對平湖派的研究也逐漸豐富,研究成果不斷出現(xiàn),平湖派琵琶這一民族音樂的珍貴遺產(chǎn)煥發(fā)了生機。這是第二階段,即“豐富一快速發(fā)展”階段。
二、重點與特點
整體而言,三十余年來,對平湖派琵琶的研究,重點是傳承人物研究、傳統(tǒng)經(jīng)典曲目研究兩大方面。
(一)關于人物的研究
中國傳統(tǒng)琵琶藝術流派的傳承基本上是以“口傳心授”的形式、以師承的關系代代延續(xù),五大琵琶流派的發(fā)展歷程莫過如此,平湖派亦然。因此,在其百年來的傳承史上對該流派的傳承與發(fā)展都有突出貢獻的傳承人物,其影響力是毋庸置疑的,也成為了學界的研究重點。如第五代李芳園、第六代朱英、第七代楊少彝、第八代任鴻翔四人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對他們的研究有三個特點。
1.人物鮮明的時代代表性
李芳園是近代平湖派琵琶的奠基人,對中國琵琶藝術的影響極其深遠。他在總結、吸收前人優(yōu)秀傳統(tǒng)的基礎上,創(chuàng)新性地輯錄了《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譜》,是中國琵琶史上繼《華氏譜》后出版的第二部琵琶譜,對平湖派琵琶具有劃時代意義,極大地推動了平湖派的發(fā)展。錢鐵民認為:“李譜輯錄的大套明顯多于諸家各譜。而就其譜中曲類的編排,記譜的精細和指法標明的詳細程度,亦較之諸譜完整而系統(tǒng)。”它是江、浙、滬眾多琵琶名家共同勞動的結晶,是平湖琵琶與他地琵琶相互交融而成的新譜。殷惠麟則首次提出“李氏學派”的觀點,認為他確定了平湖派琵琶的指法變化、旋律、格調,從而形成了平湖派的藝術風格。
朱英是平湖派琵琶的標志性人物之一,吳慧娟稱之為“繼李芳園后平湖派的代表人物”,在平湖派的傳承中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開啟了琵琶在現(xiàn)代高等音樂專業(yè)教育中的先河,開創(chuàng)了平湖派傳承的新時代。姜寶海認為他“使李氏民間、文人非專業(yè)的琵琶傳教,步入了現(xiàn)代高等音樂專業(yè)教育”。朱平生認為他“把經(jīng)過重新校訂、規(guī)范記譜的平湖派琵琶的十三套大曲作為上海國立音樂院的琵琶教學用曲”,從而改變了傳統(tǒng)樂器教學中的“演詳于教,教詳于譜”狀況,開創(chuàng)了我國高等音樂教育琵琶教材的范本,為平湖派琵琶的推廣和傳承起到了積極且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20世紀初,在西方音樂對傳統(tǒng)音樂的沖擊下,朱英持開放和包容的音樂理念,對傳統(tǒng)音樂藝術傳承上的不足之處有清醒的認識。他強調:“既不能崇西也不能貶中,而是要學習西方音樂的優(yōu)點為我所用,來改良、發(fā)展我國的傳統(tǒng)音樂。”從而保持了平湖派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同時也促進了平湖派的發(fā)展。
作為平湖派嫡傳,楊少彝是建國后平湖派琵琶傳人中對平湖派傳承貢獻最大的代表人物之一,開啟了平湖派在三秦大地的傳播時代。但他從不固守于傳統(tǒng)琵琶藝術的“流派”與門戶之見,而是博采眾長,積極改革發(fā)展平湖派琵琶藝術。李寶杰認為楊少彝是西安音樂學院的琵琶表演學科的創(chuàng)始人,為學院的教學與人才培養(yǎng)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使平湖派琵琶藝術得到了新生。因此,王范地高度評價他“在挖掘整理平湖派琵琶藝術的過程中,楊少彝先生廣交名家同好、不拘門戶交流、攜譜奉訪學友、善于凝聚團隊力量等特征與平湖李氏學派琵琶藝術治學傳統(tǒng)的傳承關系,以及這一治學方式對提升民族音樂經(jīng)典作品品質與價值的重要意義”。
作為平湖派第八代的代表,任鴻翔處于我國改革開放后、文化藝術復興的嶄新時代,學術思想更加民主解放,創(chuàng)作激情更加蓬勃,這使得他能在充分吸收平湖派琵琶藝術精華的基礎上,勇于創(chuàng)新,賦予了平湖派琵琶新的生命力,創(chuàng)作出了一批如《渭水情》等極富地域特色的新時代琵琶作品。李武華曾強調,任先生用“死品活彈”進行調諧,使不能進行十二律轉調的琵琶既能自由轉調,又能按民間音律演奏,保持了民族傳統(tǒng),發(fā)展了平湖派的琵琶技法。鄭聰認為,任鴻翔把故鄉(xiāng)情懷與對平湖古韻的深刻理解完美結合創(chuàng)作出的《渭水情》充分體現(xiàn)了他扎實的音樂修養(yǎng)與理解力,使平湖的“幽”與秦韻的“烈”時空交融,極大地拓展了平湖派琵琶的新境界,使平湖派琵琶達到一個新的高度。endprint
2.注重人物的創(chuàng)新性
創(chuàng)新性是研究者對人物研究中的關注重點。創(chuàng)新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發(fā)展的動力,更是一個流派發(fā)展的內在因素,正是依靠著生生不息的創(chuàng)新,平湖派琵琶才能成為流傳百年而不絕的民族精華。
李芳園的創(chuàng)新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李氏譜》的編訂手法新,通過連綴等形式形成新曲子,如《塞上曲》,閆定文認為這種新方法的編創(chuàng)“給樂曲注入新的內涵,使樂曲沿著新的樂思衍變”。二是技法創(chuàng)新,錢鐵民認為李芳園一生總結、創(chuàng)新了許多新指法,較《華氏譜》的26種,其右手指法就多達58種。但不足之處也很明顯,沈浩初編著的《養(yǎng)正軒琵琶譜》序言中曾評論說:“《華氏譜》指法頗簡,《李氏譜》廣則廣矣,奈花指繁加,幾失廬山真面,指法雖較《華譜》有增,尚多模糊難解。”三是曲目增加的新標題,對這一創(chuàng)“新”,研究者的觀點頗有不同。贊同者如殷惠麟認為其用意在于“突出主題,使人對這首樂曲的主題思想更容易引起想象”,贊揚“這些小標題生動傳神,語言優(yōu)美,標新立異,起著畫龍點睛的作用”。反對者如莊永平認為:“因頌古非今,輕視俗樂,反而使我們不能更清楚、客觀地認識琵琶樂曲的發(fā)展,有時甚至會障礙樂曲可能的表達。”萬莉認為,王霖的《各領風騷數(shù)百年——中國四大琵琶流派簡述》中所言也是持反對態(tài)度,而錢鐵民的《李芳園的琵琶藝術》和韓淑德、張之年所著《中國琵琶近現(xiàn)代史資料(之三)》以及劉德海的《流派篇》則認為不應全盤否定。對此,筆者認為,吳蓉所持觀點“標題音樂會引導他們正確的體會音樂,使他們對音樂的把握更準確,從而有利于音樂的傳播和發(fā)展。但作品中小標題在某些作品中的安排并不合理,在具體的作品甚至出現(xiàn)不合適的標題導致前后意思并不是太連貫”是比較客觀、中肯的。
朱英的創(chuàng)新性則體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技法,廖輔叔強調朱英“在他發(fā)表作品的后面,每一首都定例有他自創(chuàng)的新指法說明,而且創(chuàng)造出半音的奏法”。其首創(chuàng)的運用“左手大指按托之法,突破了不用小指按音的禁區(qū)”,豐富了作品的表現(xiàn)力,使平湖派琵琶以技術高超、色彩華麗而著稱于世。朱平生認為這一變革使“左手五指并用,以便演奏復音、和聲,適應樂曲的日漸繁復,充分發(fā)揮五個手指的功能”,這是他在繼承和發(fā)展平湖派琵琶藝術中前進的一大步。二是創(chuàng)作,陳恭則認為他作為一個愛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對周圍事物的反映極快,政治嗅覺極高”,創(chuàng)作了一批緊跟時代步伐、反映社會現(xiàn)實的如《五卅紀念》《淞滬血戰(zhàn)》等現(xiàn)代曲目,在當時對民眾的激勵和社會影響很大。因此,廖輔叔評價他:“就其作品的內容而論,可以說通過民族音樂來反映現(xiàn)實生活而且具有積極的批判意義的,朱應該算是屈指可數(shù)的民族音樂家之一。”
楊少彝針對平湖派的創(chuàng)新則主要體現(xiàn)在演奏上,不拘門戶,廣泛吸收他派的演奏技藝,在演奏上強調氣、力的辯證思維,即“以意代氣、以氣代力、以力觸弦、力足音實、音實韻長”,反映了他倡導“意在指先、意至指隨、意實結合”的藝術內涵,反對矯揉造作、故弄玄虛、表現(xiàn)過分等傾向。
任鴻翔的創(chuàng)新性主要體現(xiàn)在他的平湖派美學理論的形成以及與之相應的創(chuàng)作上。任鴻翔的《平湖派琵琶藝術美學思想初探》從美學的角度對平湖派藝術風格進行深入探討,揭示了傳統(tǒng)音樂對美的追求是民族音樂發(fā)展的不懈動力。這篇文章奠定了任鴻翔從美學角度探討平湖派琵琶藝術的基石,此后,王平、李寶杰、李雄飛、姜寶海分別以此為基礎,以音樂美學為出發(fā)點研究了他的美學理論,并加以完善。王平認為:“(他)靠自己掌握的民間音樂素材,大膽汲取現(xiàn)代創(chuàng)作技法的經(jīng)驗,以及多年來對平湖派琵琶藝術美學意蘊的領會進行創(chuàng)作。”李雄飛則認為:“成功地把平湖派琵琶藝術善于表現(xiàn)含蓄隱秀、清遠流暢的風格與三秦民間音樂以及秦腔音樂中常被人忽略的那種纏綿委婉、細膩真摯的情調融合起來形成自己的創(chuàng)作特點和美學追求。”《渭水情》《柳絲》《雁》等特色鮮明的作品就是這一美學理論的實踐產(chǎn)物。
3.人物特色各異的藝術風格
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審美追求,每一個人物有每一個人物的藝術風格。吳釗、劉東生在《中國音樂史略》中評價:“平湖派琵琶藝術常常通過含而不漏、余音裊裊、含蓄隱秀的特點來展示音樂的魅力。”程午加在《關于江南琵琶流派之我見》中也指出平湖派琵琶“講究韻味和意境,講究樂曲的內容表達和音樂的表情處理”。這一觀點在平湖派琵琶四代傳人身上都體現(xiàn)到極致,但具體到個人卻又各具特色,研究者對此也有認真的分析。
錢鐵民認為李芳園的演奏風格講究描繪與刻畫,注重內在表達,使人感到意境深遠。“武有武的彈法,文有文的情趣”,文曲表現(xiàn)灑脫清幽、怡然自得,有余音繚繞之感,表現(xiàn)出典雅的意趣和幽深的境界,給人以美的感受;武曲則雄健豪宕、勢不可擋,或“大弦怒裂驚征人”或“音如落大山之瀑”。而朱英的音樂風格保持了平湖的含蓄、淡遠,強調意境與情感的表現(xiàn)的特點。他最為喜愛和擅長演奏的文曲《潯陽琵琶》充分體現(xiàn)了平湖派優(yōu)美、柔和、輕淡、細膩為主,韻味為重,聲調次之,只求淡遠、不求鏗鏘的藝術風格。程午加評價其“演奏注重文雅,其特點是喜歡加花,行腔華麗,講究尾音三轉彎,即每段尾音給人聽起來曲曲彎彎拖得很長”。朱英提出了演奏中應“文武合一”的新理念,其在《長恨曲》中同時使用了文板與武板,這就與大多琵琶古曲所慣有的非文即武的氣質有所不同。楊晨認為楊少彝的整體風格質樸清新、意韻深長,演奏抒情自然、灑脫自由,音樂細膩沉穩(wěn)略帶一絲的凝重。姜寶海則指出,楊少彝追求“幽雅高深、清素自然”的崇實風格,發(fā)揚了平湖派琵琶藝術的豐滿華麗、堅實淡遠的藝術特點。作為三秦大地的后人,由于地域、出身以及時代的巨大差異等情況,任鴻翔的演奏風格無疑受到了秦地悲涼、粗獷、纏綿的地域特色的熏陶,極具特色的表情、狀物,表現(xiàn)了他厚重的鄉(xiāng)土情懷。正如他談到自己的演奏風格與特色的形成時指出:“我在探索平湖派琵琶藝術中,從另一個角度感到正是這種‘文人氣質所表現(xiàn)的藝術風格,恰恰能揭示我們三秦大地風土人情的另一個重要方面——秦韻的委婉與細致,能揭示八百里秦川與粗獷豪放相蘊含的這種不為國人所熟悉的北方人的纏綿之情。”蔣傲霜在《任鴻翔琵琶作品探究》中認為:“他的音樂中融入了很多陜北音樂元素,把對故鄉(xiāng)深厚的情感,用他的音樂淋漓盡致的表現(xiàn)出來,他悟出了平湖派琵琶藝術的真諦,以及平湖派藝術中豐滿華麗、淡遠流暢、含蓄隱秀、典雅委婉的藝術風格。”endprint
(二)關于經(jīng)典曲目的研究
曲目是音樂流派傳承的唯一載體,研究流派經(jīng)典曲目才能準確地把握其演奏風格和藝術特色。《李氏譜》是平湖派琵琶的集大成者,目前的研究均以該譜為藍本,通過旋律比較研究、風格特點研究、技指法研究三種方式,對曲目的旋律結構、技指法、藝術效果進行分析。
閆定文認為,文曲中李氏譜的《塞上曲》是李芳園選擇了風格情趣相同、調式與結構一致的五首小曲,并沿用原曲《昭君怨》的思緒用小工調統(tǒng)一起來形成的。楊曉東通過對《塞上曲》平湖派、汪派、浦東派三種流派的對比研究,認為平湖派匯編了《塞上曲》,其指出:“自《李氏譜》開始,盡管以后各流派的演奏家們對《塞上曲》各有各的處理,但是段落的相對獨立性、曲式的基本結構、表達的基本意境和基本演奏手法卻始終保持了《李氏譜》確立的標準。”任鴻翔在《集真善美于一體的琵琶曲名作——平沙落雁》中認為,《平沙落雁》“一個最為鮮明的特點,是在含蓄優(yōu)美的曲調中,時而顯露出雁的鳴叫聲,似有似無,時隱時現(xiàn),有一種俯仰自得心游太虛的感覺”。而這正是平湖派含蓄雅致、余音裊裊的審美特點的表現(xiàn)。《平沙落雁》常見的有四個版本,即李芳園譜,王天健、何明威譯譜;吳夢飛傳譜,林石城整理;蔣風之演奏譜,鄺宇忠整理;楊大鈞演奏。這四個樂譜版本均傳承于李芳園譜。劉冰竹進行比較研究后,認為總體上此曲動靜結合、虛實交融,“有著中國古典詩詞中不可言傳只可意會的韻味,使得中國古典美學思想在這里熠熠生輝”。通過氣息與聲韻的研究,強調“琵琶作為中國傳統(tǒng)音樂中以單線條旋律發(fā)展為主的樂器,在演奏中最為離不開的便是‘氣韻兩字,這也是中國傳統(tǒng)音樂文化的精髓所在”。任海花具體分析比較了四個版本的不同,認為李芳園譜音樂風格樸實、意境深邃、節(jié)奏規(guī)整,演奏技法和音樂語言相對單一;吳夢飛傳譜的主要特點是運用了“三角馬蹄輪”的演奏方法;蔣風之演奏譜的風格特點是典雅、古樸,音樂語言含蓄,旋律有加花裝飾,且每段都有速度變化,用“摭+臨”的技法組合演奏第七段,較形象;楊大鈞演奏譜的音樂風格生動逼真。《潯陽琵琶》原稱《夕陽簫鼓》,亦稱《潯陽月夜》,在《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譜》中名為《潯陽琵琶》,是平湖派琵琶文曲的一首代表作,楊蔭瀏先生曾稱贊其是平湖派文曲的極高境界。楊毓蓀在《平湖遺韻》中稱之“其品色,格調,被譽為十三套之最”。孫麗偉認為:“《潯陽琵琶》在指法運用上的特色是左手的‘捺音和右手的‘蝴蝶雙飛‘掛線輪,其‘捺音,發(fā)音清晰,虛按中似有實彈。其演奏手法簡練、音樂線條樸素、意境高雅,具有古樸之風。”
《郁輪袍》《淮陰平楚》都是我國琵琶傳統(tǒng)武曲。《郁輪袍》有平湖派、汪派、浦東派等多種版本的傳譜,還有劉德海先生根據(jù)汪派《郁輪袍》新編的《霸王卸甲》等。李氏譜的《郁輪袍》注有“即《霸王卸甲》角音,唐王維作,李基鈺、南棠正”字樣。《淮陰平楚》,亦稱《十面》或《十面埋伏》,曲譜最早見于1818年華秋萍的《華氏譜》,其后各派琵琶譜集都載有該樂譜,但各個版本在分段與分段標目都有所不同。李氏譜《淮陰平楚》十八段,是其武曲的精品。平湖派《郁輪袍》流暢飄灑、豐滿華麗、一氣呵成。烏日娜認為:“《郁輪袍》結構完整、演奏指法豐富,運用了平湖派滿輪、馬蹄輪、絞雙弦、擬音等眾多的特色指法,風格鮮明,完美詮釋了平湖派豐滿華麗、字密音繁的演奏特色,極富感情色彩地表現(xiàn)了戰(zhàn)場中人物豐富細膩的情感活動,有極強的感染力。”而《淮陰平楚》的琵琶技法更加多樣,杜佳臻認為“此曲在音樂處理上,不是單純的比速度快、聲音響,而是注重精湛的指法技巧和深厚的內在修養(yǎng),追求一種‘以形寫神,神形具備的完美境界,講究抑揚頓挫,剛柔并濟的處理手法和特點,彈奏細膩,加花多,烘托一種大場景的效果,不僅具有宏大的氣勢,而且蘊含了深刻的意境”。
現(xiàn)代曲目中最有平湖派特點的當屬《渭水情》,以秦腔牌子曲《永壽庵》為素材,具有濃郁的關中地方風格,影響極大。該曲既傳承了平湖派琵琶藝術善于表現(xiàn)含蓄隱秀、清遠流暢的風格特征,又汲取了秦腔音樂中委婉纏綿、細膩感人的抒情特點。孔靜柳按樂曲的前后順序,從曲式結構、調式對比、旋律等方面詳細解讀了作品的演奏技藝,認為作品“保持了平湖派重視線性旋律的一貫特點,同時,為了適應現(xiàn)代生活的審美情趣味、心理期待,又做了適當加工、改造,對點的力度予以突出、強調,完成了技法層面的創(chuàng)新”。鄭聰認為,作品把西方音樂的復調、和聲等技法納入到琵琶演奏中,豐富了琵琶旋律單一的不足,把琵琶演奏藝術推向了一個新高峰。“水平之高、內涵之深、最受觀眾歡迎、達到雅俗共賞之境界者,《渭水情》為最”。
三、幾點反思
通過對三十余年來平湖派琵琶藝術研究的粗略回顧可以看出,研究成果對推動平湖派藝術的傳承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同時存在一些不足,有必要對之反思。
其一,研究內容的不平衡。主要體現(xiàn)在個例研究比較豐富,群體研究不足。平湖派的傳承歷經(jīng)一百多年,是平湖派傳人代代努力的結果,也是其不斷吸收其他流派優(yōu)點、不斷創(chuàng)新、不斷豐富傳承方法與形式的過程。從近年的研究成果看,多集中在李芳園等幾個關鍵人物和經(jīng)典曲目方面,且內容重復或相近,而對于整個平湖派的傳承史、創(chuàng)作特點、音樂理念、流派之間的交融情況等方面極少涉獵,由個例到整體的研究明顯不足。筆者認為,個例的研究有一定的代表性,但群體的研究才能從整體上反映一個流派的綜合性,特別是平湖派濃郁的文人氣息和尚雅的情調是整個流派的精神符號,必須將之置于中國傳統(tǒng)音樂發(fā)展的人文、社會、政治、經(jīng)濟環(huán)境中,離開這個基礎,對個例的研究就顯得單薄,不能從整體上把握平湖派的精髓。
其二,傳承與發(fā)展的路徑研究薄弱。學術研究的目的在于推動研究對象的發(fā)展,對平湖派的研究重點也應放在如何保存、發(fā)揚光大這一古老的文化上。湯曉風曾談到:“在被確立為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之前,平湖派琵琶在平湖當?shù)亟踅^跡,幾乎沒有老百姓知道在自己家鄉(xiāng)曾經(jīng)還有過這樣一支對近現(xiàn)代琵琶藝術產(chǎn)生過深遠影響的傳統(tǒng)流派。”雖然近年來平湖派琵琶已經(jīng)受到重視,如建立傳承基地、召開全國性論壇等,但在學術領域針對傳承、傳承的方式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卻顯然不足。楊少彝先生曾說,平湖派琵琶藝術要采取“古法之佳者守之,垂危者繼之,不佳者改之,不足者增之”的原則解決繼承與發(fā)展的問題,即通過借鑒與創(chuàng)新,使之獲得新生而傳承。筆者認為這應當是解決傳承與發(fā)展的根本方法。特別是在當今時代,琵琶的傳授在過分院校集約化情形下,流派之間的交融與滲透使得琵琶流派已無界可循,所謂的流派之分只是體現(xiàn)在譜面或版本的區(qū)別。所以,對平湖派琵琶如何守之、繼之、改之、增之的研究,即剔除糟粕,存留精華的傳承與發(fā)展的路徑研究急需加強。endprint
其三,平湖派研究的基礎人才不足。眾所周知,我國傳統(tǒng)音樂傳承長期以來基本上是依靠“口傳心授”的方式以“私家秘傳”的形式傳承,一直延續(xù)到20世紀初,伴隨著西方音樂教育模式的逐步興起而向專業(yè)化教育和大眾化普及才得以發(fā)展。但平湖派琵琶藝術的發(fā)展之路顯得較為艱難。究其原因,吳慧娟在《20世紀中國琵琶藝術發(fā)展探賾》中認為,平湖派的含而不露、余韻裊裊、含蓄隱秀的文人音樂在審美上的局限性,致使平湖派的曲目越來越少的在公開的場合被演奏,其傳承的方式越來越收攏是主因。的確,平湖派琵琶藝術根植于文人雅性的土壤之中,是典型的書齋音樂,與民間音樂的大眾性、娛樂性有較大差異,其以雅、儒為標榜的音樂理想,與時代變遷對音樂的需求格格不入,特別是建國后政治環(huán)境與社會情緒使平湖派更不能適應主流音樂,導致傳承的缺失與自身的沒落,使研究者也避而遠之,上世紀80年代之后才有所復興。即使如此,專注于平湖派專題研究的學者和文章也很少,沒有研究,就沒有發(fā)展,如何提高基礎研究人員的數(shù)量和質量,是平湖派研究的一個新課題。
其四,對平湖派發(fā)展史上與其他流派交融研究不足。奉山認為:“用中國音樂史學的觀點看問題,琵琶流派同宗同源出自一家,它是從傳統(tǒng)中誕生,也將成為傳統(tǒng)而新生。”追根尋源,琵琶各流派的根都同在中國民族文化、民族音樂這片沃土中,因此,對于平湖派而言自身也是在與各流派之間相互借鑒、相互交融的過程中產(chǎn)生與發(fā)展的。音樂家黃翔鵬指出,音律、調式、傳譜、演奏技法四方面是傳統(tǒng)流派的顯性特征,是有別于其他流派的判斷依據(jù)。要尊重流派的傳統(tǒng)淵源,就要從這四個方面研究平湖派與其他流派的交融,何時交融、如何交融、區(qū)別與提高的變化等等,只有認真研究平湖派與其他流派的交融情況,才有助于全面深入地了解平湖派的形成源泉、特色,清本正源。
傳統(tǒng)文化是一個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因此,對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與發(fā)展是守護精神家園的重要舉措。平湖派琵琶作為民族傳統(tǒng)音樂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其獨特的藝術風格與藝術魅力構成為我國傳統(tǒng)民族音樂的珍貴遺產(chǎn),我們必須將之傳承好、發(fā)展好。正如任鴻翔所說:“一個流派的形成,必有本派的優(yōu)秀演奏家和佳作流傳,并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征與烙印,在另一方面也應看到流派存在的不足和局限性甚至是保守性,只有研究了它的全部才會有鑒別地去吸收繼承。”因此,對平湖派琵琶的研究要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礎上,通過理論創(chuàng)新、研究方法創(chuàng)新、不斷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才是對這一珍貴遺產(chǎn)最好、最根本的傳承與發(fā)展。
責任編輯:李姝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