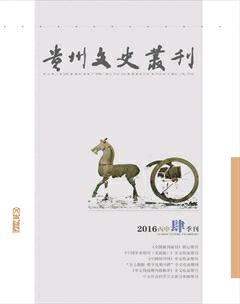清代貴州團練與地方政治
張習琴
摘 要:在清代全國團練興起的大背景下,結合貴州具體史事,分析了貴州團練興起的原因,介紹了貴州團練的名稱,規模及其經費來源,并通過地方基層制度保甲制和基層社會重要構成部分宗族與士紳在基層社會中的地位與影響,著重分析在社會大動亂時期保甲制的困境造成團練興起的必要性及宗族與士紳組織團練的原因。通過團練與官府的關系分析其在維護傳統政治格局和社會秩序的同時侵害官府利益和權威、剝蝕離心中央政權的二重性,從而揭示清代貴州團練與地方政治關系的演變。
關鍵詞:貴州團練 保甲 宗族 士紳 官府
中圖分類號:K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8705(2016)04-103-108
貴州團練因社會動亂而興起,亦因動亂結束而逐漸解體且退出歷史舞臺,其存在的時間雖然短暫,但對清代貴州歷史產生了重大影響,它好比一把雙刃劍,即彌補了正規軍的不足,維持地方治安,維護封建專制制度的統治,使清政府的統治得以茍延殘喘,另一方面促進了紳權的擴張,嚴重侵害官府利益和權威,破壞清王朝統治,加速其離心解體,形成了基礎政權與中央政權的博弈,對封建統治產生了離心作用,引起傳統社會結構與社會控制的顯著變動。
一、團練與保甲
清代團練萌生于社會控制嚴重衰弱的年代,在保甲制地方防御功能的基礎上延伸發展而來,“有保甲制度而后,因其地方防御之功能,始有團練之組織”1。清王朝的統治日趨衰落,在社會大動亂時期,鄉村治安日趨面臨緊急危機的情況下,團練從保甲結構中脫胎而出,從保甲的警衛功能轉化為團練的地方防御,因此,團練與保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其中“團練的組織規模與官僚政治的區劃保甲、里甲的組織規模相對應,在某些情況下導致行政的和自然的協作單位的混淆和逐漸融合”2。團練與保甲常常相比附而行,相輔相成,亂時則團練為靖難之方,平時則保甲為彌盜之策。清代團練的形成,在很多情況下,或是在保甲組織中而納入團練的內容,或以保甲為基礎組成團練,即使是不具有實際作用的保甲組織也能為團練的組織提供了現成的形式。由于保甲不僅利于組織團練,還可以使團練的穩定和團丁的來源有所保證,因此時人常云先保甲而后團練,或欲團練必先保甲。不過,隨著團練的發展壯大,保甲逐漸被包容于團練組織系統之內,團練等地方武裝漸漸取代了保甲制度的功能,逐漸由軍事組織演變成了地方政治組織,發展成為基層社會控制的一種有力組織。
保甲制是“將散漫而無統系之民眾,用一種適合于社會環境之規律,依一定之數字與方式,精密組織之;使成為有統系之政體”1,通過株連互保及責任連帶以達到“制一人足以為制一家,制一家亦足以制一鄉一邑”2之目的。保甲之名創建于宋,清代統治者為加強統治,參照宋明之制,在鄉村設里甲制和保甲制,其中由于“攤丁入畝”的實施,與賦役制度緊密結合的鄉里編組形式難于繼續,里甲制也就隨之失去效用,保甲制逐成為清朝最主要的鄉里制度。不過因各個時期情況不同而有所差別,其職能或重于教,或重于戶口,或重于課賦,或重于詰奸,或重于捕盜。
同時由于保甲制度老百姓不堪其擾,不斷以各種方式抵制和反抗,而地方官吏“在貫徹和監督保甲管理的過程中似乎半心半意”3,保甲制度常常處于奉行不力的狀況。到嘉慶時期,封建統治秩序受到嚴重沖擊,保甲組織更普遍廢弛,但隨著封建國家的統治力量日趨衰微、武裝斗爭在各地不斷發展,清王朝的經制之師八旗綠營也征剿無力時,從中央到地方,各官員將領又才紛紛要求嚴行保甲,被白蓮教侵擾的四川、湖南等地,辦團練者越來越多,團練相繼興起。不過這一時期保甲成分多,而團練成分少,且叛亂結束后,團練就被解散。
迨太平軍狂飆突起,所到之處封建體系分崩離析,政府機構陷于癱瘓,由于“保甲在承平時期可以在一定程度內發揮作用,但卻不能滿足動亂時期的要求。它的官僚政治的、形式主義的行使權力的方式對于遏制嚴重的社會和軍事危機就過于軟弱”4,所以保甲制已不能勝任其維護治安的職責,對于地方日益擴大的混亂無能為力。故咸豐帝沿襲嘉慶朝團練剿匪有功的思路,寄希望于地方團練武裝力量,“俾兵民聯為一氣,庶眾志成城,人思敵愾, 蠢茲小丑,不難克期蕩平也”5,而地方為了自衛也創辦團練以響應清廷的號召,于是團練以燎原之勢在各地紛紛出現。
團練與保甲常相比附而行,相輔相成,或在保甲組織中納入團練的內容,或以保甲為基礎而組建團練,將二者緊密結合起來,成為貴州團練組織形式上的一大特點。如,水城縣的團防即“向遵保甲法辦理,每十戶為一牌,設一牌長,一家有事,十家相助;一家不法,十家連坐”6。胡林翼則用印冊“將某寨若干戶,十戶一牌,立一牌長。一寨一團,立一團長。數團之中,設為總團,立一鄉正”7,互相稽覆捕治諸不法者, 以為御寇莫如團練,清內匪莫如保甲,編保甲,立團練,使保甲與團練既分工又合作,致使“黎平團練,目前無寨不傳簽,無寨不集眾,士民奉令為勤”8,如此“合一郡之人,人人皆有盜捕之責,人人皆為捕盜之人,盜將安往?從至纖至細起結成大局,不特內訌不作,即外辱亦自息矣”9。在貴陽府,唐炯集眾立團時兼行保甲之法;鎮遠因籌設府縣兩屬團防總局以清查戶口,并編聯團甲以圖自衛而補兵力之不逮,地方漸就寧靖。
二、團練與宗族
宗族制度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了幾千年,經歷了一個變化和發展的歷史過程。清代普遍存在于全國城鄉、自宋明以來才發展起來的宗族組織,以血緣關系為紐帶,以祠堂、族譜、族長三者為核心,以族田為“收族”的經濟手段,早已形成牢固的族權,成為當時封建制度社會結構的有機組成部分。其中,“祠堂者,敬宗者也”,“祖宗之神依于主,主則依于祠堂,無祠堂則無以妥亡者”1,當時,祠堂遍布全國城鄉,“直省中惟閩中、江西、湖南皆聚族而居,族皆有祠”2。族譜作為血緣紐帶而不分貴賤貧富,旨在喚起族人“木本水源”之思而不忘本,從而達到“睦族”之目的。族田是宗族存在的物質基礎,族長是族權的人格化代表,掌管全族事務,通過族規維護著宗族機構的正常運行,使宗族組織產生出強固的內部凝聚力,使基層社會保持穩定狀態。“以‘敬宗收族為目的的宗族制度在清代的發展,無論在政治上、抑或思想文化領域內,都對族人強行約束;同時,又以‘義田等作為‘恤族的經濟手段,給宗族內部的階級對立蒙上一層‘溫情脈脈的薄紗”3,成為封建統治的重要補充力量。
咸同之際,為了挽救岌岌可危之形勢,清廷號召在職官吏各回本籍憑借宗族勢力舉辦團練,不得不承認宗族的族權,使其承擔起維護基層社會治安的作用,“而后自團練自守御者有義勇,而上亦兢兢昭顯章示之,以補王政所窮”4,重申乾隆時期的法令,“凡聚族而居,丁口眾多者,準擇族中有品望者一人立為族正,該族良莠,責令察舉 ”,5于是以族人為基本力量、以族規為法令約束、以族權為指揮系統,在“鄉族自衛”和“維護幾千年綱常名教”的旗子下,各地“師皆父子,族盡兄弟”的宗法性團練武裝紛紛成立,投入到與起義軍作戰的行列。由于民眾大多聚族而居,利用族團對抗起義軍有很多優勢,宗族內部擁有其他社會群體所無法比擬的凝聚力,所以練團必先練族,以一族之父兄治一族之子弟,形成以保甲為經、宗法為緯的統治網,“一經一緯,參稽互考,常則社倉易于醵資,變則團練易于合力”6,將不同階層的人緊緊拴在一起,增強其自身的戰斗力,例如“廣東的宗族與團練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已合為一體,一個單一族的村的團練,不多不少就是一個宗族組織”7。在聚族而居如閩、贛、湘、皖等南方地區,團練往往以族團的形式出現,如湖南曾國藩的湘軍,安徽的苗霈林團練,李鴻章的淮軍等,就是由族團發展而來,這種在族正制、宗族制基礎上成立的團練的組織性更強,族正、族長往往是團練的首領。
南方宗族較北方為多,貴州屬南方,貴州民族成分復雜,大多雜姓而居,其宗族勢力相對弱小,但貴州的宗族在叛亂時期,特別是咸同貴州各族人民大起義的大變局中,宗族仍起有較大作用,如興義的劉氏家族,咸同時期,劉氏即著手組織地方防務,創辦團練并靠團練而崛起為一方之霸,對清代貴州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劉氏團練三次復興義城,其本人亦因軍功顯著而被官府賞戴花翎,躋身官場,使劉家的地方領袖地位合法化,并使劉氏跳出了庶民階層,躋身于縉紳行列,與遠在昆明的總督府建立了有用的正式關系。團練領導權是劉氏家族地位和權勢扶搖直上、急速膨脹的一大工具。
三、團練與士紳
“紳士為四民之首,為鄉民所仰望”8,是介于官僚與平民之間,不同于官、又區別于民的封建統治階級內部一種在野特權階層,一般是指有功名的人在其家鄉的稱呼,是由科舉制度和學校制度產生的一個社會階層的特定名稱。雖然士紳沒有象官員那樣擁有正式的權力,但封建的功名身份賦予了士紳特殊的社會地位,而農耕文明又使得士紳的功名與鄉土社會扭結在一起,使士紳擁有基層社會所賦予的“天然”權威,使士紳成為封建王朝也是傳統社會秩序的支柱,成為基層社區的代表,對地方社會有著重大影響,尤其是在晚清社會大動亂時期,其作用更為突出,“自寇亂以來,地方公事,官不能離紳士而有為”1。在清政府的經制之師腐敗至極,清政府諭令各直隸省辦團練時,士紳是大部分團練的發起者、創辦者和組織者,“在地方士紳的領導下,團練成為動亂時期官府控制鄉村的關鍵。同時,以興辦團練為契機,軍功士紳大量涌現”2,形成空前紳權大張之勢。正是這樣的紳士階層,和地方行政長官一道,維護傳統的政治格局和社會秩序,支撐著這座早已千瘡百孔、搖搖欲墜而不堪一擊的清王朝的大廈,使清王朝的統治得以茍延殘喘。
在咸同社會大動亂的時代里,因貧富差異所產生的階層仇恨在動亂時期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暫時讓位于群體性生命安全的擔憂,群體這種對安全感的渴望致使在共同的敵人面前不同階層能夠團結起來,并讓士紳居于地方領袖地位出面組織和領導鄉民承擔擊退敵人的任務。
正是因為士紳積極參與舉辦團練,既維護切身利益,同時協助官軍抵御盜匪和鎮壓義軍,維持地方秩序,維護清王朝的統治,因而獲得好的名聲,鞏固其在地方的領袖地位,增加了其在地方的社會“權威”,有的士紳因軍功顯著而被賞戴花翎,躋身官場。例如郎岱廳趙德光“咸豐六年始由勇丁征云南回匪積功,保六品軍功、藍翎。八年,云貴總督吳振棫飭令回黔剿匪于平越一帶,以千總拔補,賞五品頂戴。十年克復修文縣城,擢都司,賞換花翎”3,于同治五年屬貴州提督。銅仁李丕基因頻年以團練助官軍剿賊,“由俊秀累功保知府銜候選同知”4。
由于士紳是團練主要發起者,經濟力量的支撐者和組織者,所以士紳一般居于團練的實際領導地位。盡管從舉辦團練開始,清王朝試圖由官總其權而紳董其事,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由于“特官之于民,尊而不親。條告視為具文,刑章亦幸圖茍免。不若鄉里之士大夫,朝夕與處,情易通而言亦入也”5,通常“官有更替,不如紳之居處常親,官有隔閡,不如紳之見聞切近,故紳士之賢否,關乎團練之得失甚巨”6,不得不承認士紳擔任團練領袖的必要性。因此在實際操作中,因功名身份而具有社會權威的士紳成為團練組織中不容置換的領袖而掌握團練的領導權。所以團練“不僅確立了紳士在團練這一特定社會控制組織中的突出地位,而且也使紳士階層擺脫了在保甲系統中的社會尷尬,從而成為近代時期基層社會控制的主體”7,主要由士紳領導的團練使國家政權與基層社會之間的關系發生錯位,對以后的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四、團練與官府
咸豐年間,太平天國起義嚴重威脅清王朝的封建統治,為了挽救危如覆卵的形勢,咸豐帝沿襲嘉慶朝的思路,借助地方團練武裝力量,諭令各直隸省大辦團練,于是全國團練蜂起,在基層社會扮演了重要而復雜的角色。
在貴州,在社會大動亂時期,團練與官軍一道抵御盜賊,鎮壓農民起義軍,維持地方秩序。例如在貴陽府,高以廉奉命籌辦全黔防務,系全局安危,所以眾人常不稱其名而稱之為“高十二”;另有趙國澍在青巖石堡地方所興辦之團練深資捍衛,為省城犄角,迭著成績,其維護地方秩序的事例更不勝枚舉,甚至有的團練所建屯堡在城失陷后成為官吏的逋逃之處,如龍里縣東北羊場,“地方憑高結寨,地勢最佳。軍興以來,地方人士創威遠團于其間以自保。其后縣城屢陷,即長官亦寄寓團營,以為退守進取之地”8。但團練好比一把雙刃劍,其對于維持地方秩序,維護和加強清王朝的統治,確也曾擔負過重大的任務和作出巨大貢獻,但團練 曾對于中央政權所起的分化、離心作用,特別是“行之既久,流弊益多”1,隨著團練勢力的發展,團練的主要領導者地主士紳的地位不斷提高,勢力和影響也漸次膨脹,常有“借團練以科斂錢谷者無論,已有名為團總而實通賊者,不惟鄉閭仰其鼻息以圖保身家,即地方官亦聽其指揮以茍全性命”2,他們依仗權勢而桀驁不馴或獨霸一方;或互相爭斗;或依違于官府、義軍之間;或與官府爭利甚至對抗。“始也欺壓鄉里,今也挾制官長,或因要求不遂播散謠言,無識者遂以飛語之雌黃定長官之賢否”3,甚至橫行無忌,凌駕官府之上。因地方官無力駕御,從而引起新的地方動亂。“許多團練頭子,借保衛桑梓之名,拉起武裝,割據一方,不僅擾害貧苦之民,且乘機兼并勢小者以擴大地盤勢力”4,其勢強者成為在地方主宰人民生殺予奪之權的“土皇帝”和“鄉里王”,致使“小民知練總之尊,而不知有官府之令”5,除了抗官以外,還有一些團練與盜匪義軍通,有的甚至還加入其中而站在官軍的對立面,從官府的朋友變成官府的敵人。“似此情形,故咸同之際,團練的存在,倒成為軍事上的一個苦惱之癌”6,對清王朝的解體起到了剝蝕和離心的作用。
在貴州,“大亂之際,常有惡紳、強團據城逐官等事。其人在非賊非民之列,其跡在不臣不叛之間”7,例如興義的各屬強團回首,叛服不常,官其地者,弱則受其制,強則遭其害。至于一些不肖地主士紳,“借團自肥,勾結群小,危害桑梓,二十年中,亦正不乏其人焉”8。戰亂中帶兵各員大多居御賊之名而行賊之實,“藉鄉勇以為生財之具,橫征暴斂,擅行殺戮,甚至縱勇攻寨,肆意迫捐”9。援黔川軍總領唐炯對貴州興辦團練的利弊的體會,他曾說:“而桀驁之徒往往肆其橫暴,其始藉官以脅眾,其繼則集眾以挾官,致使十余年來官不敢問,吏不敢詰,任其招聚匪徒為之爪牙,部勒小民聽其驅策,一有睚眥之怨便爾爭斗不休,甚至霸據田產,毀人墳墓,焚燒擄掠,殺戮奸淫”10。更有一些地方豪紳往往借團練之名,常干預地方公事,借名苛斂,私立厘卡,攘奪民財,私設公局,擅作威福,甚且草菅人命,擅殺官吏,逞強械斗,或聚眾搗毀官署,例如“貴州清鎮團首何山斗因逼捐未遂,田興恕執而戮之,該處百姓積忿已深,遂將厘金局委員戕斃,見在聚眾數萬,豎貴州十三府總團旗號,聲稱圍省殺趙國澍方休”11。咸同各族人民大起義時期,團練抗官的情形,屢見不鮮,著名的還有遵義花田團首王安國,銅仁府三元團首雷洲、李丕基,桐梓太和團首王正儒、王正倫等。
早在咸同年間,團練在基層社會所扮演的角色重大而復雜,有些團練除了干預公事,獨霸一方,聯團抗官外,與盜匪和義軍有千絲萬縷的關系。其中團練對盜匪“暗送秋波”、持曖昧態度,他們依違于官府、義軍之間,賊來附賊,官至倚官,首鼠兩端。例如郎岱坡貢中寨團首楊開祥,因其數從官軍擊賊而頗有功,倚恃其團廣人眾,浸驕恣且通賊,挾兩端;銅仁府三元團首雷洲、李丕基常與荊竹園賊通;桐梓太和團首王正儒游弋于官府和號軍之間。許多團練在賊勢強大而官兵不足恃時,常常附賊以求自保,例如當攻興義城時,“趙德光回援,以團丁守城,自營城外盤山,賊日益眾,團丁皆散,爭附賊”1。有的公開與賊合作,例如安順府之被圍,乃“本處之六合團民與苗匪等勾結一氣,筑壘攻城”2。此后,這種情況是有增無減,并逐漸形成地方勢力與中央政府對立的局面。
五、結論
清代團練萌生于社會控制嚴重衰弱的年代,在保甲制地方防御功能的基礎上延伸發展而來,隨著團練的發展壯大,保甲逐漸被包容于團練組織系統之內,團練等地方武裝漸漸取代了保甲制度的功能,逐漸由軍事組織演變成了地方政治組織,發展成為基層社會控制的一種有力組織。咸同之際,為了挽救岌岌可危之形勢,清廷號召在職官吏各回本籍憑借宗族勢力舉辦團練,不得不承認宗族的族權,使其承擔起維護基層社會治安的作用,以族人為基本力量、以族規為法令約束、以族權為指揮系統的宗法性團練武裝紛紛成立,投入到與起義軍作戰的行列。作為四民之首的士紳,其功名與鄉土社會扭結在一起,使士紳擁有基層社會所賦予的“天然”權威,使士紳成為封建王朝也是傳統社會秩序的支柱,成為基層社區的代表,咸同社會大動亂時期,士紳積極創辦團練,成為大部分團練的發起者、創辦者和組織者,對地方社會產生重大影響,尤其是在晚清社會大動亂時期,其作用更為突出,形成空前紳權大張之勢。貴州團練因社會動亂而興起,亦因動亂結束而表面上解體退出歷史舞臺,其對清代貴州歷史產生了重大影響,既維護封建專制制度的統治,使清政府的統治得以茍延殘喘,另一方面促進了紳權的擴張,嚴重破壞清王朝統治,加速其離心解體,形成了地方政權與中央政權的博弈,對封建統治產生了離心作用,引起傳統社會結構與社會控制的顯著變動。
Tunalien and local politics in the Qing Dynasty of Guizhou
Zhang Xi Qin
Abstract:Tunalien has played an impotant and complicated role in the history of Guizhou . In this paper, combined with specific historical events in Guizhou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ise of Qing Dynasty,analyzes the status and influence of the Bao-Jia system-a local grass-roots system,the Clan and the Gentry-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local society.At the second,individually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the Tunalien rise which caused by the dilemma of Bao-Jia system,the reasons that the Clan and the Gentry organize Tunalien.In addition,analyzes the duality of Tunalien which maintenances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social order,at she some time infringes the government interests and authority,eroses and decentrlises the central regim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unalien and government,in order to reveal the evolution of Tunalien and local 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Guizhou,and investigate the position of the common people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ety upheaval.
Keywords:Guizhou Tunalien,Bao-jia,the Clan,the Gentry,the Government
1王爾敏《清代勇營制度》,載于《清季軍事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第3頁。
2(美)孔飛力著《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修訂版),謝亮生,楊品泉,謝思煒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第104頁。
1 聞鈞天《中國保甲制度》,北京: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4頁。
2 聞鈞天《中國保甲制度》,北京: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16頁。
3 瞿同祖著,范忠信、宴峰譯《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54~255頁。
4 (美)孔飛力著《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修訂版),謝亮生,楊品泉,謝思煒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第62頁。
5 《文宗顯皇帝實錄》卷八十七,咸豐三年三月上庚戌諭內閣,中華書局,1986,《清實錄》四十一冊,149頁。
6 六盤水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六盤水公舊志點校·水城縣志稿》,貴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19頁。
7 胡林翼《胡林翼集》(二),《凱里紳士團練諭》,長沙岳麓書社,1999年,第133頁。
8 胡林翼《胡林翼集》(二),《致呂佺孫》,咸豐元年六月二十九日,長沙岳麓書社,1999年,第58頁。
9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第十二冊,長沙岳麓書社,1996年,第10015頁。
1 張永銓《先祠記》,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卷六十六,《禮政十三·祭禮》,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
2 陳宏謀《寄楊樸園景素書》,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卷五十八,《禮政·宗法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
3 王思治《宗族制度淺論》,載于《清史論稿》,成都巴蜀書社,1987年,第1頁。
4 魏源《廬江章氏義莊記》,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卷五十八,《禮政·宗法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
5 《欽定戶部則例》卷三《戶口·保甲》,第7頁,同治十三年校刊本。
6 馮桂芳著《顯志堂稿》卷十一,《復宗法議》,臺北文海出版社,第1032頁。
7 〔美〕魏斐德著《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王小荷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127頁。
8 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專刊,第165頁。
1 胡林翼《胡林翼集》(二),《麻城縣稟陳各局紳籌辦捐輸情形批》,長沙岳麓書社,1999年,第1012頁。
2 楊國安《國家權力與民間秩序:多元視野下的明清兩湖鄉村社會的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40頁。
3 黎庶昌《拙尊園叢稿》,卷二,《趙剛節公神道碑銘》,臺北文海出版社,第110頁。
4 (民國)《銅仁府志》卷九,《武備·記兵》,第15頁,民國三十五年據光緒十八年刻本縮印。
5 胡林翼《胡林翼集》(二),《致保弟等》,長沙岳麓書社,1999年,第1074頁。
6 惠慶《奏陳粵西團練日壞亟宜挽救疏》,盛康輯《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八十二,《 兵政八·團練下》,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2469頁。
7 王先明《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論》,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1頁。
8 凌惕安《咸同貴州軍事史》,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163頁。
1 劉岳昭《陳奏滇黔現在軍情及吏治營務團練各情形折子》,《滇黔奏議》,卷三,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293頁。
2 朱孫詒《團練說》,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六十八,《兵政七·保甲》,臺北文海出版社。
3 劉岳昭《陳奏滇黔現在軍情及吏治營務團練各情形折子》,《滇黔奏議》,卷三,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293頁。
4 張山《太平天國時期貴州團練問題初探》,《廣西民族研究》,1988年第三期。
5 傅衣凌《太平天國時代團練抗官問題引論—— 太平天國時代的社會變革史研究》,載于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卷五,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49頁。
6 傅衣凌《太平天國時代團練抗官問題引論—— 太平天國時代的社會變革史研究》,載于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第449頁。
7 (清)羅文彬、王秉恩編纂《平黔紀略》,貴州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教研室點校,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頁。
8 凌惕安《咸同貴州軍事史》,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161~162頁。
9 (清)羅文彬、王秉恩編纂《平黔紀略》,貴州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教研室點校,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9~380頁。
10 唐炯《援黔錄》卷三,《附稟貴州巡撫夾單》,第5頁。
11 《穆宗毅皇帝實錄》卷八十四,同治元年正月下庚戌議政王軍機大臣等,中華書局,1986,《清實錄》第四十五冊,481頁。
1(清)羅文彬、王秉恩編纂《平黔紀略》,貴州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教研室點校,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13頁。
2劉岳昭《陳奏滇黔現在軍情及吏治營務團練各情形折子》,《滇黔奏議》,卷三,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2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