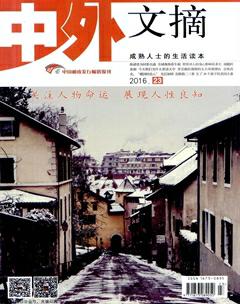斯諾登為何要出逃
□ 程 蒙
斯諾登為何要出逃
□ 程蒙

約翰·克蘭住在波托馬克河南岸,那里森林茂密、丘陵起伏,離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總部也不遠;沿著河流往上幾英里,便是五角大樓。身為美國軍事情報部門的一員,克蘭一直把這里當做自己的家。在這個情報體系里,他已經干了25年了。對克蘭來說,這個情報體系就是一種信仰,然而這個情報機構卻已視克蘭為敵。
斯諾登只能逃出去
克蘭坐在廚房里,他面前放著一個公文袋,上面蓋著美國政府印章。克蘭已經60歲了,梳著大背頭,胡子修理得整整齊齊,這讓他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要年輕。他依然穿著日常制服:一件印有他姓名首字母的襯衫,上面釘了袖扣;外套上釘著一排金色紐扣。25年來,他每天都是穿著這樣的衣服去上班,到安保門禁時亮出自己的徽章,然后徑直開進弗吉尼亞州阿靈頓的基地,走進辦公室。他時常可以看到五角大樓,就在他辦公室窗戶的右邊。
之后克蘭他們搬了一次辦公室,搬到了一個無名之塔中;他們依然是美國國防部非常重要的部分。這么多年來,他一直都在軍隊中工作;最終,他當上了副總監察長,成功躋身高層。總監察長手下有1600名公務員,其中有90人歸克蘭管轄。他們的職責就是監督內部問題、腐敗和其他違法行為。在現代民主政治中,總監察長一職就像橄欖球的自由后衛,確保整個政府體系在法治環境中正常運轉。
克蘭在五角大樓的工作非常敏感。他的職責就是“擦屁股”——從解決辦公室糾紛到處理重大丑聞,而這些問題都是軍隊內部的問題。具體來說,他的首要之責便是協調美國國會和國防部內部舉報體系之間的關系。說起來,這個國防部內部舉報體系就是一個面向五角大樓300萬雇員的“舉報箱”,美國國家安全局也在受監督的范圍之內,畢竟它也隸屬于五角大樓。克蘭一直做著這個工作,直到有一天他發現自己的上司濫用職權,干預一樁舉報。
這個事件讓克蘭開始質疑他所為之奉獻的一切。而正是因為這起事件,這位五角大樓高官與上司發生了爭執,最終他在2013年被踢出局。在25年的職業生涯中,克蘭處理了無數的舉報案件,這次他決定向媒體爆料,自己也做回舉報人。
克蘭要說的這個事情源自于美國總統奧巴馬和民主黨總統參選人希拉里·克林頓,他們倆都談到過一個人:愛德華·斯諾登。美國政府反復強調,斯諾登本不必潛藏起來,也不必將自己的故事公之于眾。他們的潛臺詞就是:監控體系是沒問題的,有問題的是斯諾登自己。
對于斯諾登這個人,奧巴馬曾表示“對政府行為有良心不安的人來說,總還有其他的方式來解決問題”,而在民主黨初選中,希拉里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斯諾登可以在政府機構內檢舉揭發,他會成為檢舉人,然后得到保護。他可以舉報一切問題,政府部門也一定會給他積極回應的。”
在弗吉尼亞的家里,克蘭目光遠眺,望向波托馬克河對岸,那個方向朝著五角大樓。克蘭知道事實的真相并非奧巴馬和希拉里說的那么簡單。如果真如他們所說,斯諾登該如何通過國內渠道來檢舉揭發?他并不是政府官員,他只是一個國家安全局外包公司的雇員。所以,斯諾登怎樣才能像公務員一樣,在告密之后得到政府的法律保護呢?即便當事人不是斯諾登這種平民,而是克蘭這種軍方高官,恐怕也沒法順利過關。
克蘭嘆了一口氣,努力拼湊著詞句來解釋自己內心的疑慮:“我可是親眼見識過如果當事人按照規定,通過官方渠道檢舉揭發,他會發生什么。”說來有意思,美國政府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為軍隊內部和國安局的揭發檢舉準備了相應的應對方案。
大學畢業后,克蘭就為一個名叫比爾·迪金森的共和黨眾議員工作。迪金森是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核心成員,同時他還是成立總監察辦公室的倡議者之一。這一職位甫一設立,克蘭就成為辦公室的首批雇員。在職業生涯中,克蘭為12位總監察長工作過,在他的幫助下,該機構為檢舉人設立了“熱線”。在克蘭看來,檢舉人是民主制度的支柱之一,這些人的存在可以幫助政府改進工作。
在切爾西·曼寧向維基解密披露了大量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軍事行動文件后,克蘭就力促建立一個新的內部制度,專門應對涉及機密情報的申訴,并為此確立了高度機密的程序,之后這一制度成文出臺。在克蘭供職五角大樓期間,他把1978年出臺的檢舉人保護法案打印成冊,以確保總監察辦公室里的所有人都能對這個隨時會付諸實踐的法案了然于胸。在克蘭看來,他的本意就是要確保不會再出現下一個斯諾登。
直到現在,克蘭依然不太贊成曼寧和斯諾登的做法。他覺得斯諾登逃到俄羅斯去實屬悲劇,而這一悲劇本可以避免。他依然認為內部方式解決問題才是好的出路。而內部渠道行不通不是因為制度的問題,而是那些在上位者的過錯,正是這些在上位者才未能讓法律得以充分實現。
監守自盜的監察機構
約翰·克蘭起初有所懷疑是在2004年,在那不久前,他被提拔為副總監察長,這個職位算是五角大樓的高層了。彼時距離2001年的9·11事件時隔不遠,針對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的襲擊徹底改變了美國安全部門的運作方式。在小布什總統的授權下,安全部門很快得到了大筆預算和更高級別的權限。
國安局內部有人開始注意到這些變化背后的東西。他們發現,監控不僅針對恐怖分子,還會瞄準普通美國公民,而這在他們看來是違反憲法的。監控項目耗資近40億美元,錢都流向了與國安局簽了合同的私人公司,這些納稅人的錢最終都被用來監視納稅人。為此,有人提出了一個名叫“細針”的內部解決方案,這個方案可以更好地處理好反恐監控,而且還能節約數十億美元。
這群質疑者就包括三名國安局的前雇員,一名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的前雇員,還有一個便是國安局監控項目核心領導之一的托馬斯·德雷克。
德雷克將自己的不滿直接告訴了國安局總監察長。其他幾位(比爾·賓利、科爾克·維貝、埃德·盧米斯和戴安·羅克)則向五角大樓總監察長發出了投訴,而那里正是克蘭工作的地方。2002年9月,正式的投訴文書送到了克蘭的辦公桌前。
2003年1月,克蘭手下的監察員們與德雷克見了面,之后好幾年對他進行了多次盤問。德雷克也向監察室遞交了國安局的文件,以證明自己說的都是真的。安保人員將德雷克每次進出總監察長辦公室的信息都記錄下來,德雷克感覺自己已經被人監視了。
克蘭的手下經過仔細調查,確認了德雷克所說的大部分屬實,這一巴掌狠狠地扇在了國安局局長邁克爾·海登的臉上。2006年,美國國會經過投票,叫停了飽受爭議的“開拓者”項目。然而,國安局依然通過其他方式來進行大規模監控。
德雷克事件可以說是舉報人制度的一次成功案例。但從一開始,德雷克和他那四個同伴都覺得自己會被報復。這五人小組中,有四個人在舉報時用了真名,而德雷克自己卻因為害怕只用了“管理層高級主管”的身份來做化名。在克蘭看來,德雷克的擔心不無道理,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于是,他打算在內部展開更深入的調查。
克蘭的上司沒有批準這項深入調查,這讓克蘭憤憤不平。在他看來,自家老板的行為就是在妨礙監察工作。克蘭說:“這恰恰說明,這個事情必須得深入徹查。”
擔心很快被證實了。2007年7月的一個早上,聯邦調查局特工突擊搜查了四位舉報人的公寓。四個月后,聯邦調查局的特工又出現在德雷克家門口,要知道,德雷克的名字在內部調查報告上可是匿名的。
德雷克長期為情報部門工作,在為美國空軍情報部門工作期間,他曾監聽東德情報機構史塔西秘密警察之間的電報往來。后來他調往國安局,第一天上班他就遇到了9·11事件。
現在,德雷克被聯邦調查局關押了起來,可能會面臨35年監禁。德雷克在忠誠調查中沒有過關,他的職業生涯被毀掉了,而造成這一切的正是他所信賴的內部舉報渠道。在針對德雷克的指控中,有一項指控他向《巴爾的摩太陽報》記者泄露機密情報,還有一項指控他用個人電腦保存國安局機密文件,這些都被他一一否認了。
就在德雷克的審判即將開始之前,聯邦政府撤消了所有指控。德雷克最終因為誤用國安局電腦被判處一年緩刑,并被處罰社區服務。在宣判時,法官措辭嚴厲地批評了公訴人,認為他們對德雷克的行為“毫無良心”。盡管法律還了德雷克公道,但他卻已經丟了工作,沒了養老金,還失去了很多朋友。
德雷克并不知道的是,自己的案子會把克蘭這個監察辦公室高官打入對手之手。而考慮到德雷克害怕被報復的處境,克蘭決定要把這事一查到底,他內心深處的懷疑也隱隱透出一絲不安。
上面插手了
2005年,《紐約時報》報道了國家安全局的國內監控項目,此文一出,舉世關注。時任美國副總統迪克·切尼下令追查新聞根源。很快,五名國安局舉報人變成了嫌疑犯,這五個人有一個共性:他們都在內部抨擊過監控項目。
約翰·克蘭至今仍記得,自己的上司在一次內部會議上提議將舉報人的名單轉給調查此事的美國司法部,克蘭則表示反對,他認為這是對匿名舉報人的迫害。兩人爭得不可開交,從會議室吵到會議室外,最終克蘭掏出那本寫有舉報人保護條例的小冊子。末了,克蘭的上司只得說,既然克蘭是負責協調與司法部關系的人,那克蘭自己好自為之吧。
對于克蘭的這番說法,五角大樓和監察辦公室方面都拒絕向媒體作出回應。而克蘭當時的那位上司也以保密條例為由不予回應,他甚至說,如果這一事件公開調查,他有信心證明自己是無辜的。
克蘭的懷疑有增無減,特別是與德雷克事件有關的重要文件從總監察辦公室消失之后,這種懷疑越來越重。德雷克的律師杰希林·拉達克曾請求法庭詢問這份文件的去向,因為這份文件可以證明德雷克只在自己的個人電腦上存了這唯一一份文件,其目的是向監察室舉報,而不涉及泄密。如是這般,德雷克便可免遭起訴。
然而這份文件卻沒能在總監察辦公室找到,據說這份文件已經被碎紙機粉碎了。而克蘭的上司這么跟他說:“替大家伙想想。”之后,這位上司告訴法官,文件是因為工作失誤而不幸丟失。對此,克蘭卻是一個字也不相信。在他看來,這份文件是被故意銷毀的。“在刑事訴訟中對法官撒謊可是重罪。”克蘭說。
克蘭并不想“為大伙想想”。他要反抗,要投訴,他向上司表示自己不會就此沉默。由于事關德雷克案,當時便可預見克蘭不會有好結果。2013年,總監察長把克蘭叫到辦公室,當著他的面把解職書遞給了他,隨后一名安保人員取走了克蘭的通行證。
祖父的榜樣
在做了25年勤懇的公務員后,克蘭為何選擇了反抗?究竟是什么讓他可以拿自己的職業生涯、公職人員的名譽、友誼甚至養老金來冒險?
克蘭走過五角大樓附近的伯德·約翰遜夫人公園,如今他不必每天一大早趕去辦公室,有大把大把的時間。散步的時候,他雙手背在背后。他還在五角大樓時,跟他打交道的都是參眾兩院的議員,他也把自己視為執法機關和立法機構的紐帶。在克蘭看來,像奧巴馬總統這樣的政治家是希望改善民主的。“我必須得做正確的事,”克蘭說,“就像我那位德國爺爺一樣。”
克蘭的祖父名叫金特爾·里德爾,是德國空軍上校,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1923年11月8日,當阿道夫·希特勒和其黨徒打算在慕尼黑的貝格勃勞凱勒啤酒館發動著名的啤酒館暴動時,里德爾和幾個其他的士兵也在啤酒館里。當希特勒拿著手槍對準里德爾的一位朋友時,里德爾擋在了槍口前,說道:“希特勒先生,你絕不可能用這種方式來解放德國人民。”
希特勒最終放下了武器,然后轉身去發動暴動了。里德爾平息了事態,之后在一份長達8頁的個人檔案里記錄了此事,由于有目擊證人,此事的真實性得到驗證。后來德國政府在戰后針對希特勒發起的公訴中打算邀請里德爾出庭作證,不過最終沒能成行。
克蘭說,直到今天,他還是非常崇拜自己的祖父,1923年的歷史事跡一直都激勵著他。不過克蘭也知道,祖父的個人事跡不只有光輝的一面,后來里德爾留在了納粹國防軍,成為納粹空軍的中堅力量,并被晉升為將軍。1942年,里德爾被解職,之后全家搬往巴伐利亞定居。
2000年,里德爾在二戰中的經歷再度被翻了出來,時任德國國防部長魯道夫·沙爾平將一個以里德爾的名字命名的空軍營改了名;與此同時,有消息顯示里德爾還出任過納粹德國人民法庭的志愿陪審員,這個法庭就是納粹政權用來迫害政敵的。不過進一步的調查顯示,里德爾只參加過一場聽證會,而且還主張釋放被告人。而那個更名的空軍營又把指揮官辦公室命名為里德爾辦公室,克蘭和自己的母親還親自出席了命名儀式。
“我從我爺爺身上學到了一種道德責任感,那就是如果政府違法了,身為個人就應該挺身而出。”克蘭如是說。他也坦承,這種高度的道德責任感會讓人難免覺得痛苦,但又令人義無反顧,“在我眼里,監察工作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份使命。”克蘭從口袋里掏出一張紙,上面有德國神學家、著名的反納粹斗士馬丁·尼莫拉的那段話:“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時,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時,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后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時,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最后他們奔我而來——那時已經沒有人為我講話了。”讀完這段話,克蘭沉默了好一會兒。
“體制還有用”
“克蘭‘反水’,本質上是因為監察制度不管用了,”托馬斯·德雷克說,“他救了我。”德雷克和克蘭在雙雙被解除公職后私下里僅見過一次。兩人都堅信證明自己是無罪的那一刻終會來臨。德雷克說,自己很快就會拿回自己的養老金,當下他還在蘋果店里做銷售員。
而克蘭這邊,他已經向當局提交多份書面申請,控告當局濫用權力。他的律師也向特別檢察官辦公室遞交了投訴書,投訴克蘭前同事的不當行為——破壞舉報者的正當權利。
斯諾登曾說,德雷克的下場讓他感覺無法信任當局,所以他帶著秘密潛逃。“在德雷克眼里,當局是絕對正確的,”斯諾登評價說,“然而當局不會保護這些舉報人,反而會迫害他們。”
在克蘭看來,斯諾登被迫流亡真的是美國的悲哀,因為對于斯諾登來說,他無處伸冤,他們如此這般不過是自我保護。克蘭說,自己的那幫同事本來就差點把斯諾登變成下一個德雷克了,這簡直就是美國情報部門的恥辱,也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失敗。“有德雷克的范例在先,斯諾登怎么還會相信這個制度?”克蘭如是說。
“我還在國安局的時候,大家都知道如果出了問題走官方渠道,很可能結局就是滾蛋,這還算是好的了。這就是一種官場文化,”在跟媒體談到克蘭的案子時,斯諾登如是說,“如果你只是舉報你的上司,那總監察長或許會看兩眼你的舉報信;可如果你舉報的是下令監控全美的美國總統呢?你覺得總監察長會怎么辦?那他們會把你碾得粉碎。”
為了證實自己的說法,斯諾登補充道:“我去找過同事,找過上司,甚至找過律師,你知道他們怎么說的嗎?‘你簡直是在玩火’。”

約翰·克蘭在五角大樓的通行證
“如今這種政策的悲哀現實就是,拿證據去找總監察長都沒法說理。找媒體爆料也要冒很大風險,不過至少你還有一線生機。”斯諾登說。按照斯諾登的說法,直到今天,情報部門內部舉報者無一不遭到報復:“舉報者需要有一個堅強可靠的保護,可如今的法律根本就不會鼓勵人們站出來對錯誤的行為說不,這才是要改革的地方。”
在講完自己的故事后,克蘭想再去看看自己曾經工作過的地方。他開著自己那輛深紅色的沃爾沃汽車,駛向了波托馬克河的一處游艇停靠點。從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五角大樓、華盛頓紀念碑、白宮以及美國所有的權力機構。附近便是羅納德·里根機場,噴氣式飛機從那里起飛,呼嘯而過。克蘭遠遠地凝視著五角大樓,他本應該滿腹牢騷的,可他卻只言未提。
根據獨立調查機構特別檢察官辦公室給出的結論,克蘭案存在可疑之處,其主張觀點可能為真;美國司法部裁定重啟對克蘭案的調查。預計一年后,結果將公布,克蘭很可能將勝訴。到那時,克蘭打算退休在家,照顧孩子。
那么克蘭想過有朝一日重返五角大樓嗎?“當然,”克蘭如是說,不過他的表情顯得很錯愕,顯然他沒想到會有人這么問,“如果我回去了,就證明這個體制還是有用的。”
(摘自《看世界》2016年6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