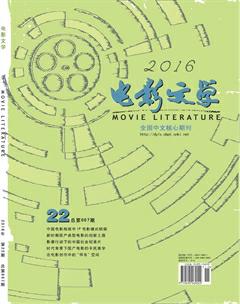米歇爾·馬利電影創作中的視點理論
謝敏 賴妍莉
[摘要]視點,作為導演的一種選擇,它可以任意性使用。然而,在這看似任意性選擇的背后,其實包含了導演自身對于整部影片的理解與闡釋。一部影片,故事的好壞在于敘述,而敘述本身要依賴于電影化視點的選取。無論是選取單一視點、多視點,還是多重視點,對于它們之間的差異性或綜合關系性,是需要導演認真來把握拿捏的,否則將直接影響到整部影片基調風格的定位,本文就此展開論述。
[關鍵詞]電影視點;米歇爾·馬利;敘事角度
電影中視點選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正如法國學者米歇爾·馬利所言,它不僅僅是作為攝影機的觀看角度而存在,更重要的是它是作為敘事、心理、文化等與觀眾緊密相關的觀影心理綜合作用的一個過程。其中,既包含影片本身的一個敘事角度,又包含觀眾觀看過程中的一個角度,通過這兩個角度才有了影片的視覺化效應和表現維度。
一、泛視點、單視點與多視點
電影的拍攝視點通常分為三大類:泛視點、單視點和多視點。它們隨著電影拍攝的需要、導演的需求而進行不同的選取。泛視點也被稱為全視點或第三人稱客觀視點,它往往帶有較強的客觀性。而單視點是指第一人稱主觀視點,帶有極強的主觀性。相比于前兩者,多視點更具有綜合性特點,它的這種綜合性是傾向于客觀化的。
單純從敘述方式來看,電影在表現過程中往往通過“講述”和“描述”進行,在運用的過程中兩者之間可以相互轉換,并且通過“講述”而進行的故事更富有傳統經典味道,而借由“描述”手段的影片更具現代主義風格。當然,兩者可以根據電影的需要而混合或交互性使用,尤其是混合型已成為當代電影敘事的典型手法。
為顯現出影片的“與眾不同”而采用泛視點的敘事手段,這種綜合性手法的運用會讓影片從整體看起來更飽滿、豐富。而單視點作為電影主觀性最強、最富表現力的電影手段之一,也常被運用到。單視點,這個也被稱為“內部視點化”的表現手法,會讓整部影片基調建立在一種富有神秘感的氛圍中。如同影片《湖上艷尸》中所表現的,影片讓觀眾產生了一種錯覺,覺得自己參與其中,從而將主觀敘事推向極致。然而,并非所有的電影人都會欣賞此類手法的運用,甚至有人會將此類主觀性過強的影片稱作“一個自戀傾向的陳述活動”,帶有極大的貶義性。因此,之后的影片又開始流行運用全主觀視點。
其實,在主觀單視點影片中曾出現過希區柯克這樣的大師。他的影片中主觀敘事成為主要的、突出的手法,并作為影片的重要敘事支點而存在。在這種技巧的運用下,影片鏡頭變得很純粹,純粹地直接進行著敘事。在希區柯克看來,此種手法的運用,更能表達出影片中所要表達的最本質的屬性層面,除此之外,別無它法。
電影的表現語言應該是純粹的,這是希區柯克所信奉的,也是他所表現的。影片《后窗》是他此類手法的典型代表作。影片表現一個坐輪椅的男人,利用長焦鏡頭對后窗鄰居進行偷窺。整部影片坐輪椅、無法行動自如的男人是其一,男人用長焦鏡頭進行偷窺是其二,男人偷窺后的反應是其三。影片用這種看似概念化的拍攝手法完成了整部故事的敘述。簡單的邏輯性也是希區柯克所尊崇的,并且他的這種主觀性手法也影響到了其他人,例如安東尼奧尼。這不僅說明了希區柯克影片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魅力,也充分肯定了此類拍攝手法的運用。
除此之外,美國新生代導演達倫·阿羅諾夫斯基同樣也運用此手法進行拍攝。在他所表現的影片中,為了能夠真實地再現一位吸毒癮君子犯癮、吸毒的過程,他采用了快節奏的主觀性敘事,讓觀眾真切地感受到了吸毒者為了毒品而抓狂、吸食后“飄飄欲仙”的主觀瞬間狀態,在這部影片中觀眾是觀看者,吸毒的主人公是演繹者,除此之外再無其他。影片中的主人公在自我感受著,世界的萬物仿佛都不再存在,那迷幻之后的沉迷和毒癮過后的真實,敲擊著每一位觀眾的心,現實得近乎冷酷。達倫·阿羅諾夫斯基運用主觀視點所表現出的吸毒者感覺非常到位,那一系列的快節奏鏡頭運用,注射、吞咽和吸食,所有這一切都在瞬間完成,仿佛這一切就是在和生命賽跑。而一旦毒癮過后,那時間的蔓延又會讓人感受到死人般冰冷。
當然,除了單一視點外,同樣有青睞于多視點手法運用多一些的。從奧遜·威爾斯的《公民凱恩》到黑澤明的《羅生門》,多視點成為他們鋪墊整部影片的基調。在他們看來,多視點手法更能體現出他們所要表達的東西,從鏡頭的變換、組織,到影片內容的最終呈現,豐富的視點變換更加體現出了影片主人公們那份復雜而糾結的心情。
二、看與被看的多重視點
電影是為了觀看,為了能夠吸引觀眾,表達出影片的獨特性。導演們選擇了各自不同的表現手法,于是也就有了單視點、多視點,甚至是多重視點的表現手法運用。多重視點相較于多視點而言,更帶有一種從屬關系,因此讓影片在邏輯表現上更具層次性。看與被看在這里既是簡單的邏輯關系,又是不簡單的觀看關系。客觀與主觀的雙重視點是一個方面,看與被看則是雙重或是多重。如同希區柯克的影片中那位坐輪椅的偷窺者,他作為故事的主觀敘事者是以單一的視點來進行敘述的。然而當影片在播放的過程中,作為觀看影片的觀眾而言,則是另一視點。這不僅激起了觀眾的好奇心,更激起了觀眾參與影片的真實性。這種多重視點的從屬關系會讓觀眾不自覺地陷入到影片的情境中。其實,作為一名導演,其應該意識到觀眾的這種心理,確切地說,這也是一種偷窺心理。正如導演大衛·林奇所言,“每一個人都具有偷窺的欲望”。然而,盡管事實的真相或許真如大衛·林奇所言,但這種偷窺性是要限度的,作為觀眾來講,過度的偷窺是他們所忌諱的,因為畢竟對于大多數觀眾而言,偷窺的欲望更像是帶有孩童般的好奇心理在作怪,卻不是獵殺者剖析解構身體時的那份殘忍心態。于是,能恰到好處地把握住觀眾這種偷窺心理的,就能夠讓影片大賣的同時還好評如潮。就如希區柯克。但也會有些導演誤入“歧途”,如邁克爾·鮑威爾,在他的影片中,偷窺已不再是簡單的一種觀看,更像是一種殘忍的獵殺。只不過這種獵殺在他的影片中更具真實性。影片的男主角喜歡殺女人,這些女人都是被他精心挑選過的,他在殺她們的過程中獲得了極大的快感與滿足,他喜歡看她們垂死掙扎,喜歡看她們尖叫與顫栗恐懼,而邁克爾·鮑威爾為了很好地拍攝該片,會躲到攝影機后面的陰影中去觀看,以此來推敲觀眾的偷窺心理與感受。
然而,他過于自信了,過于自信對于觀眾偷窺心理的把握。他用他真實的、略帶殘忍的拍攝手法,給觀眾心理帶來了極大的沖擊。尤其是在影片開端,赤裸裸地再現了男主人公殺死女人的過程。邁克爾·鮑威爾原本是想向觀眾打開觀看的大門,然而這份過于殘忍的赤裸表達完全驚嚇到了觀眾。因此,在希區柯克的影片與鮑威爾的《偷窺狂》幾乎在同一時間出現在大屏幕上時,最終的結果卻是差強人意的。一份是熱捧,一份是抨擊。希區柯克為此而成就了他的事業,而鮑威爾卻為此險些導致他導演生涯的斷送。因此我們說,觀眾作為多重視點之一,固然要考慮到他們的觀影心理,然而在注重觀影心理的同時,更應注重一種限度性的權衡,否則一切皆有可能。
在影片的表現手段中,主觀與客觀雙重視點可以在導演那里自由運用,來回轉換,而這種變換的自由性也是作為現代主義與后現代性主義電影的慣用手法來進行使用的。這種自由性讓導演們更加能夠游刃有余地進行表現,表現影片的多變、表現影片的曖昧,所有的敘述語言不再是一個聲音,所有的敘述者不再是簡單的重疊,在電影的表現中一切都沒有“一定之規”。作為電影藝術而言,最主要的敘事者也是電影本身所具有的敘述視角,而次要的敘事者即是影片自身的影像視點,對于它們在影片中所起到的作用性很難并置來論,但影片最終依賴影像視點來進行最終的傳達表現卻是不可否認的。
三、視點的轉換
電影中的泛視點、單視點和多視點注定了觀眾的觀看模式,也直接影響了影片與觀眾間的交流。其實,不論是雙向性交流,還是單向性觀看,電影最終所要掌控的是對鏡頭語言的把握。作為一部經典影片,它的經典性往往會借由鏡頭語言的“看”與“被看”的“接縫關系”來填充,當敘事和影像形成一種對視關系時,這種關系性直接決定了“看”與“被看”的緊密性。于是,影片中的鏡頭語言更豐富了,影片的表現維度也同樣更多了。
正如默片喜劇大師巴斯特·基頓,經常會將影片中的影像關系通過影片中的一個人物而將整部影片故事抽離出來,就像是在告訴觀眾這是一部影外之影,例如,在他的一部影片中,電影放映員夏洛克幻想自己是位大偵探,于是在放映影片的過程中他產生了幻覺,這幻覺真的讓他進入到影片之中,并由此開始了他夢寐以求的偵探之旅,并最終俘獲了女主角的芳心。對于觀看影片的觀眾而言,電影放映員夏洛克和他們一樣,處在影片之外。而當夏洛克最終實現了自己的夢想而真的進入到觀眾所看到的影像世界時,觀眾與夏洛克從精神層面而言已經融為一體。他們之間在不知不覺中已經產生了一種共鳴,這就是一種互動交流性,有了這種交流,才將銀幕外與銀幕內兩個毫不相關的世界縫合到一起。
類似于這樣的影片還有伍迪·艾倫的作品,他同樣會采用影中之影的表現手法,只不過這次不是銀幕中的男主角進入到電影之內,而是電影內的男主角走出來與銀幕中的女角色大談愛情。影片特寫了男主角走出電影凝視女主角的那一刻,觀眾在這時會產生錯覺,認為這個男人所凝視的是自己,這種直接性交流在觀眾面前產生了,觀眾在這樣一種雙向交流中獲得了心理上的滿足,滿足于自身在觀影過程中的身臨其境,也滿足于電影帶給他們另一別樣的心理體驗。
在諸如此類的眾多影片中,以反其道而行之的縫合手法更具代表性。正如彼得·威爾的影片《楚門的世界》。影片中的男主人公從小到大都是作為一個影像人物而存活,只不過這一切的一切他都沒有意識到。而當他真正發現事實真相時,觀眾的心會被不自覺地觸碰一下,因為他們和影片的男主角一樣,也沉迷于影片中所塑造的人生,觀眾就是楚門,楚門在這時也可作為一名觀眾。他們的交流就在楚門發現事實真相的那一刻開始了。觀眾與楚門一樣,總是自以為是地認為自己早已認清這個世界,認清了我們的人生,認清了所有與我們有關的或無關的一切,于是開始變得麻木不仁。可當意識到世界的廣闊與自身的渺小時,那厚厚的一紙屏幕又往往禁錮了我們的心,而不是我們的腳步。影片也在這有意或無意間顯現出與觀眾之間的交流、對視,每當這時,真實與虛幻就變得不再重要了,影片與觀眾的關系由此變得曖昧起來。
四、結語
縱觀世界電影發展史上這些具有深遠影響性的導演大咖,他們在運用敘事手法方面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或偏愛。從敘事的視角到鏡頭語言的變換,單一視點、多視點及多重視點,都可作為任意選取的砝碼來表現出自身的審美特色及個性。其實,任何一部影片都有它獨特的含義性隱藏其中,而觀眾所要挖掘的過程只不過有的費力而有的毫不費力罷了。正如美國學者布魯斯·卡溫所言,對于電影故事的訴說,每位導演都有他的權利所在。這不僅體現出了一名導演的藝術造詣,更體現出了一名導演的審美品位,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了影片本身的形式意義。因此,視點的選擇對一部影片而言是至關重要的,也是功不可沒的,有了契合主題的視點表現,才會有精彩的影片呈現,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參考文獻]
[1] 游飛.觀看與呈現:論電影化的視點[J].當代電影,2009(11).
[2] 封洪.視點與電影敘事——一種敘事學理論的探討[J].當代電影,2014(05).
[3] 林黎勝.“視點鏡頭”電影敘事的立足點[J].電影藝術,2015(02).
[4] 李顯杰,修倜.敘述人·人稱·視點——電影敘事中的主體策略[J].電影藝術,2006(03).
[5] 昊冬.論電影構思中的視點問題[J].文藝研究,2012(06).
[作者簡介] 謝敏(1973—),女,江西贛州人,碩士,贛南師范大學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英語語言文學。賴妍莉(1982—),女,江西贛州人,碩士,贛南師范大學講師。主要研究方向:英語語言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