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打或誤入
從來沒想過,有一天會寫歌詞。以為寫歌詞是件很簡單的事情,一首歌就那么幾句十句,難以展示才情的寬廣和厚度,更不能讓自己酣暢淋漓。
待試過一次才發現,諸如攝影、國畫與歌詞創作之類,創作過程看似簡單,實則是一個創作者畢生才情、學識和修養的集中展現。要寫好一首歌詞,比寫好一篇散文還要難。
第一次寫歌是在2014年,兄長陸翼洲請我寫一首歌,由他請省內著名作曲家譜曲。翼洲兄搞建筑,從商,但不改當年的文人情懷,曾給本地《沙地》文學雜志予好多年的支持。據說他正轉而投資文化。他應該知道,我的本行是小說和散文,推辭了好幾回,他執意要我寫,盛情難卻,于是打腫臉充胖子。促使我最終答應下來的,還有盲目的自信。我曾寫過多年詩歌,雖不成器,到底還有些底子;再說這些年從未丟過筆桿,上百萬字的小說、散文都沒覺得厭倦困難,寫那么幾句十句歌詞,也許不是什么難題。等到真正動筆才發現,不是那么回事,寫出第一句“鮮花萬盞 / 點亮秀美的春天”,就沒詞了。
為此,我好長一段時間懷疑自己是不是江郎才盡了,很委屈,很窩囊。所幸手頭的小說和散文還在正常寫著,否則屬文的自信心早坍塌了一大半。
就在這時候,南通文聯組織一次題為“江海尋夢”的大型詩音畫采風匯報演出,老副主席高龍民選用了我創作第一個不成功歌詞之后、為驗證自己智力是否正常而創作的第二首歌詞——那之后的第一首我后邊要說。他請頗具個性的黎立作曲。演出開始之前,我非常忐忑。演出的時候我讓自己的大腦同時兼具海綿和裁判的功能,沒想到,效果出乎我預料。事后回想起來,如有天助,如果不是高主席發現歌詞中那幾句亮眼的句子、如果不是黎立老師的歌譜“挽救”了那首歌詞,如果不是那位我至今叫不上名字的歌手的完美演繹,我可能終生不會再寫第三首歌。龍民前輩是我“歪打或誤入”的導師。
借著高龍民副主席給我的那點信心,我突發奇想,決定在我即將出版的長篇小說《風樂桃花》里搞幾個插曲。我把這種想法跟該書編輯郝鵬溝通,他說這是千古未有的事情,決定跟我一起冒險嘗試一次。畢竟是自己的小說,就像在自己的地盤上撒野那樣,思路順暢,沒遇到任何障礙,一口氣寫了四首,童謠、搖滾、流行和古風,各占一首。全部交給徐東老師。人家說我在下賭注,一個月時間,四種風格,這是安心讓徐東發瘋的節奏。說實話,我真把賭注壓在徐東老師身上了,而且擔心他的思路受到故事的鉗制,決定在四首歌出來之前,不給他看那部長篇小說。
那天我正準備出門上他那里送歌詞,外面正下著雨。徐東像看了我的心思那樣,似乎也要賭一把自己的才情,讓我把歌詞電郵給他,不跟我見面。春天的雨本來就冷、本來就臟,稀稀拉拉,軟不拉幾,十分的興致都會被拉低成七分。我從樓口屋檐下收了傘上樓,身上一滴雨水都沒有,卻感覺連褲腰帶都濕透了。
放著徐東譜曲的話題暫時不說,先回答大家的疑問:本身無意于寫歌詞,卻一口氣寫了四首,難不成是小菜里的鹽都被我李某人吃成了智慧丹?
我在學習。從第一首寫進死胡同開始,我連續買好多本有關歌詞創作和歌詞藝術的書來讀。有人會說,寫小說的人鉆研歌詞創作,不是不務正業,也是異想天開。老實說,我還沒高尚到寫個殺人的小說也去“體驗生活”——殺個人試試的地步,當時的想法很單純,多讀一本書不會死人。尤其對一個小說作家,天文地理,打卦算命,啥都應該了解一點。歌詞跟詩歌那樣接近,跟小說和散文都是沒出五服的近親,于小說散文的間隙,只要有了靈感,寫一兩首歌詞,既是調劑,也是生活的情趣。
人往往這樣,假如被動學習,比如你家兒子不喜歡語文,一卡車的小樹棍全爛在那小東西屁股上,不過是徒增父子雙方的失望和失敗感而已。要是正好感興趣,正好碰到了許多亟待解決的難題,比如我,拿到音樂書籍,立即成了加強版的、“如饑似渴”的學生,無數疑問就像小孩吹向天空的泡泡,指頭一戳,就破了。多年的小說、散文創作,為我進行歌詞創作奠定了比較厚實的基礎,理解起來自然容易一些,透徹一些。
《風樂桃花》上的四首歌,寫于我讀了那一批音樂書籍之后。
一個月之后,徐東老師打我電話,讓我抽空上他那里去一下。那天仍然下著雨,我卻真的不想去,希望他在電話里告訴我結果。出門的時候,我覺得不帶傘更合適,萬一他跟我說他對這四個歌詞不感興趣,找不到切入口,無法下手,回來時淋一場雨比較方便。
徐東音樂工作室里只有他一個人,天冷,開了暖空調,開了空調還是冷。來的路上落到身上的雨水穿透衣服,正向我的皮膚緩慢地狂奔。我跟徐東多年前就認識,可惜無緣深交,到那時候還算不得朋友。我不曉得他對我感覺如何,反正我有些拘謹。
“李老師,我現在很忐忑。”徐東很誠懇,一雙睿智的眼睛看著我,頭頂上的燈光打在他剃得光亮的腦袋上,在他腦袋后面折射出一圈隱約的佛光,讓我暫時放下拘謹,油然而生幾許親切和親近。不待我說話,他又說:“我生怕把你的歌詞搞砸了,所以今天先請你聽第一首。看看符不符合你和你那部小說的本意,要是符合,我們繼續做下面三首;要是不符合,立馬調路頭、換方向,一切都還來得及。”話在理,卻足見其誠懇和謙虛。我意識到,我們的友誼開始了。
四首插曲像四座姿態各異、瑰麗秀美的山峰,橫空出世,令人耳目一新。所有試聽過的人都說,這是聽了還想讓人聽的歌曲,這全賴徐東作曲之功。編輯聽了之后,很興奮,請人做成了二維碼,印在小說的后勒口上。讀者只要用手機微信的“掃一掃”功能,就能聽到四首歌曲。汕頭大學的曾令霞教授聽后,發了一條微信感慨道:“二維碼是小說中的聲音通道,或許還可以通向視頻。十幾年前討論未來小說的樣子,老師說那時的小說會不會寫著寫著畫一符號,插入一段音樂,或者聲音,將文字具體化實像化?看來真的要實現了,前提是手機等新媒介的技術參與。這是《風樂桃花》帶給我的感受。”
這四首歌的編曲、配器全是徐東為主體的團隊完成的。徐東的團隊既不做官也不經商,主要從事音樂輔導,相當于處在社會底層。正是這樣一種接地氣的狀態,使他們具有俯瞰樂壇的胸懷和勇氣,他們的視野不是啟東的,也不是江蘇的,而是整個樂壇。從這四首歌的氣質能看出,闊大,開放,坦率,真誠,猶如曠野上的風、草原上的馬,是自由的,而不是拘束的;是純粹的,而沒有任何功利。在一次晚會上,《那一年的星空下》讓多少在場的觀眾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聽風吹》又讓多少人懷想起自己并不遙遠、永不再來的青春。
那一天,從徐東的工作室出來,我一頭鉆進瀟瀟雨中。感覺人如草木,有時需要雨水洗涮一下枝葉上的灰塵和污垢,需要澆灌和滋潤。我在雨中開懷大笑。
回過頭來說我那第二首歌詞,歌名《生命原鄉》。寫于散文《日漸淺淡的地理鄉愁》之后,故鄉在游子心中越來越符號化,越來越沒有具體的內容,今天的故鄉能為游子所熟知的事物越來越少,多少人的故鄉在行政村社的合并及其動遷開發過程中,不復存在。可是,只要父母親在那里,故鄉就永遠存在。我覺得有必要寫一首歌來作為那篇文章的補充。第一稿是隨手寫下,只有一段,交由文化館楊曉燚館長譜曲。小樣出來,感覺有必要再寫一段,否則空了。我考慮了好幾天,卻一點也找不到當初寫第一段時的感覺,好不容易寫下第二段,總感覺不太順。
歌曲是個神奇的東西,有時候非常優美動聽的歌詞,可能砸在作曲家的手上;有時候尚存缺憾的歌詞,卻被作曲家的曲給挽救和彌補了。當《生命原鄉》唱響在舞臺上的時候,已經聽不出第二段的缺憾了。
假如《生命原鄉》只是作為一般舞臺演出節目,演出完畢也就過去了,卻偏偏忝列重點扶持歌曲。據說數百首里選了五首,壓力一下就來了。歌詞的豐富程度,決定一首歌的品位。到這時候我特別想把這首歌重新寫過,先不說將來能有什么樣的結果,至少要能在更大的平臺上拿得出手。磨蹭了好長時間,跟車輛掛不上相應的檔位、收音機調不到相應的頻道那樣,努力了好多次,就是找不到寫第一段時的感覺,一直下不了手。
2016年9月2號,季節已是秋天,午后還有些熱。南通文聯召開重點扶持歌曲評審會。像這樣的評審會,對于創作者來說,意見和建議比表揚和肯定重要。當然有的人是不能接受的。每一個造詣已經成熟的藝術家,都有自己的堅持,都有自己的藝術理想和追求,輕易不會被別人的意見和建議改變。像我這樣歪打或者誤入的詞作新人,反倒沒有過去榮譽和名聲的羈絆。事實證明,我的判斷是正確的。著名音樂人吳幼益老師說,《生命原鄉》是一首表現鄉愁的有新意的歌詞,但第二段不夠順暢,“鄉愁往哪兒落腳?不能空掉。”就是這句話,讓我突然想起寫第一段時的心情,意識到我應該用具有畫面感的形象來抒發對故鄉的情感,這種情感既是個體的,也是大家的。會議結束的時候,李中慧副主席專門找到我,給了我一首讓她每一次練習都會熱淚盈眶的歌曲做參考。那是一首我從未聽過的歌,她只唱了幾句,我已經深受感染。
從那時候到夜里,因為幾位老師的點撥,我的感覺像茶杯中的茶葉,在水中一點一點復蘇,一點一點展開。入睡之前我已經有了主張,沒有寫下來。我賭一把自己日漸衰退的記憶,我要第二天早上再寫,如果第二天早上什么都記不得了,或者記不全,說明我的主張還不夠堅定,反之則可以。第二天早上五點過醒來,伏在電腦前面寫完,卻忘了保存。夫人在廚房里做早飯,聽說我找不到剛才寫的東西了,系著圍裙跑出來作同情狀圍觀。我老早蒙了:老夫老妻的,你想看猴戲只管看,我表演得還不夠精彩!跑到衛生間把每天必須要洗的臉洗了,清醒許多,繼續回到電腦前面,打撈瞬間失去的文字。我用半個小時證明,剛才只是蒙了一下,一句話都沒忘記。
文章不厭千回改,歌詞是音樂文學,一樣值得改千回。我知道,這一稿肯定不是最后的定稿。不管是哪一首歌,我希望在作曲家小樣出來之后,請人視唱,根據視唱效果,同時對詞和曲做相應的調整。于詞和曲作者來說,旋律出來了,歌曲才會像一棵樹,哪里枝丫長多了,哪里還需要增補,一“耳”了然。
一首歌可以是一個世界,里面有遼闊和寬廣;一首歌也可以打開一個世界,打開眾多的心扉,打開眾多的精彩。不要小看任何一首歌,不要小看任何一種藝術。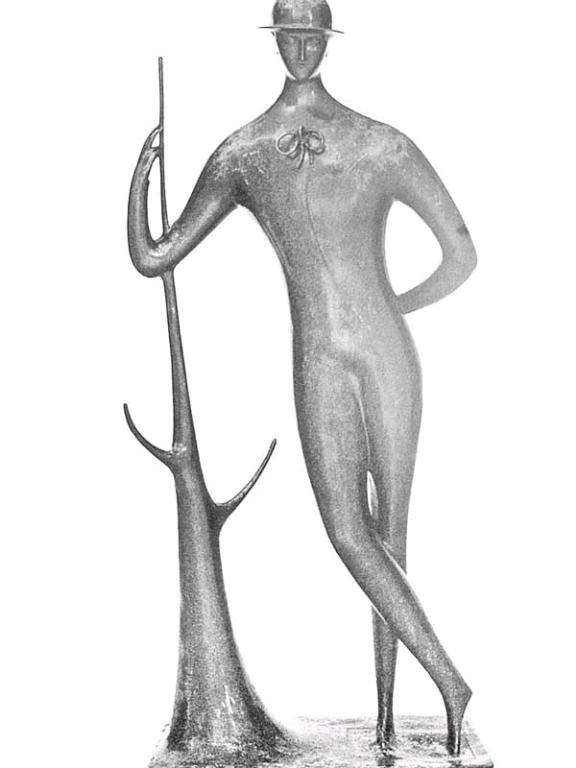
【作者簡介】李新勇,生于四川大涼山西昌,現居江蘇啟東。在《北京文學》《散文》《上海文學》《小說月報原創版》等刊物發表小說散文300余萬字,部分作品被《小說選刊》《中篇小說選刊》《中篇小說月報》等刊物轉載,入多種年度作品選。出版小說集《麗日紅塵》《風月》《某年某月某一天》、散文集《穿草鞋的風》《余棉有韻》《馬蹄上的歌謠》、長篇紀實文學《到江尾海頭去》、長篇小說《風樂桃花》等12部。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江蘇省作家協會理事、南通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啟東市作家協會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