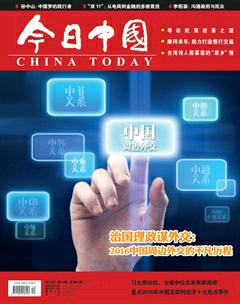中國人眼里的鮑勃·迪倫
文|蔣連華
中國人眼里的鮑勃·迪倫
文|蔣連華

鮑勃·迪倫
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文學評論家楊慶祥表示:鮑勃·迪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近幾年“諾獎”中他最滿意的一次,“瑞典文學院的那幫老評委們總算重新找到了‘諾獎’和文學的準則:文學必須是高度參與,高度社會化的藝術形式。
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落戶美國民謠歌手、詩人鮑勃·迪倫(Bob Dylan)可謂諸多個“沒想到”。此結果在中國文學界產生了巨大爭議,有人認為這是文學的創舉,也有人表示“眼鏡碎了,瞎頒!”而迪倫這個中國人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在中國人的音樂記憶中再次掀起狂潮。
“他是時間,也是世界”
瑞典時間2016年11月16日,鮑勃·迪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當天,中國的微博音樂界變成了狂歡的海洋,李健、汪峰、左小祖咒等音樂人均發布微博慶賀。歌手張楚表示,這事兒對音樂界來說是個鼓勵,特別是對中國音樂界。因為中國音樂在商業上的價值不夠,所以得到的榮譽也不夠。
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文學評論家楊慶祥表示:鮑勃·迪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近幾年“諾獎”中他最滿意的一次,“瑞典文學院的那幫老評委們總算重新找到了‘諾獎’和文學的準則:文學必須是高度參與,高度社會化的藝術形式,而不僅僅是修辭或者講故事。另外,請注意鮑·勃迪倫與1960年代的緊密關系。這也是他獲獎的一個重要因素。”
作家北村卻直言此次迪倫獲獎是“瞎頒”。他認為,鮑勃·迪倫獲獎,意味著新世紀以來文學邊界的消失得到了正統文學獎最高權威的認可。這是本體意義上的,也是現代性的終結。
出生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人,很多都是聽著迪倫的歌來認識搖滾民謠的。1983年,23歲的服裝設計師朱敏得到了一份特別的禮物。一個國外回來的朋友送給他幾盒磁帶,全是歐美當時大熱的流行音樂,其中包括有“搖滾女詩人”之稱的美國歌手帕蒂·史密斯的第一張專輯《馬群》,還有鮑勃·迪倫的《重訪61號公路》。一向喜歡音樂的他如獲至寶地拿回了家,盡管當時他并不知道鮑勃·迪倫是誰。
當鮑勃·迪倫的嗓音從音箱里飄出來時,朱敏被震住了。他拿起磁帶,認認真真地記住了這個歌手的名字。很快,他便知道了這個人在流行音樂史上的地位,也知道了這張專輯的意義。
《重訪61號公路》是迪倫在1965年發行的第一張搖滾專輯,也正因為這張專輯,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攻擊—歌迷們在演出現場大罵他是民謠的叛徒。這張專輯的第一首歌,便是在流行音樂史上聲名大噪的《像一顆滾石》。
“所有中國的搖滾樂,今天那些還拿著吉他在唱的人,無論大家承認與否,接受與否,鮑勃·迪倫或多或少都對我們有過影響。”崔健說,“有一個叫‘滾石’的樂隊,一本名為‘滾石’的雜志,臺灣有一個叫‘滾石’的唱片公司,包括后來大家很喜歡用的和‘stone’有關的名字,都是從他的歌里出來的。”
身為中國的搖滾教父,崔健曾被媒體認為是中國最接近鮑勃·迪倫的人,但他并不愿意做這個比較,“鮑勃·迪倫是一個傳奇。”
作家麥加表示,中國沒有鮑勃·迪倫這樣的人物,他請自以為像鮑勃·迪倫這樣的人別自作多情。“鮑勃·迪倫不單純是個詞人、音樂人,他是時間,也是世界。他屬于時間,屬于世界。”
獨立表達的歌手

崔健說:鮑勃·迪倫是一個傳奇
在中國大陸,迪倫最早是以文字而不是音樂的方式出現的。兩部大名鼎鼎的啟蒙大作——威廉·曼徹斯特的《光榮與夢想:1932—1972年美國社會實錄》和莫里斯·迪克斯坦的《伊甸園之門》鄭重介紹了迪倫。《伊甸園之門》有整整一章專講迪倫,看得嗷嗷待哺的中國青年干著急,聽不到歌,只能加倍把他想象成一個1960年代的革命尤物。終于聽到而不僅僅是讀到迪倫,要等到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那首《答案在空中飄揚》(Blowin’ in the Wind)。有人認為,迪倫在中國的最初乃至最大的貢獻,是通過這首他25歲之后就差不多不再唱的成名作普及了英語。
在很長一段時期里,鮑勃·迪倫的音樂在中國的流傳,都只能借助于一些音樂雜志的推崇和人們的口口相傳。“他很早就高高在上,年輕人都很尊重他。真正把布魯斯音樂帶到白人世界,推向全世界的,其中就有鮑勃·迪倫。”崔健說。
20世紀90年代初期,一種名為“打口磁帶”和“打口CD”的音像制品流入中國。當年像海綿一樣不斷吸收著音樂營養的那批樂迷們,后來有的成為中國搖滾的中堅分子,有的成為資深樂評人,有的依舊是純粹的音樂發燒友。但幾乎所有人,都聽過同一個名字—鮑勃·迪倫。凡是寫著鮑勃·迪倫名字的專輯,總是很好賣,有時候賣到50元人民幣的天價(當年這是一個不小的數字),也有人搶著要。
“每次到達一個新的城市,我第一個要找的,總是這個城市的打口碟市場。而在每個打口碟小攤,我總會要求老板把鮑勃·迪倫的所有唱片都翻出來,讓我慢慢挑。”一個叫涂涂的歌迷曾記錄他的每一次尋覓。
從最初對南方民謠的刻意模仿,到一把口琴殺出血路,再到成為抗議歌手領袖,卻在最高峰時拂袖而去,然后是插上電吉他被人狂噓,接著是急流勇退回歸田園,不斷地詩化、哲理化,到如今的老布魯斯姿態,迪倫無愧于“變色龍”的稱號。民謠、民謠搖滾、鄉村、藍草、福音、藍調……都被他隨心所欲地玩過。
反叛二字,在鮑勃·迪倫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但他拒絕人們把他視作大眾偶像、“時代良心”或“道德的裁判和布道者”等等。這些贊美甚至讓他覺得自己被“綁架”了。在一次頒獎禮上,他喝得醉醺醺地站起來,高聲吶喊:“我不分黑白,我不分左右,也不是什么政治詩人,更不是任何人的仆人,我最多只是一個獨立表達的歌手……”
真正的先鋒就是做自己

巴西藝術家美國街頭繪巨型壁畫,致敬民謠歌手鮑勃·迪倫
2011年4月6日,70歲的鮑勃·迪倫在北京工人體育館開唱,這是他第一次在中國演出。當日的工體座無虛席,很多媒體甚至用“朝圣”一詞來形容中國觀眾。張楚也觀看了這場演出,令他印象最為深刻的是迪倫的低調,“他在一個非常講究音樂張力的時代把大劇場布置成了酒吧,燈光也是那種感覺。沒想到他的個性這么樸素。”
對于中國樂迷來說,這是一次好好地重聽經典的機會。他們放下了那些小清新、小獨立,花上大把時間、上網搜集一摞子資料、看一堆注釋、觀摩幾出傳記電影,在論壇與人交流,諸如此類。在此過程中,他們的英文閱讀水平、吉他技巧、口琴技巧等都在大幅度提高。
“一個男人要走多少條路,才能將其稱作好漢。一只白鴿要飛越多少道海,才能在沙灘上入眠。炮彈要飛多久,才能將其永遠禁縛。答案在風中飄蕩……”鮑勃·迪倫的成名曲就是20世紀60年代創作的這首《答案在風中飄蕩》,很多人是聽著這首膾炙人口的美國民謠長大的。張楚坦言,在他自己的音樂創作中,還真沒有受過迪倫的影響,“他對我的影響體現在人生觀上。”張楚說,他欣賞迪倫面對曲折人生的態度,“他有著客觀認識自我的能力,我覺得他是個非常聰明的人。”
不是所有人都喜歡鮑勃·迪倫。“畢竟你要先理解美國社會,理解嬉皮文化,才能準確地去體會他的文化價值。年輕人聽的是現代工業的產物,都是重型的音樂。而民謠的東西,沒辦法去融入。”崔健說。
鮑勃·迪倫從來都不取悅誰,他一直堅持演出。從1988年起,迪倫開始了“永不落幕巡演”(Never Ending Tour),平均每年100場,迄今為止已在世界各地演出了2300多場。“這是一種最好的對話方式。”崔健說。
如今,在中國居然找不到一個鮑勃·迪倫的歌迷網站。他的歌迷們分散在各個行業和領域,低調冷靜。喜歡他的人幾乎都上了一些年紀,受過教育,換句話說,鮑勃·迪倫的歌迷的門檻比較高,知識分子居多。
“鮑勃·迪倫越是不代表誰,他的影響就越大,那些總是想代表時代的人,越無法獲得持續性的影響,那個時代過去了,他們就過去了。鮑勃·迪倫很低調,他一直在堅持做演出,從他的第一首歌到現在,這中間一脈相承的音樂形式,反而給了我們深遠的影響。”崔健說。
2003年,鮑勃·迪倫歷時3年在手動打字機上一鍵一鍵敲出了他的回憶錄《像一塊滾石》出版,最終將詩人和散文家的情懷表露無遺。該書進入《紐約時報》最佳暢銷書榜單長達19周之久,還被全球數十家著名媒體評選為“年度最佳圖書”。
書中,迪倫對自己被無限擴大為抗議、民權、嬉皮等60年代運動代言人表示不認同,甚至嘲諷。他是這么解讀自己的身份的:“無論我到哪里,我都是一個60年代的游吟詩人,一個搖滾民謠的遺跡,一個從逝去時代過來的詞語的匠人。我處在被文化遺忘的無底深淵之中。”
對于迪倫的獲獎,有人感到吃驚,《大家》文學雜志主編陳鵬說:“干嘛吃驚?他另類,反叛,浪漫,不合作,不流俗,不沖大眾而去,不為主流寫歌,甚至不為主流金屬搖滾、pop搖滾、朋克搖滾左右,他用干脆直接憂傷隱秘的詩句直指嬉皮時代的流浪之心……真正的先鋒派!就做自己。”
上海作家黃煜寧說:“其實老頭在名單上也已經好多年了,只是太多人把這個當笑話看了。很多搖滾、民謠甚至說唱的歌詞都是絕妙的、冒著活氣的、隨時可以從舌尖上綻放的現代詩,嗯,比很多詩更像詩。瑞典的老頭們能認識到這一點,說明他們還是與時俱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