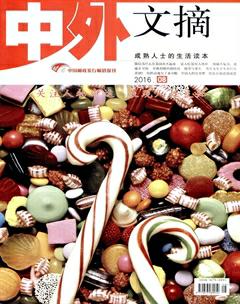韓國(guó)人的家庭意識(shí)為何全球第一
李圭泰

家庭意識(shí)全球第一
韓國(guó)語(yǔ)中有“人間”一詞,意指“人”。從詞的結(jié)構(gòu)上來(lái)看,作為主體的人,要和某一客體之間形成關(guān)系時(shí),才能成為“人”。
“我”是不能獨(dú)立存在的,只能存在于與異性、與家庭、與民族、與共同體、與國(guó)家等眾多客體的關(guān)系中。
民族不同,與某一客體的關(guān)系就會(huì)有親疏遠(yuǎn)近之分。例如,有的民族看重與父親的關(guān)系,而有的民族則更看重與共同體的關(guān)系。
因此,有的民族因其風(fēng)俗和先天條件,家庭優(yōu)先于國(guó)家,而有的則是民族優(yōu)先于家庭。
那么,我們所屬的朝鮮民族最看重與哪一客體之間的關(guān)系呢?重視的程度又如何呢?這個(gè)問(wèn)題需要探討一下。因?yàn)檫@是了解韓國(guó)人、了解歷史的最核心、最關(guān)鍵的問(wèn)題。
西方文化發(fā)源地之一的古希臘,那里的人最重視城邦這一客體。因?yàn)樵诘乩砩纤麄兂3C媾R海盜和受侵略的危險(xiǎn),他們的生死存亡與城邦的存亡密切相關(guān)。
較之家庭,沙漠民族更重視部族。因?yàn)橛文辽顭o(wú)法以家庭為單位,而必須以部族為單位遷徙。以家庭這一規(guī)模,是無(wú)法對(duì)抗沙漠中惡劣的自然條件的,也無(wú)法抵御侵略者。
伊斯蘭民族之所以對(duì)猶太人部族執(zhí)著地抱有成見(jiàn),正因?yàn)樗麄兪巧钤谏衬貐^(qū)的游牧民的緣故。
穿越絲綢之路的過(guò)程中,我曾見(jiàn)到并采訪過(guò)阿富汗的庫(kù)奇族牧民。在他們身上,找不到一絲一毫所謂阿富汗國(guó)民的國(guó)家意識(shí)。他們四處游牧,全然不顧國(guó)民的一切義務(wù)和權(quán)利。他們從不受阿富汗法律的制約,而只執(zhí)著于庫(kù)奇族的律法。他們會(huì)獻(xiàn)上自己的兒子,作為祭祀儀式上的祭物。他們認(rèn)為這是光榮的事情,并親手將自己的子女送上犧牲的祭壇。在他們的價(jià)值觀上,國(guó)家、家庭之重,較之部族之重,簡(jiǎn)直是九牛一毫。
韓國(guó)又怎樣呢?家庭之于韓國(guó)人,可謂是重之又重。這雖然是處于季風(fēng)氣候民族的共同特點(diǎn),但韓國(guó)的家庭中心主義較日本和中國(guó)要更加徹底。
韓國(guó)人不會(huì)為了家庭之外的共同體而拋卻私心,但在家庭之中,卻懂得犧牲一己之私,這一民族性也許是全世界中最為極端的。
歷史上,為了父母、為了家庭的名譽(yù)而不惜犧牲生命的事例比比皆是,且這種犧牲被歷史評(píng)價(jià)為最高貴的犧牲。
獨(dú)居的家也是“我們家”
看似兄弟倆的兩個(gè)小孩在玩放風(fēng)箏。問(wèn)小的那個(gè):“這風(fēng)箏是你的嗎?”小的搖頭說(shuō)不是。又問(wèn)大的:“那這風(fēng)箏是你的吧?”大的同樣搖頭。再問(wèn):“那這風(fēng)箏是誰(shuí)的?”兩個(gè)小孩異口同聲地回答說(shuō):“是我們的。”這個(gè)“我們”,是全體的“我們”,不僅包括弟兄倆,因?yàn)榘职钟袝r(shí)也放風(fēng)箏,所以也包括爸爸在內(nèi)。
由此可見(jiàn),在風(fēng)箏的歸屬上,
“我”被“我們”埋沒(méi)了。不僅僅是作為玩具的風(fēng)箏,所有的什物及有價(jià)值的東西都是如此,所謂“我的”,所謂個(gè)人所有這一概念,韓國(guó)人是極度缺乏的。個(gè)體埋沒(méi)于集體,這是韓國(guó)人很突出的意識(shí)之一。
日本人、中國(guó)人抑或西方人,在指稱父母、家庭,以及自己所屬的學(xué)校、社區(qū)、單位、團(tuán)體、民族、國(guó)家時(shí),不使用表示復(fù)數(shù)的“我們”,而說(shuō)“我的媽媽”“我的家”“我的學(xué)校”“我的國(guó)家”,唯獨(dú)韓國(guó)人說(shuō)“我們媽媽”“我們家”“我們學(xué)校”“我們國(guó)家”。
“我們”這床溫暖棉被下蓋著的,是韓國(guó)人的赤子之心。寒冷的冬天,大家把腳放進(jìn)炕頭的被子里,形成了共同體的紐帶感。在流浪乞討的饑寒交迫中,興夫的老婆對(duì)全家人說(shuō),咱們一家二十七口,還是各奔東西、各自為生吧。興夫卻說(shuō):“要沒(méi)有二十七口子背上的暖和氣,就該凍死了。”興夫的話是對(duì)“我們”這一紐帶感的準(zhǔn)確詮釋。
靠著抱團(tuán)取暖,我們才能夠在數(shù)千年間歷經(jīng)窮困、饑餓、欺侮、亡國(guó),堅(jiān)強(qiáng)地活下來(lái)。
其實(shí),西方的“我的家”和韓國(guó)的“我們家”在結(jié)構(gòu)上是不同的。被家務(wù)事搞得筋疲力盡的主婦有個(gè)共同的愿望,那就是鎖上門(mén)好好休息一天。主婦們的愿望,正說(shuō)明了韓國(guó)的房屋結(jié)構(gòu)特點(diǎn)——沒(méi)有可以將自己隔絕開(kāi)來(lái)的空間,抵制個(gè)人的私密性。
換言之,西方的房屋在結(jié)構(gòu)上有著隔音的厚墻和房間門(mén),房間門(mén)上有鎖,可以提供徹底隔絕的自我空間,而這在韓國(guó)的房屋是不允許的。韓國(guó)的房屋是所有家庭成員的,是“我們”的空間。當(dāng)然,房間是隔開(kāi)的,但這種隔斷不同于西式房屋的物理上的隔斷,而不過(guò)是精神上的隔斷罷了,就好像是畫(huà)出一道分界線。韓國(guó)的房屋采用紙糊的橫推門(mén)或隔扇門(mén),任何時(shí)候都可以進(jìn)進(jìn)出出,聽(tīng)得到聲音,也可以隨時(shí)探望。這種精神上的隔斷只針對(duì)尊重這種隔斷的人,因此即便屋里只有一人,旁邊的房間空著,也總是感覺(jué)到旁邊會(huì)有人在,精神上不可能獨(dú)自存在。
“我”埋沒(méi)于“我們”之中
家是“我們”的共同空間,由此形成了韓國(guó)人特有的“干咳文化”。這種咳嗽不是生理上的自然現(xiàn)象,而是為告知自己的存在而發(fā)出的人為的咳嗽,韓國(guó)人對(duì)此駕輕就熟。跨進(jìn)屋來(lái)時(shí)干咳,表示“我進(jìn)來(lái)了”;在屋子里干咳,則表示“我在里面”。移至某一空間時(shí),一定要先干咳一下,發(fā)出信號(hào)。韓國(guó)人之所以有“干咳文化”,是因?yàn)榭臻g不是自己獨(dú)有,而是“我們”大家共有。不僅是干咳,韓國(guó)人常常自言自語(yǔ)也是出自這一緣故。
例如,明明沒(méi)有聽(tīng)眾,也會(huì)說(shuō)——“天氣怎么搞的”“風(fēng)真冷”,或狗遭數(shù)落雞遭攆;明明沒(méi)必要問(wèn),也一定要問(wèn)上一句——“喂豬了沒(méi)”“衣服干了沒(méi)”“爺爺來(lái)了沒(méi)”。這并不是為了傳達(dá)話語(yǔ)本身所包含的內(nèi)容,而是一種進(jìn)入共有空間的信號(hào),和干咳的性質(zhì)相同。
因?yàn)轫n國(guó)人的家是“我們家”,所以先得收發(fā)“我們存在”的信號(hào)。縱然有門(mén)相隔,也必須要有一雙透視的眼睛,用心靈之眼關(guān)注著旁邊房間里有誰(shuí),以及正在做什么。因此,韓國(guó)人用眼說(shuō)話要多于用嘴。
食文化也不例外,“我”同樣埋沒(méi)于“我們”之中。西方人把大容器中共有的食物倒在各人的小盤(pán)子里,把食物變成自己的,然后再吃。而韓國(guó)人則是先將食物上桌,大家一起夾著吃。因此,擺到桌上的食物,從湯水到醬料都是“我們”的。
祭拜完后,將祭拜的食物倒入盆中,做成拌飯,你一勺我一筷地吃掉,這種飲食習(xí)慣強(qiáng)化了彼此之間的紐帶感,也是韓國(guó)所特有。這種拌飯里一定要有供桌上供奉過(guò)的食物,通過(guò)這一媒介,把大家族的“我們”聯(lián)系起來(lái),不僅僅是現(xiàn)在活著的后孫們,還包括已經(jīng)去世的祖先。
孩提時(shí),如果沒(méi)等到吃祭祀拌飯就沉沉睡去,那么母親就會(huì)把飯留下,待第二天早上再給我們吃。母親這么做,飽含著母性的眷顧愛(ài)憐,她不想讓年幼的子女游離在大家族的“我們”之外。
以前的小孩子,不會(huì)隨隨便便摘自家院里的果子吃,哪怕是一個(gè)柿子,一顆栗子,或一根黃瓜。如果摘了吃,就會(huì)有脫離“我們”的犯罪感,因?yàn)檎氖恰拔覀儭钡臇|西。新果和新谷要先供奉到祖先的祠堂,然后大家族的“我們”才能吃。
(摘自《新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