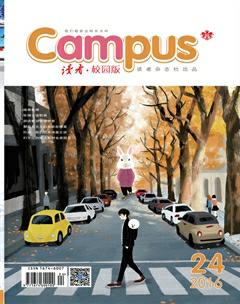畢業
喻麗清
我上中學時,校門外有一家小吃店,老板娘胖胖的,我們給她起綽號叫“瑪麗蓮·夢露”。
“瑪麗蓮·夢露”做的蔥油餅非常好吃,又香又油又燙。但是如果現在請我吃,我真的不知道還敢不敢吃。因為我老是記得她那口黑不溜秋的大油鍋,旁邊還有一桶洗碗洗筷還洗抹布的水,更別提她用來包東西的那些舊報紙了。無論包子、饅頭還是蔥油餅,她都是撕下半張報紙,卷個錐狀的圓筒,把食物擱在里頭遞給顧客。有人吃饅頭要剝皮,我想大概就是不能忍受那些印在饅頭皮上的油墨吧。
后來讀到一本書,里面說古時候在埃及,巫師為增加智慧,用酒把寫在紙上的字洗下來喝下肚去,我立即想到“瑪麗蓮·夢露”的“特種包裝紙”。說不定我就是從她那兒吃下了很多報紙上的字才能畢業的。
我們中學畢業那會兒好像并沒有什么“典禮”。初中時,就在學校的操場上舉行了一個營火晚會,營火還是老師幫我們點著的。只記得在夜色中有人跳草裙舞,有人跳山地舞,如此而已。雖然也聊勝于無,但是心里還是很氣校長不準我們去畢業旅行。校長當時說:“等你們高中畢業時再去旅行慶祝吧。”言下之意是,初中畢業沒什么好慶祝的。其實在我們心中也并無慶祝之意,即使高中畢業又怎么樣呢?我們不過是舍不得跟同學告別而已。為著心中的不舍,我們想努力爭取一次畢業旅行,以便在分手之際留下一些課堂之外的記憶,可惜老師們除了眼前的聯考什么也顧不上了。到了高中,校長果然又沒批準我們的畢業旅行。到現在,我只記得大家分手時,互相交換相片,然后寫幾句名人名言在紀念冊上。誰也沒有料到出了校門,世界忽然變得太大,大得會使我們逐漸迷失。對于真正有理想、有抱負的人而言,畢業是開始;但對庸人而言,畢業也就是一種結束。
如果說社會是一部大書,那么中學不過是一本字典。中學之所以單純,是因為一切只為了讀書。如果進了社會以后也能不為那復雜的生活分心的話,相信我們也還能享有那種單純之樂,可惜字典畢竟不是書。讀書是一種積累與貫通的功夫,其實沒有畢業的時候,尤其寫作這一行,無所謂開學,更無所謂畢業了。
也許校長是對的,畢業有什么好慶祝的,不如去看“瑪麗蓮·夢露”如何煎她的蔥油餅:在我們的記憶中,那可口的滋味,無須智慧,也可以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