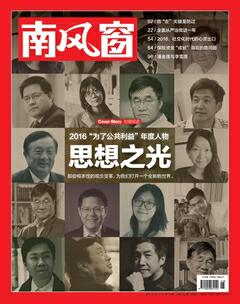崇福寺彩塑:態濃意遠淑且真
宿小白
“功德佛事需用壯觀。”佛教藝術極少以簡潔和克制為重要理念,相反,佛教塑像和供養物往往通過極端壯觀的景象來喚起人們的敬畏和虔誠。
位于山西省朔州城區中心的崇福寺,創建于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為鄂國公尉遲敬德奉敕建造。金皇統三年(公元1143年),又增建彌陀殿、觀音殿,寺廟規模更為宏大。遼金等少數民族政權極為崇信佛教,修建大量寺院弘揚佛法,大概是因為作為異族他們的統治不容于被征服地區的社會傳統和宗教傳統,推崇佛法有社會和政治整合的意味。
彌陀殿為崇福寺的主殿,亦是全寺文物的精華所在。從洞開著的大門里,可見殿內供奉的是“西方三圣”: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和大勢至菩薩,呈現的是西方極樂世界的圖景。根據佛經描述,“極樂國土,有七寶池,八功德水,池底純以金沙布地。四邊階道,金銀、琉璃、玻璃合成。上有樓閣,亦以金銀、琉璃、玻璃、赤珠、瑪瑙而嚴飾之。池中蓮花大如車輪,微妙香潔。”
這樣一個華麗的世界,如今就呈現在我的眼前:主佛端坐于束腰須彌式基座之上,寬胸厚背,面相豐盈,鼻梁凸起,呈端莊慈祥神態,較唐代塑像略短而圓潤,有宋金塑像豐腴柔美之姿;佛像后面是以青色為主色調的華麗背光,由飛天以及迦陵頻伽組成,衣飾華美的脅侍菩薩分立兩側,兩位怒目金剛力士圍擁左右,一派和諧完滿莊嚴的境界。
這些佛像異常精美,雖由凡夫俗子所作,但卻代表了信眾心目中對佛的完美想象,仿佛來自彼岸,是凈土世界在人間的顯現,給人以出離之感。古代的雕刻代表了和我們今天所熟悉的雕塑技術完全不同的一種創造,是特別精神性的一種活動。
主佛威嚴令人敬慕,而四尊脅侍菩薩華美瑰麗的風貌更令人傾倒。她們頭戴華冠,身披瓔珞,鏤空背光聳立肩頭宛如孔雀開屏,衣紋自然流暢,身軀飽滿圓潤,肌膚柔麗光滑好像具有彈性,初塑時身上敷描的濃淡彩繪的顏色雖歷經千年依然鮮亮如初。這樣的塑像,讓我想起了杜甫那首贊美長安美人的名句—“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見,翠微盍葉垂鬢唇。背后何所見,珠壓腰衱穩稱身。”剎那間,我被這組絕妙佳作完全征服了。
面容的表現是雕刻的生命。四尊菩薩面相俊俏雅致,長眉彎曲如新月,眼神微微向下注視,嘴角呈現含蓄的微笑,舉止嫻靜優雅,表現出極不平凡的內心世界。李澤厚認為,古代藝術經歷了從注重外在美、動態美到注重內在的精神美、靜態美的轉變,表現在雕塑藝術上,則是越來越注重表現人的精神氣質、情感和內在性格,在意象上由鏤金錯彩轉至自然平淡的追求,由五彩繽紛的動的氣勢轉為靜的意味。
仔細觀察彌陀殿內的彩塑,可以發現,其造像藝術恰好處于這樣一個藝術風格轉換的關鍵點上:脅侍菩薩身姿微曲、衣紋飄蕩,雕飾繁復華麗,力士脖頸上方挺立的彷佛正在燃燒的橢圓形火焰背光,呈現出一種永不休止的動感姿態;同時菩薩的形態具有了高度的寫實性,清麗明晰、親切和爽的面容,極具人性的風儀,嫻靜、善良、恭順的性格刻畫得淋漓盡致,在動靜、外在與內在之間取得了微妙的平衡。
由此也產生一個困惑,為何反物質主義的佛教,其營造的宮殿卻是如此富麗堂皇,塑像如此繁復華麗,似乎有悖于佛教徒苦行的理想。“功德佛事需用壯觀。”佛教藝術極少以簡潔和克制為重要理念,相反,佛教塑像和供養物往往通過極端壯觀的景象來喚起人們的敬畏和虔誠。柯嘉豪在《佛教對中國物質文化的影響》一書中給出的答案是,把珍貴物品融入宗教藝術、儀式中,在展現莊嚴、尊貴和榮耀的同時,還表達了供養人和被供養者對豐足物質生活的集體性渴望。
夕陽西下,柔和的光線均勻地灑在佛殿的屋頂上,為之鍍上了一層絢麗的光輝。路旁國槐和高大的松樹,自然排列成一條幽深、細長的小徑。我忘掉了嚴寒,久久地佇立在大殿門口,為這座寺院所具有的獨特魅力醉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