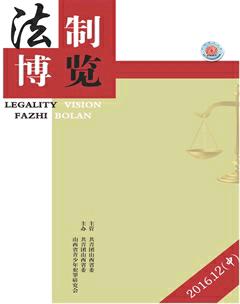中國法律傳統文化中的禮與法的關系
摘 要: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禮與法就如一對孿生姊妹共同支配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傳統文化中的禮與法是對立統一的關系,兩者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其區別表現在地位上、起源上、價值取向上;其聯系主要表現在性質上的互通、內容上的互融、功能上的互補。
關鍵詞:禮;法;區別;聯系
中圖分類號:D90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4379-(2016)35-0073-02
作者簡介:范曉晉(1963-),河北廊坊人,河北省廊坊市光明公證處,公證員,研究方向:民商法。
禮與法,是兩種性質不完全相同,但又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社會現象和規范人們行為的規范。許慎在《說文解字》中指出:“灋(法),刑也,平之如水,從水;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由此我們認為法具有公平裁判之意,禮最初的意思是一種事神的祭祀儀式。后來隨著法與禮的系統化、規范化,法與禮從宗教意義向世俗、社會意義轉變。中國傳統的法指的是由國王、皇帝或專門的立法機構制定的體現統治階級的意志,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并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行為規范,在內容上主要表現為刑、律令及例等形式。“中國傳統的‘禮則可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制度層面的,其包括隆重正規的國家典禮,如皇帝、王室的祭祀;不同社會等級所相應享用的不同規格的車馬、輿服、飲食、居所等等。制度層面的‘禮還包括不同地區、家族的人們在長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被國家認可并默許的風俗習慣,如鄉規村約、家族法等等。二是價值觀層面的,‘禮凝結了中國傳統法的價值追求,如和諧、道德等等。”①
在中國的古代,禮與法作為兩大社會規范總是聯系在一起的,法與禮有著極深的淵源。中國古代禮與法的關系是對立統一的關系,在表現出區別的同時,兩者又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系。
一、傳統禮與法的區別
(一)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不同
禮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基礎地位,而法居于輔助地位、從屬地位。中國傳統的禮起源于對上帝、神靈、祖先的祭祀活動,要求人們事上帝、神靈、祖先的內容和程序符合天道、神道和孝道。“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禮。禮有五經,莫重于祭”②雖然后來禮也有“地之義”、“民之行”的含義,但在對神靈和祖先懷著無限崇敬的古代社會,由于人們對禮起源的神秘崇拜從而使禮在調整世俗社會時也就具有至高的核心地位。
古代由于立法技術落后,執法司法成本較高使法律體系遠沒有現代這樣完備,而且在法律的適用上也不是完全地依法辦事,禮、德、情在處理具體的案件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德主刑輔”就反映了古代法的輔助地位,遠沒有形成現代社會的司法獨立。其實在整個古代社會,法(通常是刑)在維護社會統治中主要是起到維護封建禮制、德治、人治的作用,實現禮制、德治并最終達到人治才是古代“法治”的目的。因而古代法在傳統社會主要具有工具性價值,其輔助服務地位也就顯而意見了。
(二)起源上的不同
禮起源于唯心的自然法。自然法是自然演化而形成的支配人們言行的人們無可抗拒的自然規律,也叫做天道。梁啟超在分析先秦的“天道觀”中指出:“有一有感覺、有情緒、有意志之天直接指揮人事者,既而此感覺、情緒、意志化為人類生活之理法,名之曰天道”③《漢書·刑法志》這樣總結了中國傳統法與自然間的關系:“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固天討而作五刑。”④為了順應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則、效法自然、在與自然溝通的原則基礎上制定人間的法則,這就是中國古人的“自然法”,即中國傳統的禮。這種對自然神靈的敬畏而對自然規律的認識是建立在唯心論的基礎之上的不太科學的認識,這也與當時科技的不發達有很大的關系。
法作為一種較為規范的社會控制手段是與國家分不開的。在古代和中世紀流行著君權神授,法自君出的觀點,資產階級人文主義法學家認為法起源于人性和理性的需要,他們所倡導的自然法就是指永恒不變的普遍真理和道德原理,當然還有人認為法是民族精神的體現等。非馬克思主義關于法的起源看到了法演變的一個方面,有的混淆了法與原始習慣、風俗的區別,因而并沒有揭示法的本質和物質基礎,具有一定的片面性。馬克思主義從歷史發展的必然性上闡述了法產生經濟條件、階級基礎和人性的需要,即生產的發展使產品有了剩余,產品分配的不均而導致的貧富差距從而產生了階級以及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產生的矛盾沖突,所有這些都需要規范的、系統的、強制的社會控制手段的出現,這就是法。而且馬克思陳述了法產生的標志,即國家的產生,訴訟與審判的出現,權利與義務的分離。因而法是階級的產物,現代意義的古代法起源于物質沖突和階級劃分。
(三)價值取向上的不同
禮的價值取向是人倫道德,人倫在古代首先主要指的是人的行為符合一定的風俗、習慣,比如有關服飾、飲食等方面合乎風俗、習慣的禮;其次禮表示人的行為要遵循一定的程序步驟,如祭祀、結婚、朝拜等方面的有關程序、步驟之禮;再次禮表明社會成員依其社會地位的不同而區別對待,如尊尊、親親等方面的等級禮。禮的道德屬性主要是要求人們講究仁愛、忠孝、信義等具有善內涵的品行并要求行為符合這些善德,具有教化洗禮的功能。
古代法主要的價值取向是維護社會秩序,維護皇權等統治階級的利益,從而使人們的行為符合法所維護的統治階級的意志。古代的法家思想家雖然倡導公平正義的法,但事實上由于剝削階級的本質不變,從而使古代的法并未真正實現現代法所體現的價值,適用法律上的等級差別,法的非道德性,非嚴格的依法辦事都體現了法的任意性和階級性。但無論如何法都是統治階級手中的統治工具。
二、禮與法的聯系
(一)性質上的互通
人們通常把禮與法當作合成詞使用,從而可以看出禮與法在性質上具有一定的相通性。這種禮與法在性質上的互通性表現在:第一,唯心意義上的互通。從許慎的《說文解字》對法的解釋,神獸具有識別曲直的能力,可以“觸不直者去之”,因而法具有神明裁判的含義。而且,古代強調“君權神授”,“法自君出”,法是由上帝派來的天子制造的并用來統治臣民的工具,具有神圣不可違反性。可見,法從一開始就具有神秘的含義。而禮的神秘色彩更是顯而易見,它起源于天地鬼神的治人之法,因而有人把中國傳統中的禮與西方的宗教相提并論。第二,由神秘向世俗的轉變使禮與法都成為了古代人們行為的坐標。法在發展過程中由神獸“觸不直者去之”逐漸地變為由世俗的政府司法官員運用其裁判和解決人們之間的案件糾紛,法因而成為了規范人們行為的規范,盡管這種法不具有現代意義上的公平、正義、平等,但它在約束人們行為上具有強制性。禮在發展過程中由“事神致福”逐漸向“民之行”轉變。禮的內容不僅包括從事宗教、祭祀和其它一些活動的程序、步驟的禮制或禮儀,也包括用來解釋禮制或禮儀的禮義,還包括傳播、講述這些禮制和禮義的禮教,這些內容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那就是使人們的行為符合某種禮儀或精神尤其是統治階級所倡導的禮儀和精神,這與法規范人們的行為并符合統治階級的意志在性質上是一致的。從上面我們可以看出,古代的法與禮在性質上是互通的。
(二)內容上的互融
禮的內容包羅萬象,它在范圍上寬泛于法。日本的穗積陳重博士曰:“舉凡宗教、道德、慣習、法律,悉舉而包諸禮儀之中。……故上自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下逮冠、昏、喪、祭、宮室、衣服、飲食、器具、言語、容貌、進退,凡一切人事,無大無小,而悉納于禮之范圍。”⑤但法與禮在許多方面是相同的。如古代有“尊尊”、“親親”之禮,而古代法中的十惡不赦中就有關于維護皇帝和家長的“大逆”、“不孝”等罪,體現了禮與法在內容上的互融性。
(三)功能上的互補
中國傳統的禮法在功能上具有互補性,具體表現在禮的教育功能和法的保障功能。
1.禮的教育功能
古代的禮有一種內涵就是禮教。《辭源》釋“禮教”為“禮儀教化”。實際上,禮教不只局限于教導人們禮儀,禮教更重要的是通過國家、社會、宗旅、家庭等各種教育手段,以禮儀來統一人們的思想,指導人們的言行。孔子主張“有教無類”,又廣收弟子,私設私塾,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傳統,從而使尊師重教成為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因而傳道授業的老師也被抬高,可以與天地君親相并列。禮教的主要內容是人倫道德,《孟子·藤文公》曰:“教以人淪——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教以人倫”的主張自漢武帝時起,就被作為冶國的根本,一直綿延至清代。這些人倫道德正是古代法的精神價值之所在。因此,禮教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人們守法的自覺性,禮的發展也因而奠定了法的倫理基礎,提升了法的道德性。
2.法的保障功能
中國古代的立法與司法十分強調法制與禮義(即人倫道德)的統一性。《禮記·王制》有這樣的論證;“凡制五刑,必即天倫……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在中國古代社會,禮教所提倡的價值觀浸透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也浸透在法的規范之中。因而法律化的禮義更具有強制保障性。傳統法中的禮義與法制的關系頗有些類似西方法的正義精神與法的規則之間的關系。禮義是入們心目中的“大法”,法制只是實施這個大法的一個渠道,一種手段,一條途徑。
由此可以看出,禮的教化功能和法的保障功能使禮與法在功能上形成了互補,共同規范人們的行為符合人倫道德和符合法律規范。
無論如何,禮與法在中國古代共同統治著人民,維護著社會秩序的穩定,它們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功能維護了兩千多年的超穩定統治。在建立和諧社會的今天,我們有必要研究古代傳統文化中對我們有用的東西,在加強依法治國的同時,強調以德治國,以禮治國。因此,我們有必要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中禮與法的互補功能,借鑒傳統文化中禮與法共同治理國家中的積極作用,從而促進我國社會的和諧。
[ 注 釋 ]
①馬小紅.禮與法:法的歷史連接[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8:69.
②<禮記·祭統>.
③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太原:東大圖書公司,1987:25.
④<漢書·刑法志>.
⑤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五·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M].北京:中華書局,2005:7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