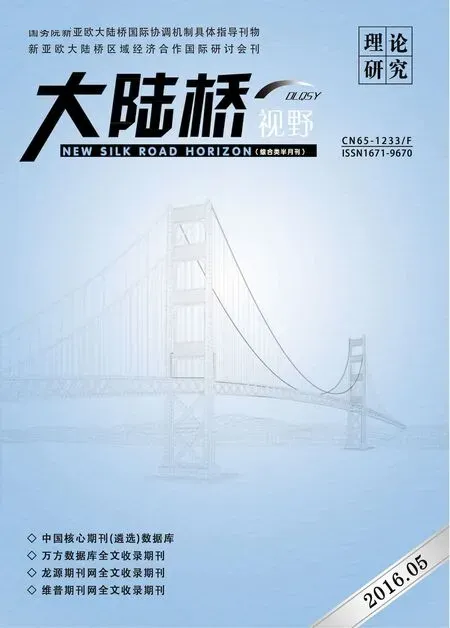環境保護的公眾參與制度研究
邱 童 / 鞍山市立山區環境保護局
?
環境保護的公眾參與制度研究
邱 童 / 鞍山市立山區環境保護局
【摘 要】公眾參與制度是環境法的一項重要制度,各國基于國情而建立了不同的機制,在對各國公眾參與機制進行考察的基礎上,我國借鑒各國的有益經驗,應當明確公眾范圍,確定公眾參與的內容,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公眾參與方式,并設計合理的公眾參與程序。明確公眾參與具有決定性的法律效力。
【關鍵詞】環境保護;公眾參與;公眾參與主體;被動式行政性參與;公益訴訟
世界環保事業的最初推動力量就來自公眾,沒有公眾的參與就沒有環境保護運動[1]。公眾參與環境保護最初主要采取集會、游行、抗議、請愿等方式,到20世紀70年代以后,公眾參與形成政治力量,并逐漸法律化、制度化[2]。一般認為,美國《環境法》首先從法律上確立了公眾參與制度,以后為各國環境法所推崇,成為環境法的一項重要制度。從而形成了制度內和制度外公眾參與環境保護。制度外的參與主要是環境抗議活動,制度內的參與就是人們是日常所言的公眾參與制度。其中以制度內公眾參與為主流。但在我國公眾參與制度尚不完善,因此本文擬對此進行探討。
一、公眾參與的主體范圍界定
公眾參與之主體即公眾,指的是政府為之服務的主體群眾;所謂公眾參與,指的是群眾參與政府公共政策的權利[3]。因此,公眾是與政府和建設單位相對應的社會民眾,其具體范圍指:(1)自然人,公眾主要是指全體社會成員的集合體,自然人是公眾的主要部分;(2)法人,是指受環境影響的法人組織,在環境保護中法人也應當作為公眾參與其中;(3)社會團體,是指人們基于共同利益或者興趣與愛好而自愿組成的一種非營利社會組織,國外稱之為非政府組織或者非營利組織,社會學使用中介組織,經濟學常用非營利組織,政治學稱之為第三部門[2]。
明確特定環境事務公眾參與的公眾范圍才能確保公眾參與的實質實現,如果沒有明確的界定,那么公眾相對人或政府有關部門在公眾參與制度中可能利用其不明確性而達到自己的目的。比如一個建設項目可能對周圍環境造成破壞,一般而言,最靠近項目的環境破壞最嚴重,從里向外擴散,受破壞的程度逐漸減輕,如果相對人、政府選取最邊沿的公眾參與,那么當然會得到同意。因此,我們應當通過立法方式明確特定環境事務參與的公眾范圍,可以以環境事務所在地點為中心,沿著環境受影響的擴散方向,確定一定區域內的公眾即是該環境事務的公眾參與主體,進而以中心為基點,按影響環境的因素的衰減率,劃分不同區域,并確定不同區域的公眾參與的權重,受環境影響越大的區域內的公眾參與的權重也越大。
二、公眾參與的內容
關于公眾參與的內容,一直有爭議,有的學者認為是參與決策活動[4];有的學者認為是參與有關環境立法、司法、執法、守法與法律監督事務決策活動;有的學者認為公眾參與包括立法參與、決策參與及執法參與[5]。我國環境保護法律法規規定環境決策力主政府主導,如我國《環境保護法》規定了環境質量標準由國務院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制定國家環境質量標準;沒有規定公眾參與決策保護和改善環境、防治環境污染和其他公害;只規定了公眾參與環境影響評價的執法,而對參與環境法律救濟則僅規定了個人權利受到侵犯時通過訴訟救濟自己的權利,而沒有規定公益訴訟制度。這種不全面的參與實質排斥和限制了公眾參與,因為如果僅僅是某一方面的參與,結果可能將其參與空化,必然打擊公眾參與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因此,我國應當借鑒發達國家的有益經驗和成熟的制度建設,建立公眾全方位參與決策、監督、執法和法律救濟的制度。
執法參與,即參與到政府相關機關的環境法律法規和政策執行、貫徹活動中。任何環境法律法規、政策、技術規范無論有多完美,對公眾的環境利益確認和保護如何周到,如果沒有得到執行,那么只能是美好的畫餅。執行的參與可以確保公眾決策的落實,從而實現公眾的環境利益。
公眾參與監督即公眾參與對所有有環境保護義務的人監督其是否履行法律法規規定的義務,以及其行為是否符合環境政策。這種監督是一種社會性監督。
公眾參與法律救濟,即公眾對于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和政策,致環境受到損害或可能致環境受到損害的行為,通過法律途徑使受到損害的環境得到恢復,或可能受到損害的環境免受破壞。法律救濟的公眾參與應當與因環境侵權而受到損害的權利人通過法律救濟而獲得賠償有所不同,應當特指我們所言之公益訴訟。公眾參與法律救濟是公眾參與環境利益保護的最后一道防線。
三、公眾參與模式的比較與選擇
我國公眾環境保護意識淡薄,參與意識不強,因此許多學者在探討我國環境保護公眾參與機制或制度建設時,都特別強調要提高公眾的環境保護意識和參與意識[6],但公眾的環境保護意識、參與意識的培養和提高不是短期內就能實現的,因此,我們目前迫在眉睫的是根據當前的國情建立一種適當的參與模式。
根據公眾參與主體是否自覺,可分為主動式參與和被動式參與。主動式參與即參與主體通過自己的積極行為,參與到環境保護活動中去的方式。是主體自覺的一種行為。被動式參與則是在環境保護活動中,參與主體基于相對人或政府的行為而參與其中,并非一種自覺的行為,如在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對組織者發放的調查表的回答、對有關問題的回答等都是被動式參與。
根據公眾參與主體參與的直接目的,可分為預防性參與和救濟式參與。預防性參與是指公眾參與的目的是為了防止環境事故之發生,比如參與決策多是預防性參與,一些監督、執法活動也是預防性。救濟性參與則是環境事故已經發生,公眾參與是為了救濟被破壞的環境和受害人,公益訴訟多是救濟性的。
根據公眾參與的活動性質,分為行政性參與和司法性參與。行政性參與是公眾參與至環境行政管理活動中,或配合行政管理,或通過行政管理方式到達保護環境之目的。
上述單一模式進一步組合,形成主動式的預防性行政性參與模式;主動式預防性司法性參與模式;被動式預防性的行政性參與模式;被動式的救濟性司法性參與模式。不同的模式需要不同的條件,才能發揮作用。一般而言,主動式的模式中必須要有良好的公眾環境意識,在法律上確立環境權,公眾的權利意識強烈。而被動式模式中相對對公眾的環境意識、權利意識要求不高,但對法律制度要求應當更嚴格,相關程序保障更具體。
我國目前民眾的環境保護意識較為淡薄,公眾參與意識不強,公眾性的社會團體較少,市民社會不成熟,而且中國環境保護主流是自上而下式的,司法的獨立性仍然較為脆弱,因此,我國更應當采取一種被動式的行政性參與模式。
四、公眾參與的程序保障
公眾參與程序是公眾參與能否實際得到實現的根本保障,任何權利或制度如果沒有程序的保障,必須淪為空化,加強公眾參與的程序制度建設對于確保公眾真實的參與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因此,我國《環境保護法》《環境影響評價法》規定了應當確保公眾參與,但沒有建立相應的程序。我們不僅應當建立相應的程序,而且程序必須公正。公眾參與的程序應當公正,程序公正是保證公眾參與的公信力,使相對人和其他一般人心悅誠服的條件。首先,必須在確保公眾都有參加到環境保護中的權利,這些權利應當包括直接參加權、參加機會權、間接參加權,以及保證公眾具有充分而實質性的話語權[7]。我國《環境影響評價法》、《公眾參與環境影響評價辦法》等環境法律法規雖然建立了公眾參與制度,但卻缺失這些權利確認和保護。其次,提供參加場所的便利,降低參加程序的成本。公眾的參加是否能夠具有實質性內容,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作為參加前提的程序進行場所,參加程序的場所的地點、距離、陳設等都可能影響到公眾是否參加和參加時能否充分地表述自己的意思或反駁對方的主張[3]。
五、公眾參與的法律效力
公眾參與在法律上有什么效力,我國〈環境影響評價法〉、《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公眾參與環境影響評價辦法》等環境法律法規雖然建立了公眾參與制度,但卻只規定了對沒有公眾參與的環境評價有關單位、人員承擔相應的行政責任或刑事責任,規定了建設單位如果沒有公眾參與而作出的環境影響評價報告,要求其補辦,而沒有明確規定沒有公眾參與的環境評價是否有法律效力,以及公眾表示反對有法律效果。更沒有規定沒有進行法律規定的公眾參與的環境活動或環境行為的法律效力。
公眾參與不是僅僅表達意見,而是要維護其環境利益,因此,公眾參與如果不能產生相應的法律效力,即不能產生阻止或同意某種環境活動或行為的效力,那么,公眾的環境利益就不可能得到實現和保護,因此,我國公眾參與制度建設必須明確公眾參與的法律效力,明確規定公眾參與可以起到阻止或同意特定環境活動或行為的作用,如果沒有進行法定的公眾參與,那么特定的環境活動或環境行為就不能進行。
參考文獻:
[1]潘岳:環境保護與公眾參與,《人民日報》,2004年07月15日第九版.
[2]李艷芳:《公眾參與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P41、9-10、126、228-229.
[3]潘岳:環境保護與公眾參與——在科學發展觀世界環境名人報告會上的演講.
[4]常紀文、陳明劍:《環境法總論》,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03年,P148.
[5]如陳泉生等:《環境法學基本理論》,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4年,P162;石莎:我國環境保護中公眾參與問題研究,中國環境法網.
[6][英]克里斯托弗.盧茨:《西方環境運動:地方、國家和全球向度》,徐凱譯,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P40、P41.
[7](日)谷囗安平:《程序正義與訴訟》,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P12-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