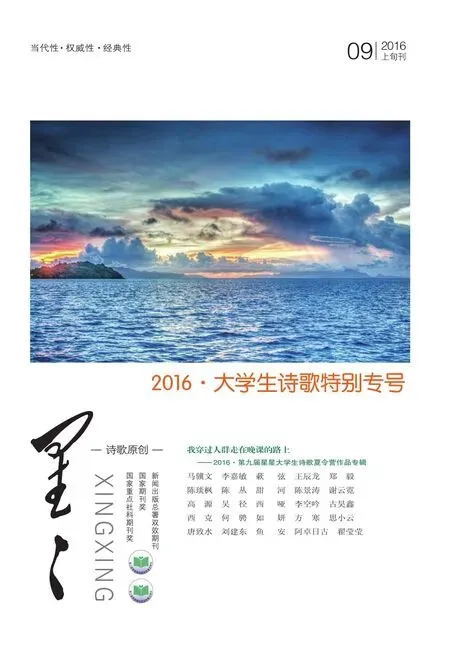上海交通大學白巖詩社
2016-12-29 05:20:53
星星·散文詩 2016年25期
上海交通大學白巖詩社
長 信
張瑪麗
你知道我給一個男人寫長信
他有時在北方
我肯定這世上有一條路停著他那輛切諾基
很老,又很整齊
曾搭載我和一只黃腹樹鶯
一會兒很熱,一會兒很涼
我嘗試在遠遠的地方存在
在這兩次,輕輕的崩塌之間
不斷撕扯出新的
金色的
驚訝
蹤跡無循的時候
我肯定這世上有一條路停著他那輛切諾基
松散的可疑點落在雪后的樹枝上
很晚了,他的周身也活在這流動的風中
撬開一只貝類攫取一線光明
偶爾夜憐憫我低垂的眼皮
從窗縫中擠進來,躺在我的床畔
飲下我高貴的頸部,我們一起注視
秋天的燈光開始變得暗沉,或許是
杏花慢吞吞地褪盡顏色,像扔掉一只拖鞋
我這時對詞語的選用便格外較真,是因為
你曾仔細將一枚耳釘鉤在我空洞的聲音中
讓我忌諱不具體的音信,那如同被尊嚴泅濕的地址
你知道我給一個男人寫長信
他有時在南方
大明湖記事
王藝彭
從白天到夜晚,詩歌的質量變得輕盈
夜色像一杯酒,而我們像冰塊,像檸檬
投身于斯,有些沉下去,有些浮起來
我想要趁著這酒尚未喝光之前,與你們
溶化在一起,溶化在你們讀詩的余音里
酒館的小木桌子是余音里搖曳的一條船
載著杯子瓶子,載著搖曳的人們,熏熏
與其尋找彼岸,倒不如就醉倒在此處
不如聽我唱幾首跑調的歌,不如沉默不語
喝下更多的酒,直到
直到把所有瓶子倒干,直到人們都離開
回家睡覺,直到賣煙小鋪打烊,多少條街都打烊
直到城市沉睡之后,整個濟南只剩下大明湖
赤裸裸等在那里,等我們從許多街道的身后
跋涉而來
來,大明湖是今夜的最后一杯
渡 口
樟 木
在暮色的渡口尋一舟寂靜
渡我瀚海,渡我春水
渡我混沌月色
渡我如日悲歌
或者你成為河流
馬不停蹄地奔向簇擁的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