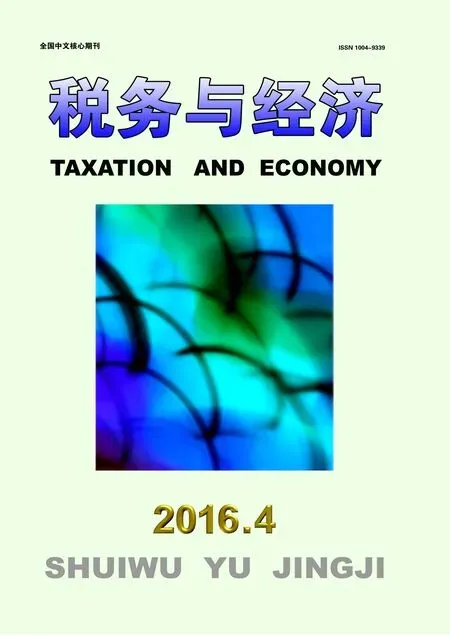我國技術創新的經濟增長效應
孫文博
(吉林工商學院 金融學院,吉林 長春 130507)
創新是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面對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滑、單純依賴要素稟賦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果弱化、人口紅利銳減導致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下降等現實,中國政府開啟了尋求技術創新拉動經濟增長的改革之路。然而,我國在技術創新模式選擇、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構建、創新環境營造、區域經濟發展非平衡調節等層面缺乏成熟的經驗,這也導致短期內我國技術創新的經濟增長效應并不顯著。
一、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通過技術創新拉動經濟增長的理念源于經典的索洛模型。一國科技投入的增加將首先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在先進科技的引領下,資源環境約束被進一步打破,增加的市場需求將起到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根據索洛模型,后發地區正是依靠成熟的技術創新擴散實現經濟趕超。經濟增長的路徑是持續穩定的,技術創新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應積極鼓勵技術創新,實現技術進步。趙樹寬等(2012)利用VAR模型及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對技術創新與經濟增長的合意結構進行了研究,發現技術創新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動態均衡關系,技術創新是經濟增長的原因,技術創新對技術標準和經濟增長呈正相關關系,是經濟增長的不竭動力。[1]張妍等(2012)認為,技術標準化能夠極大地促進產業合理競爭,對技術創新的持續循環也起到積極的助推作用。技術標準化體系的成熟構建有助于規范市場競爭和技術創新,反之則會導致市場壟斷的形成,桎梏技術創新的進一步推進。[2]董直慶、王林輝(2013)將要素錯配和適宜性技術發展結合起來進行探討,指出經濟增長除與要素異質性息息相關外,還受要素匹配因素及適宜性技術因素的影響。此外,通過計量模型分析,他們認為,資本體現式技術進步是生產率增長的重要動因,行業整體的技術合意結構特征并不明顯,而高國有化行業和高利潤率行業具有較為顯著的合意技術結構。[3]
近年來,對于技術創新能力是促進企業不斷發展壯大、提高產品競爭力的重要動力,學術界已達成共識,但是,對于從何種角度來分析技術創新的影響因素,學者們尚未形成統一的意見。簡兆權、王晨和陳建宏(2014)以內外相結合的視角研究戰略導向和動態能力對技術創新的影響,通過計量分析得出,市場導向對技術創新具有明顯的正向影響,動態能力則起到了媒介作用。其中,動態能力對技術創新的影響程度與企業所面臨的環境因素呈正相關關系,企業所處的外部環境中不確定性越高,動態能力對技術創新的影響程度就越顯著。[4]王必達和鄭永杰(2008)則認為,要使技術創新的后發優勢從潛在優勢真正轉化為現實優勢,不僅需要諸如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規模經濟等條件的支持,還取決于各種條件的合理搭配組合,如技術模仿和制度移植的互動性。[5]鮑輝(2010)通過對技術差距模型和南北貿易模型的分析得出,貿易中的技術創新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影響因素,同時也是后發地區后發優勢發揮的重要內容。[6]康凱、蘇建旭和張會云(2000)以地域差異性作為切入點,建立了非均質空間各向同性的技術創新擴散模型,并得出了技術創新空間擴散的基本趨勢,即不同地域的技術創新擴散速度是不同的,擴散首先在被采納概率高的地理范疇內發生,然后逐漸向被采納概率低的地理范疇轉移。[7]程淑娜(2010)進一步對技術創新的空間擴散及采納理論進行研究,利用空間擴散動態模型對采納率和距離兩個變量進行測算,通過回歸分析,驗證了技術創新擴散的時空雙重動態性。[8]
綜上可見,技術創新能夠起到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但是技術創新的經濟增長效力發揮則需要國家不斷提高創新采納能力,將適宜性技術應用于當地經濟,促進其與區域發展的耦合協調,只有這樣才能激發我國技術創新的優勢潛能,并規避落后地區后發優勢陷阱的發生。
二、中國技術創新的經濟增長效應分析
2015年7月,由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發布的《國家創新指數報告2014》顯示,中國國家創新指數排名位居全球第19位,在亞洲處于領先地位。2014年,中國R&D人員全時當量達到371.1萬人/年,比去年同期增長5個百分點;全年R&D經費支出13 015.6億元,占當年國民生產總值比重為2.05%,其中,投向基礎研發的資金為613.5億元,實驗發展支出11 003.6億元,分別占比達4.7%和84%。由此可見,我國科技研發經費支出與基礎性研發資金比重依然偏低。2014年,我國在專利申請受理數方面首次出現下滑,由2013年的2 377 061件下降至2 361 243件,最終專利授權比重方面也呈現出0.061%的微弱下降。在技術市場中,我國高技術產品進口額為5514億美元,而高技術產品出口額為6605億美元,最終技術市場成交額高達8577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4.83% 。
與此相應,國家科技創新要素的大規模投入也進一步刺激了我國產出水平的節節抬升。2014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高達60.6萬億元,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新產品開發項目數為375 863個,同比增長4.9%;新產品銷售收入達到142 895.3億元,新產品出口量更是達到26 904.4億元。隨著科技含量與附加值的提升,我國的工業制成品進一步提升了市場認可度。在規模以上企業創新采納方面,2014年實現產品創新的企業占總企業比重為24.6%,而實現新工藝的企業占總企業比重為25.1%;高新技術企業在技術創新主營業務收入與利潤方面,分別達到127 367.7億元和8 095.2億元。在科技論文收錄方面,2013年我國SCI期刊發表數量為192 697篇,EI期刊發表數量為153 717篇,可見高校科技研發實力進一步增強。而相繼出臺的一系列創新扶持政策實施效果也開始顯現。從大中型工業企業享受加計扣除減免稅政策看,2014年受惠企業突破0.6萬家 。而在資源消耗方面,技術創新亦起到了積極效應。我國能源消費總量增幅相較2013年下降1.5%,同時單位GDP能耗也下降近5個百分點。總體而言,在人口紅利銳減、國內經濟步入發展新常態的背景下,技術創新作為拉動產出增長的新動力,為我國經濟的再次蓄力新騰飛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我國利用技術創新提振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也存在諸多問題,這也阻礙了我國技術創新的經濟增長效應的進一步發揮與釋放。
1.技術創新的拉動效應呈現顯著的區域非平衡性。尹偉華、張亞雄(2016)研究發現,我國的技術創新能力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自主技術創新能力也更為突出,而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由于創新環境落后、創新采納能力不強等原因,技術創新能力也更為薄弱。[9]從國家統計局對我國科技數據的統計結果也不難發現,2014年北京地區R&D人員全時當量、R&D經費和專利申請數分別為57 761人/年、2 335 010萬元和19 916件;而經濟相對欠發達的青海地區的R&D人員全時當量、R&D經費和專利申請數則僅為2068人/年、92 528萬元和384件,兩者的創新發展數量級不可同日而語。在分地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新產品開發及生產情況方面,上海的新產品開發項目數、新產品開發經費支出和新產品銷售收入分別為18 927項、5 875 497萬元和84 469 638萬元;而海南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新產品開發項目數、新產品開發經費支出和新產品銷售收入卻只有843項、116 963萬元和1 482 605萬元。創新資源投入的傾向性引致非均質技術創新擴散,而這也加劇了區域創新產出非平衡的現狀。技術創新的“馬太效應”愈發明顯,這對于原本就存在嚴重區域發展不協調的我國而言,地區兩級分化問題更加突出。
2.非均質技術創新擴散致使經濟后發優勢陷阱出現。一直以來,在后發優勢理論的引導下,落后地區可以不必像先進地區那樣依靠高額的研發投入來提高技術水平。它們可以充分利用“后發優勢”, 通過接受來自先進地區的技術擴散與技術外溢從而實現技術進步。如此推論,中國地區間的經濟發展非均衡應在后發優勢理論下得以解決,后發地區應該遵循一條“后來居上”的發展道路。然而,當前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現實卻是——廣東省地區生產總值已于2013年超越世界第16大經濟體印度尼西亞(0.87萬億美元),而西藏地區卻僅僅相當于排名世界第122位的阿爾巴尼亞(129億美元)的水平。從人均來看,天津、北京、上海、江蘇、內蒙古人均GDP已超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1.06萬美元左右),而貴州卻不及世界第110位佛得角(3785美元)的水平。上述現象就是所謂的后發優勢陷阱——理論上落后地區的后發優勢潛能并沒能因技術創新而被完全激發,而落后地區技術創新接納能力不足是導致地區后發優勢陷阱形成的最根本原因。由此可見,后發優勢趕超理論在中國存在明顯的悖論,技術創新的經濟增長效應存在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的趨勢。在知識經濟時代,由于知識更迭加快,新技術開發周期縮短,落后地區僅靠跟蹤學習和模仿,難以追趕、超越發達地區。而在資源稟賦、智力稟賦、乃至制度稟賦都更為優越的發達地區,技術創新的邊際收益呈現出遞增態勢,這也進一步強化、鞏固了其先發優勢。與此同時,技術創新的擴散方式也極大地影響著后發優勢的發揮。具體而言,技術創新擴散分為鄰近型技術創新擴散和等級型技術創新擴散兩類。然而,并非地理位置鄰近就易于技術創新傳播。緊靠北京的河北、毗鄰廣東的廣西,都沒能更好地受惠于此種地緣優勢,形成顯著的經濟水平提升。
3.我國技術創新的立法環境建設不健全。提及中國制造留給世界的印象,更多是以仿造、“山寨”為主,可見我國對于外來技術創新的引用亂象依然十分明顯,創新立法環境建設并不完善。縱然,技術創新的最基本模式是模仿創新,但純粹復制、抄襲外來商品,甚至利用非法手段侵蝕他人品牌、專利和商標的行為,將更被市場所不恥。正所謂,無規矩不成方圓。我國創新產品若想要更被市場認可,就需要在公平、統一的規則和秩序下,有約束地制造與生產。因此,不僅僅是企業的創新保護意識需要進一步提升,相關知識產權與專利立法體系也要盡快完善。健全的立法體系是企業技術創新實現的根本,企業若是單純為了追逐財富而有選擇地無視相關法律,最終只能是作繭自縛。
一國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究其根本在于技術創新環境的營造和技術創新文化的培植。“山寨”、復制、不尊重知識產權的現象是我國企業對研發生產流程的怠慢與不屑。中國制造從思想源頭就沒能形成精益求精、踏實尊重的創新沿襲理念,這種文化層面的熏陶不利、生產過程的偷工減料,也是我國產成品不被市場認可、品牌效應無法樹立的關鍵所在。
三、增強我國技術創新經濟增長效應的策略選擇
在技術創新初期,創新投入將帶來非常顯著的創新產出增加,即經濟增長效應。但隨著創新投入要素的繼續增加,這種經濟增長效應便呈現出邊際效應遞減的態勢,最終技術創新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將在某一水平實現穩定。若一國希望獲得更大的創新增長紅利,只能通過技術創新模式的革新與創新環境的進一步營造才能最終實現。每一個后發國家都是遵循了這樣一種創新發展軌跡,才最終實現了經濟的飛躍式發展。
我國當前正處于技術創新的初級階段。高新技術產業、新能源產業、高端裝備制造業等尚未完成技術全面引進,所以我國在挖掘技術創新紅利的道路上依然有機可尋。對于一個接近獲取完人口紅利的國家而言,技術紅利的獲取尚處于初始階段。因此,應審時度勢,抓住技術創新經濟增長效應大幅增長的時期,努力挖掘技術潛力,順利實現對于“經濟發展新常態”的跨越。為此,結合自身技術創新中存在的不足,當前為了增加技術創新的經濟增長效應,我國應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做起:
1.加速推動我國技術創新從外部引進向自主創新轉變。技術創新模式由外部引進向自主創新轉變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外部引進型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效力是有限的,如果將其作為本國技術創新模式的主流,極易形成技術創新的外部依賴。這種被動型的創新模式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我國的創新活力。因此,我國需要在引進、吸收、模仿的基礎上,繼續加大對原有創新的創造與改良,依此,新的科技創新才會萌生。在推進自主技術創新的過程中,首先,應追加實驗室研發與基礎學科研發的R&D經費投入。同時加強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的指引作用,推動科技成果的實驗室轉化比率。其次,在人才隊伍建設方面,高校應注重標準化教育,而企業則需要不斷提升人才激勵機制。最后,還需加強技術創新與市場需求的相互銜接程度。只有不斷順應市場需求,提升產成品的創新改良傾向性,才能真正加速我國自主技術創新的步伐。
2.加大對我國落后地區的技術創新要素投入力度。區域經濟發展的非平衡已成為阻礙我國經濟轉型的最大桎梏,而各地的技術創新水平也呈現出明顯的差異性。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無論在創新資源、創新環境還是高端人才吸引力上都比經濟落后地區擁有更多的比較優勢,而伴隨著創新要素的持續投入,地區間技術創新的經濟增長效應也呈現出“馬太效應”。因此,我國技術創新政策在制定過程中需要采取一定的傾向性,即加大對落后地區的創新投入與政策扶持力度。市場應更加發揮投資、價格等變量的指引性效力,推動不同地域間資源和人才的流動速率。
3.加強我國技術創新制度與技術創新環境營造。在技術創新的制度環境營造方面,國家應形成自上而下的技術創新發展戰略,而各省市亦需要在此戰略下制定兼顧差別化和靈活化的配套政策。我國已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科技規劃綱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決定》、《國務院關于實施<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若干配套政策》和《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而為全面提升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動力,國家發展改革委又聯合科技部等十部委出臺了《關于支持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若干政策》。但若想通過這些政策的推出更好地激發中小企業的創新熱情,還需要地方政府努力促進相關政策在當地的落實。除扶持政策外,國家還應加大力度參與與技術創新相關的立法體系建設。要強化知識產權保護風氣,從根本上扭轉中國產品“山寨制造”的不利形象,依托技術創新重塑中國制造的品牌形象。
在技術創新環境的營造方面,國家應大力加強地方創新技術示范園區的建設工作。配套完善示范園區內的資金供給與技術轉讓等平臺建設,進一步發揮創新園區在官、產、學、研方面的整合力度與集群效應。可以說,技術創新環境的營造將直接提升一國的創新采納能力,而這也是國家吸收外部技術創新,發展自主技術創新的根本基礎,也是改變和規避落后地區后發優勢陷阱的必經路徑。可以預見,軟硬件環境建設的加強與協調將決定我國技術創新能力發展的下限。因此,只有不遺余力地對其進行完善,才能不斷釋放我國技術創新的經濟增長效應。
[1]趙樹寬,等.技術標準、技術創新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理論模型及實證分析[J].科學學研究,2012,(9).
[2]張研,等.技術標準化對產業創新的作用機理研究[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2,(5).
[3]董直慶,王林輝.要素錯配、異質性要素發展和適宜性技術進步前沿文獻述評[J].學術交流,2013,(1).
[4]簡兆權,等.研發服務業成長:模式與路徑[J].軟科學,2014,(5).
[5]王必達,鄭永杰.論技術模仿創新后發優勢及其轉化條件[J].吉林師范大學學報,2008,(2).
[6]鮑輝.后發地區的后發優勢發揮——基于區域貿易中的技術擴散和創新視角[J].經濟研究導刊,2010,(17).
[7]康凱,等.非均質空間各向同性的技術創新擴散模型研究[J].河北工業大學學報,2000,(6).
[8]程淑娜.技術創新空間擴散理論及動態模型研究[J].理論探討,2010,(6).
[9]尹偉華,張亞雄.我國工業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分析[J].調研世界,20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