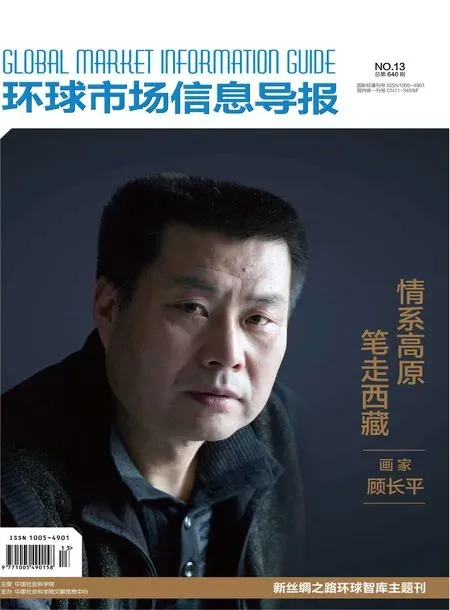物質經濟與精神財富
——錢穆的經濟史思想
◎陳厲辭
物質經濟與精神財富
——錢穆的經濟史思想
◎陳厲辭1,2
錢穆的經濟史思想立足于中國傳統文化,沒有盲目套用西方經濟學家觀點,保持了很高的獨立性。其客觀、理性,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治史原則對于當今史學研究與國家經濟理論探索有重要意義。
錢穆是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并稱為“史學四大家”。其著作既包括《國史大綱》、《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學術經典,也包含根據其講課記錄整理而成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史學名著》等通俗史學讀物。這些經典被廣大民眾喜愛或熟知。錢穆治學門類頗廣,僅臺灣聯經版《錢賓四先生全集》,共54冊,多達80余種著作。就經濟史而言,除貫徹于其他著作中的經濟史學觀點,錢穆先生也曾于五十年,于香港新亞書院講授“中國經濟史”及“中國社會思想史”兩門課程,后經其弟子葉龍先生根據講課記錄整理成《中國經濟史》一書,使公眾能夠一窺錢穆先生經濟史研究之一斑。本文將就其著作中所體現的經濟學思想進行總結、探析。
重視文化傳統的一體性,是其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原則
重視文化傳統的一體性,不但是錢穆先生經濟史思想的基本原則,也是其宏觀上治史的方向。他認為:“每項制度之變,也該有一可變的限度,總不能惟心所欲地變。所貴的是要在變動中尋出它不變的本源,這便是所謂歷史傳統。傳統愈久,應該此大本大源之可靠性愈大。換言之,即是其生命力益強。”就經濟史而言,錢穆認為:“我們要研究中國政治史,或社會史,或經濟史,只當在文化傳統之一體性中來作研究,不可各別分割。我們當從政治史、社會史來研究經濟史,亦當從政治思想、社會思想來研究經濟思想,又當從政治制度、社會制度來研究經濟制度。”可以說,錢穆先生的經濟史思想是由文化傳統萌芽而生,因此,傳統文化是錢穆先生經濟史思想的理論基石與來源。這與其同時期的史學大家多借鑒西方史學觀的治史方法有極大的不同。
“經濟人生”相對“政治人生”、“精神人生”處于最底層
錢穆先生認為,人生具有三個層次,即“經濟人生”、“政治人生”、“精神人生”。“經濟”人生是人類生活最先經過的階段,之后就是以“安居樂業”為目的的政治人生,以及第三階層“宗教、道德、文學、藝術”的精神人生。“沒有第一階層,不可能有第二第三階層,但有了第一階層,不一定有二、三階層。但有了第二階層,一定會有第一階層…這是人類文化階層遞進提高的一條規律,可衡量批評一些人類文化意義的標準。”第一層文化是外傾的,向外斗爭的;第二層則是內傾的,向內團結的;第三層是“內外一體”“物我交融”的。古今時間性的隔閡融合了,自然界和人文界的隔閡也融合了。這符合人的發展規律,同樣也是社會與歷史的發展規律。
“低水準的必須經濟”的重要意義
經濟的人生是最底層的人生,而經濟又分為“高水準的不必須經濟”與“低水準的必須經濟”。“低水準的必須經濟”這一概念的提出十分新穎。錢穆認為中國傳統經濟重農抑商是有緣由的,中國人歷來認為,物質經濟對人生的影響是有限的。就人生對經濟的需求而言,也會有個限度,超出這個限度就屬于超水準不必須的經濟。就經濟社會而言,什么是低水準的必須經濟呢?中國以農業立國,因此,農業是最根本的低水準必須經濟。工商業則容易超出此必須的水準與限度,趨向“高水準的不必須經濟”發展。這是中國的歷史傳統,緊握以人生為主,經濟為副的價值觀誕生的原因。事實上,這種思維方式與西方人的史學觀甚至是思維方式是有區別的。不論是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或是馬克思,西方經濟學家都注重工商業的發展。馬克思經濟理論以經濟為社會的基礎,主要在從工業生產中,指出剝削勞工的剩余價值來。雖提倡唯物史觀,但其眼光所到并未看到農業,也沒有將農業在其理想社會中作出安排。這符合西方學者對社會、經濟的論調,即重視工商業,忽視農業。根據錢穆的理論,并不是證明西方學者短見或錯誤,而是認為西方學術觀點誕生于西方學者對歐洲經濟社會的思考。我們有自己的社會,自己獨特的情況,不能將西方的學術理論照搬照抄。
“道德性”在中國經濟史中的意義
根據錢穆先生的理論,中國人自古認為“高水準的不必須經濟”提高了人的欲望,而非人生,是無作用,無價值的。而且引導人生向上的,應非經濟,而實有別的東西。那么,引導人生向上的動力或是本源是什么呢?中國人認為是“道德性”。換句話說,“道德性”超出了貧富的意義,是中國社會的終極標準。中國人說“貧而樂,富而好禮”又說“天下太平”就是這個道理。正因為如此,古代封建制度崩潰后,社會上的三種勢力,即太史公《史記》中的《儒林》、《貨殖》、《游俠》,最終只有半耕半讀,安分守己的儒生,不失平民身份,沒有遭到禁止。中國古代典籍有很多“道德性”在社會經濟生活作用的描述,如《論語》:“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孔子此語雖說經濟,但主要著眼處并非在經濟上。錢穆推及20世紀,認為:“20世紀世界并不貧窮,人口生殖律也不弱,所患指示不均與不安。”中國古代認為:"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才有用"。近代西方帝國殖民政策與此相反,因財用觀點而拓展土地,而奴役人民,這就是本末倒置。
錢穆概括數千年中國歷史,“自秦至清,直到道光年間,向來佳于西方。經濟落后,是近百年的事。”認為,我們應該引進西方新科學,而保持中國經濟的舊傳統,即“人文本位”的經濟思想和經濟政策。使新學科興起后的經濟發展不至于“超水準”走到“不需要經濟”上去。此外,錢穆經濟學思想展現了我國當今經濟發展的自信與另一種可能,彌足珍貴。就是經濟可能面臨很多問題,并有待新起的經濟學家來設計、督導,來創造一種適合中國傳統的信經濟思想與政策及制度。但我們今天一定不能失去此種自信,“種種聰明,都奔湊到抄襲與模仿上,自己不能創造,也不敢創造。”
錢穆的經濟史思想立足于中國傳統文化,沒有盲目套用西方經濟學家觀點,保持了很高的獨立性。其客觀、理性,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治史原則對于當今史學研究依舊可貴。五四以來,文學、醫學、史學、經濟學等學科提倡“西學中用”甚至“全盤西化”。中國近現代多個歷史時期將傳統文化視為糟粕,眾多中國優秀文化精華沒有得到傳承。更可怕的是社會輿論氛圍將傳統文化與封建殘余混為一談。堅持立足傳統社會基礎,不盲目借鑒西方史學觀點,獨辟蹊徑分析中國古代歷史的史學家鳳毛麟角。一個人的思想對錯需要時間驗證,但沒有敢于質疑、敢于挑戰的精神,一個民族的史學理論怎么能夠有質的飛躍。因此,錢穆先生的治史精神又高于其治史思想,應成為新的時代各行業研究者研習標桿。
(作者單位:1.秦皇島市玻璃博物館;2.東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