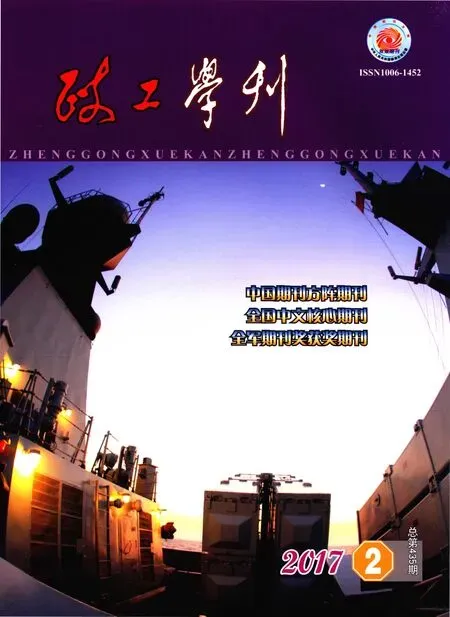家鄉的味道
☉馬紅剛
家鄉的味道
☉馬紅剛
在秦嶺的北面,黃土高坡的南面,穩穩當當地橫著一條東西長、南北窄的狹長地帶,人們稱之為八百里秦川。這里土地肥美,水源充足,糧食滿倉,瓜果飄香。我的家鄉便坐落在這片神奇而美麗的土地上。
面食是家鄉的特色,如岐山臊子面、羊肉泡饃、鍋盔、醪糟等等,花樣繁多,歷史悠久。從這片土地走出去的人們,無論身在何處,味蕾深處總會留下濃郁的鄉土印記。我喜愛家鄉的各種面食,最為鐘情的還是一種叫涼皮的小吃。涼皮以酸、辣、勁、爽而聞名,夏天吃生津開胃,冬天吃驅寒發熱,老少皆宜,百吃不厭。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現如今已經走出三秦大地,風靡全國各處。說起涼皮的起源,已有上千年的歷史了。相傳秦始皇在位時,有一年關中大旱,稻子因缺水歉收,碾出的大米又小又干巴,根本沒法向皇帝納貢。大家正在發愁的時候,有個叫李十二的,用這種米碾成米面,蒸出了面皮,來到咸陽上貢,秦始皇吃了面皮,其味甚美,頗感稀奇,這才赦了眾人之罪。沒想到,小小的涼皮還救了眾多百姓的命。正是這神奇的傳說,使我打心底又多了幾分喜愛,也為身為陜西人而自豪。
記得小時候跟著父母上街趕集,每每經過農貿市場旁的涼皮攤,一雙腿就邁不開步子了,眼睛直勾勾地看著涼皮在盆缽里歡快地跳舞,像身材苗條的少女,腰肢是那么的軟和,舞姿是那么的曼妙,在太陽光下閃耀著晶瑩透紅發亮的光芒,身旁嘈雜的喧鬧聲頃刻間凝固了。“看你那沒出息的樣兒……”我被母親的呼喚聲驚醒了,可口水早就不聽使喚地流了下來。在母親的嗔語中,伸手接過一碗涼皮,仿佛立刻沉浸于物我兩忘的世界,哪里還顧得上什么吃相,簡直就是豬八戒吞食人參果,還沒細細地品嘗其中滋味,就已經嘩啦嘩啦“流”進肚里了。那時家里雖不富裕,但也能隔三差五地吃一次。當時心里想,這可能就是人世間最美的美味了,要是天天能有涼皮吃,那該有多好啊!
小時候奶奶最疼我,她最了解我的心思,就每隔一段時間,自己動手做涼皮,給我解饞。做涼皮需要上等的精粉,在磨坊磨面的時候,奶奶就把第二遍磨下來的面粉小心翼翼地單獨收起來。除去了面粉中的精華,剩下的自然就黑一些,口感也粗糙不少。在接下來一個月甚至幾個月里,全家人就不得不吃黑一點的面食了。做涼皮很是費時費力,奶奶雖然上了年紀,但身體也還硬朗,她不顧辛勞,連夜洗面做準備。洗面有點像洗衣服,先把面粉和成面團,在清水里一遍一遍地搓揉,把洗得牛奶一樣白的液體倒入更大的盆里,經過一夜的沉淀,再把浮在上面泛黃的水倒掉,剩下黏稠的白色液體,就是蒸涼皮的原料。洗面的過程其實是最累的,而且只能用涼水,尤其是在冬天,兩只手長時間在涼水里不停地搓洗,刺骨的冰冷直往心里鉆。蒸面皮也要起個大早,等鍋上冒熱氣后,把洗好的面水薄薄一層攤平在特制的籠屜上,鍋蓋壓嚴實,大火猛燒約兩分鐘,一張水晶透亮、彈性十足的涼皮就蒸好了。灶膛里燒的是煤或木頭柴火,風箱呼啦呼啦,大火熊熊燃燒,映得灶火邊奶奶的臉紅彤彤的,一雙眼睛特別堅毅有神,那溫暖的畫面直至現在還常常想起。等廚房里騰云駕霧的時候,所有的面皮就蒸好了,為防止粘連,奶奶還會抹上菜籽油,用熱油把辣椒面燙得滋滋作響,涼皮的麥香、菜籽油的清香、辣椒油嗆鼻的香氣,爭先恐后地彌漫開來,真是勾人魂魄,讓人欲罷不能。當我們大快朵頤陶醉于幸福之中的時候,奶奶那布滿皺紋的臉龐如花朵般綻放了。說實在的,自家涼皮的質感遠比不上市場售賣的,但是這種特殊的味道,滲透著家人的疼愛,永遠印刻在了心底深處。
長大后,到外地求學工作,節假日得出空來,就喜歡大街小巷地亂轉,尋找家鄉的美食。隨著年歲越來越長,離家越來越遠,思念的味道也愈來愈濃烈了。去年,在一個陌生城市的背街小巷,終于找到一家陜西小吃店,頓時倍感親切。在與老板的閑談中,得知我們是同一個縣的,兩個村相距不過百八十里。老板很樂觀,總是笑呵呵的,他說以前家里窮,思想觀念也保守,固守著老婆孩子熱炕頭,大家都一樣,誰也不笑話誰。如今卻不一樣了,大家南下的北上的,不僅把我們陜西的美食帶到全國各地,還變成了一條脫貧致富的好路子。我由衷為家鄉勤勞致富的鄉親們高興,小小的吃食能填飽肚子,也能讓人過上好日子。
是啊,我有好幾年沒回去了,家鄉的變化可真不小。前段時間,母親寄來一些特產,在包裹箱的底部,居然放了我最愛吃的涼皮。兒行千里母擔憂。原來,家鄉的味道一直陪伴著我,這便是兒時成長的記憶,是歷久彌香的思念,更是珍藏在心底的絲絲縷縷的親情。
【作者原系海軍指揮學院政治部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