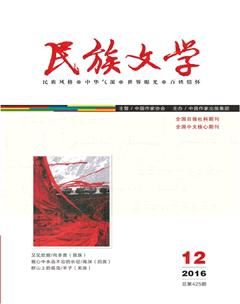時間的烏鴉
綠窗
是前幾年秋,我乘車穿越山野,蘋果垂向大地,塵寰靜美。前座的男人忽然講起一個驚悚事件,北方偏僻村莊的,殘篇斷簡,話如刀鋒削過樹枝,立刻后背冷森森了。更多細節被恐懼遮蓋,我怯于凝視,當作深淵遠遠地避著。直到我閱讀茨威格,“如果你長久地凝望一個深淵,它便也就凝望著你了”,說尼采生命最后的五個月,激情瘋狂,幻象如暴雨,仿佛魔鬼扼住了咽喉,必須噴薄奔涌,醫學上稱為欣快癥,茨威格說是深淵之上的舞蹈。也許瀕臨絕望的人心里都曾奔跑著一個尼采,突然爆發一種力量,超乎尋常,如同精神錯亂,偉人抓住了真理,怯懦的小人物呢?大概只能制造一次事件。
有些恐懼如同疼痛,時間埋不住,早晚要躥出牙齒,昭告世人:不珍重待春風,細雨,花朵,陽光,甚至寂寞些的安寧,是傻透頂,不知福。豈知有些人要用掉許多年甚至一輩子,才能贖回被黑烏鴉叼走的好時光,苦難遠非我們想象。
一旦追溯根由,仿佛我就立于實驗室,抄起探針,刺進一只青蛙隱秘的顱腔,左旋右搗,蛙斃。蛙忐忑,我亦戰栗。生命在承受詭秘的深淵,耳朵逼迫意識,剝離下去。
1
黑夜使他放光。那個人說。
這天,他子時即起,露水汩出植物的清氣,一顆星快速劃過西南角,本該呼嘯,卻像一抹煙碎掉了。他劈柴燒水,火光雕刻他的表情,似哀傷似祈禱,猶如忍受過蟒蛇緩緩勒緊的摧殘,眼睛是深陷的豬籠草,鼻唇溝蔫成大旱天玉米秧的錐尖,尖頂卻頑強地冒出一叢花線來,他的長須,接壤頹肩的灰發。
他抱起半瘋的女人,她咒罵著蹬踹,一進水里,老實了,臉上現出孩童的光芒。他呆了一下,他怕這種光。他也坐進水盆,用力搓洗厚厚的塵垢,多年累積的屈辱,不甘,憤怒,漫漫長夜黑透的星光,看不清色澤的花朵,一瓣瓣剝落了。
胡須那么輕,仍是重的,剪,控制嘴巴的鏈子,咣當委地。
大黑夜做這些如同白天,他早混同了黑與白,哭與笑。他去鎮上買回最鮮的菜肉回來,太陽才昂昂地爬上山尖。
他在村里一家一家地走,多年不走動了,看慣了他病態的陰郁,冷不丁像個人樣,每一戶都一驚。他誠懇地邀請主人到他家吃頓午飯,極力笑了下,如刀切在極哏極澀的瓜上。他們來不及考慮,驚慌著答應了。他武二呀,肅殺。
院子深而靜,武二獨女已折,不年節不過壽,門口貼了紅對聯,擺著鞭炮,瘆得慌。但見四桌大菜,泛出香味,大家略有松弛。
2
我發覺試圖還原記憶,亦是小磨難,窗外一黑,我即惶然,幾次欲擱筆。為稀釋緊張度,我插入我們村莊的另一件狂人紀事。我曾疑惑,現在也不肯定,他們的行為對與錯,善與惡,美與丑,在醫學上是否屬于精神的缺陷。但我以為小人物和偉人在心路歷程上,也定有著重合處,他們都是黑暗中長期摸索,努力尋找光明的人,與心魔搏斗的人,是深淵之上的舞者。
在我們村,只有紅白喜事和孩子滿月,才能動請村中所有家庭。這正顯示村莊獨特的責任與力量,不論親戚貴賤,存在古老的締結關系,一家的悲傷就是全村的悲傷,一家的喜事也是全村的喜事。沖這點,村莊永遠高于城市,體現遠古的人類精神。
臘月底了,我正與母親忙碌過年的事,村東傳出有板有眼的哭調,心立刻緊縮起來。東面,雷爺家的柴門上頭挑起了歲頭紙。雷爺長子臉色凝重,急急走。
雷爺,上世紀三十年代生人,滿族后裔,黑紅臉,身高粗壯,有使不完的力氣,早年種地飼馬,后遇良人薦了管倉庫的活,后攤上了官司,人生大起大落,仍改不了骨子里的血性,不管啥事尥蹶子就上,一匹草原上奔騰的烈馬,打不倒,幺蛾子多,抽不冷子就拽響一個雷,嚇村鎮上一跳。高興時三吹六哨,這叫精神,骨氣,這叫老驥伏櫪,比曬太陽等死,上了一個榛柴坡了!那架勢,天地日月都會照應他長命百歲,忽而腐朽了?
說,是老人自己作的。孫子來送飯,見雷爺赤條條橫地上叫,爐子滅了,窗紙扯壞,風嗷嗷地灌。趕緊叫人一番收拾,弄好。再去送飯,老人又是赤條條趴地上。幾天下去,兒子們終于明白,老人是在說話,他要“挪鋪”了,要“下去了”。
那條小徑曾經雛菊擋腳,籬笆墻鉆滿燦黃的金簪子花,幾頭牛懶懶地嚼著祥和,雷奶拎著鏟子站在屋檐下,呵斥叫嚷的大黃狗,一面笑著邀請行人,聲音里有酥甜的烙餅味。
轉眼鍋涼灶冷,雷奶去世三年,雷爺也走了,帶著他的秘密和不甘。院子沉了,多子多孫的雷爺家,肅穆里有另一種豐盈。
3
猛然間。車震動了一下,那個人嗓音變緊,仿佛弦要繃斷了。
一人瞥見棒桔遮蓋的紫紅大柜子,靠墻小案上,供著花果,黑白照片上燦然的姑娘立在大號黑匣子上。他駭然一叫,大家的臉跟著白了。都知道,匣子里不是器物珠寶,不是骨灰,是李慧娘那樣,怒目圓睜著的,武二女兒的頭顱。
這匣子他拎著走了二十年。麻雀咕咕叨叨換了幾十茬,陪他一起痛哭的人,有的入土,有的遠走,有的成家立業杏花滿枝頭。只他一門素簡,一身黑衣,像黑紙白字,醒目的枯冷。他拒絕紅,不吃肉,不穿過暖的棉衣,不刮胡子,每根胡須都是不屈的小烏鴉。
他的不幸,指定也是村莊的不幸,他一個人的黑暗,整個村莊都陰郁起來。拎著炸彈的幽靈,肩負秘密使命,怒沖沖走著。他一走上街頭,街頭就空曠了,他一出門,天就黑了。
他就是一襲鬼魂的形象,有暗夜的氣味,但許多活在光下的人,似乎也不過是傀儡罷了。漸漸地,他自己也怕了光,只愿在黑夜行動。鋤地,施肥,在大月下等一枝野花開了又合。他盼著祖先的幽靈能一個個出來,幫他行風行雨,倘或有一條明路,他寧愿是甘心赴死的老禿鷲,給成群的兒郎啄吃。
他空著手,手上仍像拎著一把刀。以為林教頭的風雪山神廟,百般憋屈,終于搠出明亮的一槍。但這個怪人,兇狠的面孔下,內心卻是良善的土壤,刀只扎向自己,骨頭密布內傷。
他拿不出柔軟,炊煙里迷蒙的溫馨,嗅不到每一個節氣里類似玉米大豆成熟的清歡。他的老房子是洞窟,洞壁低飛著悲鳥。
4
每個瓦片都蓋著秘密,每個皺紋里都匿著悲苦,一旦抻平,秘密坦露,黑深裹著白。而刀片,可以任意劃開一段皮毛,肉骨分明。當它漸冷漸僵,殘碎的肢體扔進垃圾堆,操作臺干干凈凈,人們很快就忘了那個會叫會疼的生命,之前的不安也沒了。
雷爺一走,一直在村莊的枝頭上鼓噪的烏鴉,消停了,村里村外許多提著的心安寧了。
破老頭,快八十了,十幾畝地不摟干,就想說個后老伴兒,剛提了頭,孩子們紛紛扣動機關,射他一百單八箭,渾身篩子眼。當年雷奶苦熬十八春,敢說老婆子進家,踹不死你。
那十八年監獄生活,是他的深淵,一輩子的羞恥。別的孩子哐哐冒出來“坐法院,十八年”,兒子們石頭瓦塊立刻投將過去,恨不把對方腦袋開瓢。深及骨髓的痛,必產生深及骨髓的憎恨。
他立刻蔫了,怯怯收斂著。他擺不出父親的尊嚴,哪個孩子都能橫眉怒目,呲他個兵敗如山倒。他認,只有豁出力氣,像能干的騾子,大量承包土地。老天獎勵他,十年,房子一處處蓋起來,兒媳婦一個個娶進來,孫男娣女一個個撒歡跑了。那真是不小的工程,別人累死也揍不出來。這匹奔騰的老馬,終于可以喘口氣,響亮地抽煙說話了。
可是雷奶突然走了,他的心上,如同酸菜大瓷缸里壓個大石頭,要發酵出什么。他從電視里聽到一個新詞“上訪”,十分順耳,清官過街,鳴鑼開道,得遞個狀子上去。他過去可是官家人,識文斷字,不少掙錢,但架不住雷奶土地肥實,真應了結婚時的喜歌:“搟面杖,敲門框,丫頭小子養一炕。”連珠炮的一炕小蛋子,吃草芥了。他酒后起了貪念,拿些倉庫的東西,正是嚴打,二十年高墻就此壘成。
雷聲隱隱,河灘上的茅屋燈光閃爍。他仔細研究買來的法律法規,以為當年量刑過重。威嚴的庭上那一記錘聲蒼然落下,他這樹干折了,他的七郎八虎遭受多少磨難,小兒尚未斷奶。他突然奔出茅屋,跑向梁頭,抱著一棵老杏樹哭嚎,才從麻將桌下來趕回家的人嚇毛了。
時間的烏鴉躥出塵封的巢穴,他要上訪,他是犁鏵下激情燃燒的種子,無可阻擋。
5
萬物朝生,純粹的孤獨是沒有的,受難的狀態,精神的苦悶,是一棵樹上的葉子,風來哪片不動?那個人仿佛犯了偏頭痛,摁住太陽穴,齒間費力地蹦出字來。
花枝開,隨手花枝謝。二十年前的深秋,武二唯一的果實被殘暴地收割了,他活著的食糧,生命,未來,都沒了。他的女兒,銀行小職員,被一個貪污事件污染了,押解的途中小解,憋急的她向著林子奔跑,子彈瞬間穿越了她的腳步。被蓬頭垢面扔進了太平間,被加上重重的罪責,白紙黑字的長棺戳了三寸大釘。
憤怒者藏了刀,借著黑,潛入太平間。
他捧著她回家,像捧著幼小的芽孢。他摸到冰涼的斷頸,喉嚨憋進腔子里,發不出聲,心上左一刀右一刀,白厲厲的茬口,流不出血淚。他用清水擦洗她臉上的驚愕,梳理她發絲上的哀塵,小心放進玻璃容器,福爾馬林里,像制作一件精美的醫學標本。他挖了更深的地窯,搬進冰塊,安放了這顆長發飄然的頭顱。
夜里她冒著滿腔的熱血來找他,含著淚水懇求放她投生。他咬牙不答應,她罪不致死。他叫她的靈魂暫且歇著,他要帶她的頭顱去找清水,大江大河,大雨大雪,來洗泡她,讓她透亮,讓她有真面目,桃紅李白。
世界只有通過極端才有價值嗎?極端了也未必展現真理,倒刺反戳向自身。母親驚斷了魂,大罵造孽,要天打五雷轟,下十八層地獄,昏厥不醒。她心中的燈滅了。
他披掛上陣。他奔跑于曠野。他大戰風車。那野蠻又危險的人,那嗜血的冒火的眼睛,那風雪交加深一腳淺一腳的路,那不腐的水里飄動的亂發。
6
是什么思想的激流奔瀉而下,魔鬼撕扯著他的靈魂,他竟如此激烈憤怒,嚎向天,刃向骨肉。那一斷,驚破心。
魯迅說,不知死日,不知死地,不知死法,是生命最悲苦的代價。包公審過一案,一家突然出現無頭女尸,父親被下了大牢,女兒為了給爹澄清,自縊而死,母親隨即割下頭顱,送上大堂。絕望的逼迫下,一門剛烈,愛到極致,冷到極致,完全超乎常人的理解。
他暴虐的氣質,也許源于長期的性格閉鎖,也許來自家族深刻而孤獨的血脈,也許他中了狄仁杰和包公斷案的毒,只有觸目驚心,才能觸動法庭,觸動社會,制造大的效應。理智,屬于圣人偉人,要么是無心之人,懦弱之人,麻木的,不敏感的軀體。
善良的血液里也藏有暴虐的因子。我初時帶學生做實驗,也曾拎著兔子耳朵錘擊枕骨致其死亡,有時枕骨青爛,亦不死,解剖一半,它突然蘇醒尖叫,魂都飛了。但我也竟能趁著那一點溫熱,三兩下剝掉一只兔子的皮毛,一撕一拽,仿佛對付的是一匹絹帛。我做藥理課題時,頸椎脫臼處死過幾百只大小白鼠,嘎奔兒,脊髓與腦髓拉斷,脆,成為一種節奏。
令我不安的是斷頭處死小鼠,瘦弱溫婉的導師沉著示范,左手握鼠身,右手鋒利的剪子,對準脖子咔嚓剪下。掉在水池的頭顱尚沒意識到這變化,眼睛還在眨,努力扭頭要看個究竟。我忘不了小白鼠朱砂痣一般哀傷的眼神。它犧牲于暴力,它有邪惡之氣。但我堅定地以為,它就是通往救死扶傷的沿途祭品。反省是后來的事。
“生命的實質似乎是絕望與驚駭”,列維坦觸摸俄羅斯蒼茫大地的時候感慨。當我深入靠近生命,看到了扭曲猙獰血腥。我仍不敢在凜冽的刀鋒停留片刻,骨的疼痛只有骨頭知道。頭顱會想念它的肢體嗎?靈魂會想念它的肉身嗎?二十年孤獨的抗爭,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又夜鳴,他們要怎樣穿過暗黑之痛?人們定不愿提起這迂腐笨拙的怪物,可憐可悲可嘆的黑烏鴉,怕不祥的空氣污染了陽光和干凈的清風。他寒入骨髓,而他的房子和村莊之上,世間一切明媚。
7
我不能偵破,那個默默掙扎忍受的靈魂,我只是在時間之外,揪出那個尖利的黑點。出發是活著的佐證,是為了尋找光亮。我想不出武二走的路,但我知道我村莊的雷爺,為了驅趕那二十年的黑暗,自己駁掉老年的老字,躲開阻攔的兒子們,踉蹌上陣。
一級級申訴,一級級駁回了,路上荒草一片。他首次讓心愛的玉米泡了荒,再一次向更遠出發。他沒有什么醒目的證據,只有他蒼老的年歲。
午后,街頭大榆樹下,一輛警車威風地馳進村莊,京字號。一個武裝戰士下了車,打開車門,恭恭敬敬攙下一枚老頭。雷爺!他們護送他回到茅屋,鄭重地交到兒子們手里。
這一次,他秘密地,扛著大牌子,去了北京。他太激動了,日頭刺進他和他的影子,晌午歪時,昏倒在大地上。醒來后,粉嘟嘟的護士正給他掛輸液瓶,“國家醫院,國家給治病,那大房間,護士跟天仙似的,說話跟小鳥似的,咱全鎮找不出一個。”雷爺的幾根長眉毛快飛到樹梢了。“這回國家給做主,層層下報告,我那二十年,要翻過來了!”他背著手踱到街頭,眼神明亮,像剛從前線下來,身上帶著打勝仗的硝煙味。
果然,鎮里來人了。“說,上面一個電話打到市里,市里一個電話打到縣里,縣里一個電話打到鎮上,鎮上一個電話打到村里。市里罰款,縣里罰款,鎮上罰款,村里罰款,好家伙!威風!”
8
力量從大地上生長。種下玉米的,祈求玉米拯救。
那個人喝了一口水,調整情緒,說出結局。
四處都是柵欄,有身披鎧甲的勇士。武二不能出發了,靈魂也似乎被關在了匣子里,守著日歷,一日日黑下去,黑撕盡了,會不會露出白?
他拿起了木匠活計,要給孩子造個像樣的宮殿,讓她有正宮,行宮,別院。覺得樣子單一,刻進一些鳥獸花朵。為著畫得有神,他盯住野雞,野兔,狐貍,獾子,桃花,桔梗,山櫻,百合。他懷著悲傷的眼光,看著這些毛茸茸的生物,似乎慢慢長出柔軟的皮毛。大雪天,獵手們上山布置陷阱,后腳他就蹓過去,拿木榔頭碰壞了偽裝。
然而他越發不安,痛苦萬狀。她托夢說,造最好的宮殿,她也戴不上王冠,身首異處是最嚴酷的刑罰,她前世造孽何其深重,今生才受此咀咒。他大汗淋漓,控訴別人的暴行,焉知自己亦生著施暴的手,他動了魔鬼一根頭發,魔鬼回手扼住了他整個頭顱。她托一次夢,就是給他上一次夾棍。他墮入了潰爛的深淵,忍不住發出尖利的嚎叫,人們既恐懼,又心疼,隨后的寂靜堪比疼痛刺耳。
他行將崩潰。他去懇求香頭,村里的大神,負責全村人的靈魂解脫。神說,他身上陰氣太重,暴虐性重,陽性的不敢進身,他應該深埋一切帶有血污的東西,多曬太陽,積德行善,多長正氣,以去邪氣。神說,地有土地爺,山有山神,家有保家仙,長仙(蛇),黃仙(黃鼠狼),狐仙,兔子仙,他的一切行動皆在天地神明的注視下,神也一定在庇護他。
野花繞過來,日光紛紛射入了他的胸膛,逼迫寒氣一點點起身,骨頭也似乎熱了。“該做的你做了,不該做的你也做了,現在你該從黑夜擠出白色的圣果,讓他指引今后的日子。”神教他禱告,那個圣果叫寬容,你憤怒,果實就不會成熟,靈魂永難安生。
他似懂非懂。但做回陽光下的農夫,做回他在紅白喜事中熟練操作的大廚,說聲“油著,慢回身!”而鄉鄰都盯著他,無比羨慕。這些思想,突然像滿坡橫生的野草,壓不住的新生氣力。他能否解禁自己,解禁房屋,小路,和不安的村莊?
9
正是,鬼魂已諒解,復仇者還揮舞著長劍。他匍匐在自己的黑暗里,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亦有災難殺戮疾病非正常死亡,多少人因此絕望哀愁,一片惶然。但大地深處有多少寒氣,大地之上還是草生花長,這就是天道。所有的功成,只能來自于內心,上天救你,實是自救。
雷爺偏執了,白紙黑字的重新判決并沒有落實,他夾著黑包再次出發了。回來時,臉上密布頹廢的汗珠。大巴車和出租車主都有他的照片,拒絕拉他。工作組帶著慰問品來看他,兒孫滿堂,消停了行不?兒子們接了任務:看好他,誰捅婁子誰負責。
一個精神有毛病的人,一個令人討厭的人。雷爺澀答答了,不種地不做飯了,孩子們輪值。他散步,采菊,遛狗,思考大事。他到鎮上逛,跟擺攤的婦人嘮嗑;往曖昧的按摩店里去;他盯住婦人的背影拐進瓜地,硬把自己的影子疊加上去;他像河邊那頭老驢,自言自語,或剛剛大笑。每一件事都引起村莊的悸動。他終于按捺不住,哐哐敲了寡婦的門。
雷爺倒了。兒子們羞恥心驅動豺狼虎豹,打斷了他的精神。
一場透雨,他又翠綠了,他那蓬勃的思想用不著春風吹。法院的傳票突然遞到兒子們手里。趁大家忙著收玉米,他把兒子們告上法庭了,說不孝。才吃了兒媳送過來的飯,馬上又上堂對質,滑稽,他遭到嚴厲的訓斥。破老頭,生蠱蟲了,就不能安靜老去?
夜半,兒子們請了香頭,畫了幾張黃符,點燃一張,念念有聲,“該走的快走,該留的留下。”繞他身上一圈,把那鬧騰的魂靈送到西天去了。
10
那個人一直沒回頭,他徐徐吐出一些細節,響應我手里的刀片。最后的現場,他在。
他頭皮發炸,但還是堅定地看著。武二攔住了騷動的鄉親。“我想讓大家見證,送她走,讓她安生去。”受難者不是孤立的存在,天空大地人,都在。
武二用水泥封上了地窯,倒了三碗酒,敬天,敬地,敬亡靈。而后,打開了黑匣子,露出玻璃器皿,她飄蕩的發絲,緊閉的眼睛,樹皮一樣的臉色,羞怯,惶恐。武二安慰著,請她的靈魂原諒,用干凈的白布擦拭,梳理,移駕到她的宮殿,穿好衣服的木身子上,縫好。她圓滿了。武二叮囑她要痛快地喝完孟婆湯,一滴不要灑,來世她會是純潔的新人。
鞭炮熱烈地響起,那沉沉地壓了二十年的不安,請出去了。武二凈水潑院,掃房,除塵,迎接新的陽光。仿佛他的食糧,他的自由,他的小鳥,那個院子,都將在陽光下活過來,過去的一切都是虛無,是荒謬的惡夢。
散發寒冷的,只配得到寒冷,散發溫暖的,溫暖來到。這時,天上掉下了終結之果。武二收到十幾萬匯款,一份遲到二十年的裁決。
11
人的內心亦潛伏破壞的力量,向內使,自殺,向外使,殺人,或攪亂空間,失衡。攪不動了,玩完。
那日早起,我踢著露水草跑過雷爺的家,見他黑蟾蜍一般,摞在門前的石墩上,胸戳進肚子里,腦袋戳進腔子里,像身體對頭顱視而不見。我從遠處拍下他此時,和他在街頭遠離眾人孑然而坐的影子,那種嗜血的孤獨與尷尬。
他眼里的公平與孝道,指定和兒子和法庭都不一樣。就是滿足他的需求,估計也只是一時,他的內心澎湃著激情,努力地要活出他認定的,一匹奔馬的模樣。但與人們的慣常越來越遠,成為可笑可悲的范例。
我說,雷爺,石頭太濕了,小心著涼。他把頭抻出半寸,哼了一聲,又縮得更深,更矮,到扁,到無。
沒到人生秋天,他痛快地搖落了自己。他砸碎所有的藥,赤身一次次滾落濕冷的水泥地。這剛烈的血性的死,是他最后的作品,再次驚動村鎮。人們把他當作一個有德行正常壽終的老人,隆重地送走。
12
時間把人沖得七零八落,自然一步步推進,什么樣的結局都屬瓜熟蒂落。我在雷爺孤獨的影子里,看到武二更深切的孤獨。也許他們最真切的需要,并不是真理,而是來自情感的真實溫暖,內心的安寧。
二十年,悲哀爬進每一個細胞,蒼涼看飽,他穿過深淵,是哲人了。人如草芥,但不能活得如草芥。他將扶起自己,冷靜于深秋,大地之上。他推著老伴曬太陽,花朵在身旁開放,他們滿臉是受難后的安祥,天國的光輝照耀著。
但很可能,武二得了強迫癥。他不能饒恕自己,長日到墓前擺酒謝罪,大把地燒錢,終于在一次大醉后,以頭做錘,瘋狂擊在墓碑上。痛苦中埋下的利刃,長出了更鋒利的寒光。
或者武二遠走異鄉,像斬掉一顆頭顱一樣,斬掉了故鄉。
或者,講者就是親歷者,我怕他回頭,會有一幅瓜薩亞明骷髏般的肖像。
也或者事件本身就是虛擬,我的刀片只是分解了一只蛙,我聽到的只是一種含混不清的呼嘯。一只時間的烏鴉,多年后叫出的預言,也許沒有什么用,終究是個警醒。
生命,飽受生活的逼迫,即貴且賤,無不惶然,每個人都該是深淵之上的舞者,努力去嗅大地橫溢的豆香,聆聽太陽安靜地碾過萬物,而充滿飛翔的勇氣。
責編手記:
這篇散文寫的是小人物的悲哀與抗爭。乍讀起來,隱喻的描述與臆想較多,似不是十分曉暢,但恰恰一股別致的“澀”味,正與主角們的命運融洽了。兩個人,兩條線:一明,“我”村莊的雷爺,親身經歷;一暗,車上聽說的武二,試圖還原他的經歷。蒙冤受屈的底層百姓,生活陷入困頓,運命發生轉折,但他們沒有認命,終有一天驀然覺醒,意識到應該向社會尋求尊嚴和公正,由此開始了卓絕的跋涉。其間遭受種種阻遏,心靈屢屢挫傷,但他們未曾妥協,寧可將整個生命放棄,留下一個大寂靜給世界。漫長的數十年人生命途,銷蝕的是活生生的時間,而這暗黑的烏鴉,或許它剛剛落下,或許它終于飛走了。關乎命運的思考,作者似乎一直被一種強大的不可知論所圍裹著,顯得有一些悲意迷惘,但對生命時光的尊重,同樣被作者置放在了心靈的高度上。這或許是理解此文的一個角度。
責任編輯 石彥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