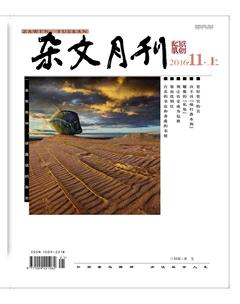護蟬行動與抵制捕螢的昭告
陳慶貴
蟬鳴乃天籟,夏季最常聞,它鐫刻著厚重的鄉村記憶,承系著濃濃的游子鄉愁。歷古以來,多少蟬鳴詩文讓人魂牽夢繞。最喜南朝王籍名作《入若耶溪》佳句:“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其被譽為“文外獨絕”,乃千古傳誦絕唱,呈現了詩家筆墨難以抵臻的體驗化境。
歌手羅大佑在《童年》里唱道:“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在聲聲叫著夏天……”夏天聽蟬,國人最憶。可近年來,蟬鳴離我們漸行漸遠。原來,蟬鳴不僅能迸發雅士詩興,還能刺激俗人味蕾。蟬,昔往曾為達官貴人玉盤佳肴,現今則成“美食家”們特色小吃,自然不幸成為獵捕對象。在“捕蟬大軍”掃蕩下,一些地方蟬鳴行將亡群滅種。幸好,天無絕蟬之路,一些地方民間自發發起護蟬行動,強力反制“捕蟬大軍”造孽,攜手看護蟬鳴世界。其中,自設“金蟬保護區”者有之,倡議“留住蟬鳴,留住鄉愁”者有之,自組“護蟬大軍”者有之。
無獨有偶。杜牧《秋夕》里寫流螢的佳句“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也堪稱不朽經典,庶幾抵達“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的詩藝至境。關于流螢,《晉書》記載的《車胤囊螢夜讀》勵志故事,可謂世代相傳,家喻戶曉。可以說,與鳴蟬無有二致,作為鄉村行將消逝的記憶符號和鄉愁標簽,流螢亦“載不動許多愁”,承載著厚重的鄉村記憶和濃濃的游子鄉愁。要命的是,與鳴蟬命運多舛同病相憐,如今流螢也罹遭人類捕捉的厄運。
不知濫觴于何時,打造“螢火蟲公園”,搗鼓“螢火蟲主題展”等人造噱頭,成為國內不少景區跟風盲從的時髦。這邊廂,人造流螢惡作劇持續升溫;那邊廂,野蠻引進致死流螢悲劇輪番上演。放飛數以萬計的螢火蟲固然能讓觀者養眼,但卻在復加毀傷我們已然脆弱瀕危的生態系統,加速透支我們留給后代愈加骨感嶙峋的生態遺產。流螢發光,本屬其繁殖期求偶行為,“蜜月”捕捉無異于殘忍殺戮,甚至給種群帶來滅頂之災。在生態系統食物鏈等級上,螢火蟲種群數量驟減,意味著將對其他生物帶來“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連帶災難;如果是外地“進口”螢火蟲,則可能引發外來物種入侵的生態災難。讓我們稍感釋懷的是,幾乎每次人造流螢惡作劇,都因民間環保組織和良知媒體的聯手抵制干預,而被叫停或流產。
其實,觀賞流螢并非吾國專利,國外早已有之,只是觀法分野罷了。我們一些人不惜破壞生態,將螢火蟲捉到家門口給人看,誤導強化民眾生態認知愚昧;人家旨在保護生態,把人送到螢火蟲家門口看流螢繁衍,濡染強化國民生態文明意識。2014年7月14日,美國田納西州大煙山國家公園埃爾克蒙特露營地,迎來每年一度螢火蟲繁殖交配季,無數只螢火蟲在空中飛舞,美麗點亮整個夜空,吸引數千游客到此觀賞。如今,日本人之所以還能在現代都市感受到“晝長吟罷蟬鳴樹,夜深燼落螢入幃”的生態體驗,既得益于民眾生態保護文化自覺,更歸功于城市規劃的“生態留白”。相形之下,我們不是在“開發”的名義下,干著格式化螢火蟲棲息地的蠢事,便是打著“創意”的幌子,向蜜月中的流螢伸出黑手。
鳴蟬與流螢,均為具有指標意義的生物,它們與人類對生態環境的要求高度趨同。換言之,呵護蟬鳴與流螢,其實就是呵護我們自己。要不要護蟬行動與抵制捕螢,不是問題,問題是,護蟬行動也好,抵制捕螢亦罷,目下多為發軔于民間的自發行動,罕見相關地方政府出手作為。設若說民眾的覺醒和行動,充其量只可謂義不容辭;對肩負公共治理“天降大任”的相關官員而言,在文明教化、規劃保護、完善規制等方面“該出手時就出手”,則堪稱責無旁貸。無論如何,生態文明不能單單指望來自民間自下而上的自發覺醒,更須政府自上而下的強力推動作為。護蟬行動與拒捕流螢昭告我們:一些地方的生態文明行動,“民眾已經過了河,官員還在摸石頭”。